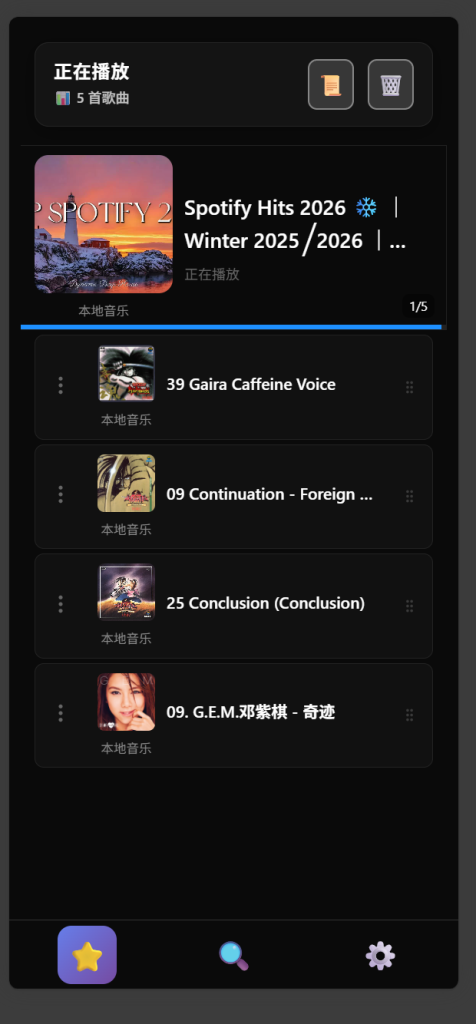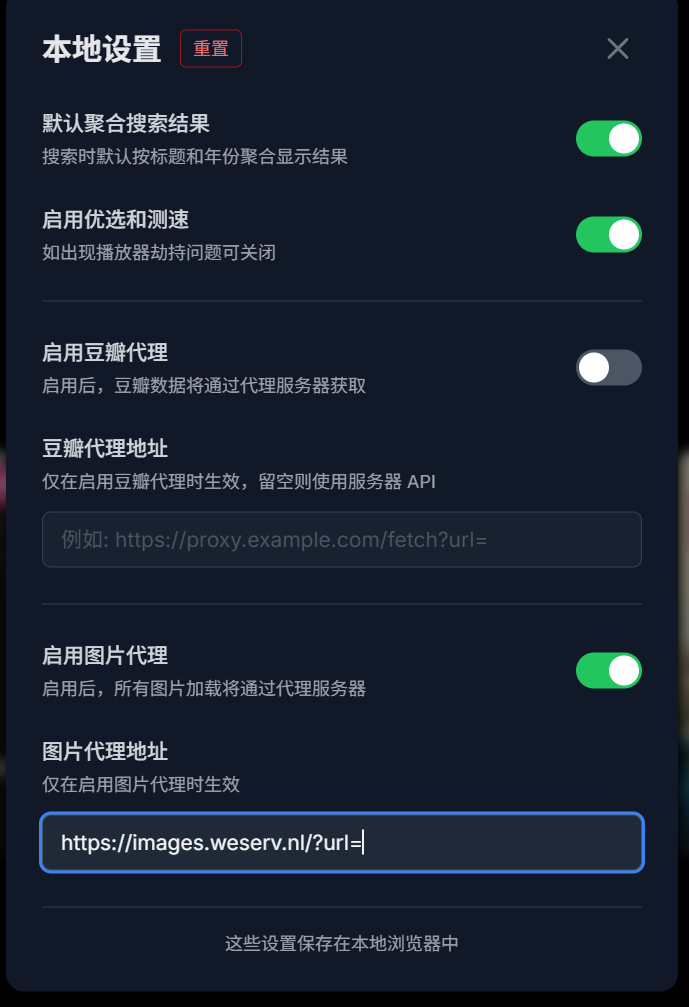目 录
版权信息
中年之路:人格的第二次成型
译者序 听从内心的召唤
序言
第一章 临时的人格
童年创伤
个人情结
第二章 中年之路的出现
内在压力与预警
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身份变化
撤回投射
身体和时间感的变化
希望的减退
神经症体验
第三章 内在的转变
人格面具与阴影的对话
亲密关系问题
中年外遇
父母情结的影响
职业世界:工作与使命
劣势功能的显现
阴影入侵
第四章 文学案例研究
《浮士德》与《包法利夫人》
《地下室手记》
诗人与诗歌
第五章 个性化:荣格的当代神话
选择与决定
个体化的意义
第六章 航海与孤独
从孤独到独处
消化分离的创伤
经历丧失和撤回投射
直面恐惧的仪式
联系失落的孩子
激情的生活
灵魂的沼泽地
伟大的辩证
牢记死亡
生命是一束光
精选参考书目
普通参考书目
中年之路2:解开前半生的束缚
前言 对意义的探寻
第一章 无处不在的内疚
真实的内疚
非真实的内疚
存在性内疚
第二章 哀悼、失去与背叛
找回领航的星星
失去与哀悼
背叛
第三章 怀疑与孤独
无垠空间的寂静
孤独地漂流在灵魂的公海上
第四章 抑郁、消沉与绝望
三只乌鸦
抑郁:无底的深井
消沉:无精打采的国度
绝望:最黑的乌鸦
第五章 强迫与上瘾
地狱一季
强迫思维:不请自来的念头
上瘾:伊克西翁之轮
第六章 愤怒
喂饱三头恶犬
第七章 恐惧与焦虑
焦虑如冰山,我们是泰坦尼克
管理焦虑
第八章 情结:“大脑主机”里的模式化反应
第九章 穿越沼泽
重新想象自我
参考文献
后记 斑驳与模糊
版权信息
书名:中年之路(全2册)
作者:【美国】詹姆斯·霍利斯
译者:郑世彦 苏西
·
在人生的中途
我迷失了方向
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黑暗的森林。
——但丁(Dante),
《炼狱》( The Inferno )
我们的心盛满新的痛苦,
新的光彩和沉默。
神秘变得野蛮,上帝变得更伟大。
黑暗势力提升,因为它们也变得更强大
整个人类岛屿都在震动。
——尼古斯·卡赞扎基斯(Nikos Kazantzakis),
《上帝的救世主》( The Saviors of God )
生活向后回忆,但活着必须向前。
——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
《克尔凯郭尔日记》( The Journals of Kierkegaar d )
若将你内在的东西活出来,
它们必能拯救你。
若不把你内在的东西活出来,
它们必将毁灭你。
——《多马福音》(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Thomas )
译者序
听从内心的召唤
有本书里引用了这样一段话:
正如荣格所断言的:“神经症的暴发不仅仅是偶然的。一般来说,这是最关键的时刻。它通常是
要求新的心理调整、新的适应的时刻。”这意味着我们的心灵组织了这场危机,制造了这种痛
苦,因为伤害已经造成,改变必须发生。
当我看到这段话时,我便搜索它出自哪本书。当我看到书名 The Middle Passage:From Misery to
Meaning in Midlife 时,我便寻找这本书。当我得知这本书没有中文版时,我便联系了出版社。当
我手上还有其他稿件时,我便寻找小伙伴一起来翻译这本书。几经努力,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出
版机构,经过日夜锤炼,翻译、审校和编辑的工作也得以完成。因而,此刻她能与大家见面。
在这个过程中,我不知道是我在努力寻找这本书,还是这本书通过各种方法找到了我。
不可否认,我的人生走到了中年,且经历了一些痛苦,我想理解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人人如
此,我想在这本书中寻找答案。但换个角度来看,是这段话潜藏在书中,等着被人发现;而这
本书又借由这段话伺机而出,她在等待和召唤一个有缘人。
不管怎么说,这本书的出现可谓恰逢其时。人到中年,必须经历一场转变。
在成年早期,或者说,在第一个成年期(12-40岁左右),我们的人格不过是对外界的反应的集
合。我们还不完全了解这个世界,我们学习的是身边大人的态度和行为,我们被要求成为这样
或那样的人。到了第二个成年期,我们才有了一点闲暇和空余,自我才有了一些力量,可以琢
磨着如何“成为我自己”。
成为我自己,这是心灵发展的目标。在荣格看来,心灵是一个实体,有其自身的目标,那便是
求得圆满。对一个人来说,便是尽量实现完整性。一个前半生依赖性强的人,后半生需要学习
自力更生;一个控制性强的人,后半生则需要学会顺其自然。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心
灵就会轻轻敲击我们;如果我们还是毫无意识,心灵就会用板砖拍打我们。
所以说,如果我们不是一直保持有意识的状态,如果我们不是一直在积极地改变自我,在中年
时期,内在压力的不断累积就会引发一场心灵的危机。危机是一种警告,危机也是一种召唤,
召唤我们走向更广阔的旅程。正如本书作者詹姆斯·霍利斯所说:“我们的心灵组织了这场危机,
制造了这种痛苦,因为伤害已经造成,改变必须发生。”
但愿每个人都能经历这场危机。除非你一直在经历调整和更新,否则,心灵就会以危机的形
式,逼迫你不断扩展自己的边界,发展出那些被压抑的人格侧面,直到你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此生短暂,请听从内心的召唤,活出圆满的生命。正如《多马福音》中所说:若将你内在的东
西活出来,它们必能拯救你;若不把你内在的东西活出来,它们必将毁灭你。当然,这里的“毁
灭”不是说让你真的死亡,而是说你辜负了自己的生命,你没有成为你自己。
听从内心的召唤,我组织了几位小伙伴来试译此书,作为一次练习。本书初稿分工如下:柳橙
(序言、第一章和第二章部分)、张慧强(第二章部分)、陈月星(第三章部分)、田雨婧
(第三章部分)、张琴(第四章、第五章)、王晓东(第六章),大约每个人承担了六分之
一。柳橙对全书进行了初次审校,郑世彦进行了二次审校、部分重译和统稿。童桐认真阅读了
部分章节并提出了宝贵意见。本书的出版离不开编辑老师的勤奋工作。在此,对大家的辛勤劳
动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鉴于精力与学识有限,书中错讹难免,敬请各位读者指正!
郑世彦
2022年5月4日
序言
为什么这么多人在中年遭遇如此多的挫折?为什么我们会把这种挫折当作一种危机?这种经历
的意义是什么?
中年危机,我更愿意称之为中年之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自己的机会,并提出了一个
看似可怕实则具有解放意义的问题:“除了我的过往以及我所扮演的角色,我究竟是谁?”当我们
发现自己一直在以虚假的自我生活,被不切实际的期望驱使着扮演一个“临时的”成年人格时,我
们就打开了第二个成年期的大门,将迎来我们真实的人格。
中年之路是一个重新界定和调整人格的机会,是介于首次成年的青春期和无可避免的老年及死
亡之间的过渡阶段。那些清醒地穿越了这段旅程的人,会为自己的生命赋予更多的意义。那些
没有清醒穿越的人,无论他们在外部世界表现得多么成功,仍然是自己童年的“囚徒”。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的精神分析实践对象主要是中年人;中年之路代表了一个极好的——尽管
常常令人痛苦——修正自我感(sense of self)的机会。因此,本书将会探讨以下这些问题:
●我们是如何获得特定的自我感的?
●有哪些变化预示着我们进入了中年之路?
●我们如何重新定义自我感?
●荣格的个体化 概念与对他人的承诺之间有何关联?
●有哪些态度和行为的改变能够支持个体化过程,并帮助我们穿越中年之路,渡我们脱离痛苦,
去往意义的彼岸?
深度心理学家认为,一个人的成长空间取决于他向内看和承担责任的能力。如果我们总是将自
己的生活看作由他人造成的困境,看成一个可以“迎刃而解”的问题,那么就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勇气,人格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荣格在一封1945年谈及个人成长的信中
写道:
(成长)的史书由三部分组成:洞察力、忍耐力和行动力。心理学只在第一部分被人需要,而
在第二、第三部分,道德力量将发挥主导作用。
许多人把生活当作一部小说。我们被动地从一页翻到另一页,以为造物主会在最后一页告诉我
们生命的意义。正如海明威曾说过的,如果主人公还没有死,只是因为作者还没写到结尾。因
此,无论有没有获得启迪,在人生的最后一页,我们都会死去。而踏上中年之路会让我们更加
清醒,能够为余下的篇章担负起责任,敢于为召唤我们的广阔生活而冒险。
无论读者身处生命的哪一阶段,所受到的召唤都一如丁尼生(Tennyson)在《尤利西斯》(
Ulysses )中所言:
长昼将尽,皓月徐升。内心召唤,耳边回响。
一起来吧,我的朋友。探新寻异,永不为晚。
第一章
临时的人格
我读五年级的时候,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老师买了一些本来用作潜艇望远镜的玻璃棱
镜。课前课后,我们会(透过玻璃棱镜)在过道上摸索着前进,有时会撞上墙壁或其他同学,
并乐在其中。我们着迷于究竟什么是现实,以及如何在如此弯曲的视角下找到道路。我很好奇
那些一直戴着眼镜的同学,是否会看得更清晰,或者是否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当我得
知眼睛里的晶状体也会折射光线时,我不得不进而怀疑,我们所看到的现实,是否完全取决于
晶状体。
年少时的觉察对现在仍有启发意义,我意识到无论现实情况本身如何,在某种程度上,它都离
不开我们看待它的视角。甫一出生,我们就被赋予了多种“视角”——遗传基因、性别、特定的文
化,以及迥异的家庭环境,所有这些奠定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多年后回头看,不得不承认,
生活与其说源于我们的真实本性,不如说源于家庭环境因素,这些因素直接塑造了我们的现实
感。甚至不得不承认,生活与其说源于我们的真实本性,不如说源于我们看待现实的视角。
心理治疗师有时会画一张代表家族情感的家谱图。家族几代人所延续的历史会揭示一些反复出
现的主题。虽然遗传倾向发挥了作用,但很明显,家族会将其对生活的看法代代相传。父辈将
“视角”传给子女,在这个折射的视角下,某些选择和结果被不停地重复。正如我们通过透镜看到
了这个世界的某些方面,我们也因此错失了这个世界的其他方面。
也许,让中年之路变得有意义的第一步,就是承认家庭和文化的“视角”失之偏颇,而我们正是基
于这些视角做出了选择并承受其后果。如果我们在另一个时空出生,有着价值观不同的父母,
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视角。我们被赋予的视角带来了一种受限制的生活,这种生活并不能体现我
们是谁,而是反映了我们如何习惯性地看待人生和做出选择。世世代代的人都被人类中心论所
吸引,试图捍卫自己的世界观,认为自身的视角比其他物种更优越。同样,我们也深信自己看
待世界的视角是唯一正确的,很少怀疑自身感知所受到的限制。
童年创伤
哪怕处于最被优待的童年期,生活体验也可能是痛苦的。我们原本在母亲的子宫内与其连为一
体,突然间,我们被粗暴地推入现实世界,开始了流放,同时也开始了追寻,以恢复失去的联
结。甚至宗教也可以被视为寻找与母体子宫联结的一种投射(religion来自拉丁文religio,意为
“人与神之间的纽带”;或者说religare,意为“重新联结”)。对许多人而言,由于贫困、饥饿和各
种虐待的影响,对世界的最初体验摧毁了他们对自我的感知。在童年时期,他们就封装了自己
的感觉、认知和情感,以免受到进一步的伤害。这些人长大变成了反社会者和精神失常者,充
斥于我们的监狱和街道。
可悲的是,对于因此遭受重创的人来说,成长和改变的前景是暗淡的;成长意味着要向充满痛
苦的世界敞开自己,而这太可怕了。我们大多数人作为神经质人格幸存下来,这意味着在孩童
的原始天性和所适应的世界之间的夹缝中生存。我们甚至可以得出结论,未经审视的成年人格
是由童年创伤引起的态度、行为和心理反射的集合,其主要目的是应对关于童年的机体记忆所
体验到的痛苦。这种机体记忆也可以被称作内在小孩(the inner child),我们的各种神经症代表
了无意识地进化出保护这个内在小孩的策略。(这里使用的“神经症”一词不是临床意义上的,而
是泛指我们的天性与文化适应之间的裂缝。)
童年创伤的性质可以概括为两个基本类别:(1)被忽视或遗弃的经历;(2)被生活压垮的经
历。
我们所谓的临时人格,其实是脆弱的儿童在应对存在性焦虑时采用的一系列策略。这些行为和
态度通常在五岁之前就已形成,并以一系列惊人的战略变化加以发展,其共同动机是自我保
护。
在儿童对自我和世界的认知过程中,虽然一些外部因素如战争、贫困或残疾起着重要作用,但
对我们生活的主要影响来自亲子关系的性质。人类学家描述了所谓的原始文化的认知过程,并
注意到它们如何复现了我们童年期的思维方式。这种文化的特点便是泛灵论和魔法思维。
原始文化和童年期的思维都认为世界充满了灵性,换言之,内在和外界的能量被认为是同一现
实的不同方面;这就是泛灵论思维。此外,这些原始文化推断——就像儿童所认为的那样——
内在现实和外部世界会相互影响;这便是一种魔法思维。就像原始人只能知道自己的洞穴或雨
林的边界一样,儿童也试图理解环境以提升自己的舒适度和扩大生存空间。(在柏拉图著名的
洞穴寓言中,人类理解的极限被比作囚禁,被囚者根据自己被困的洞穴墙壁上的影子得出关于
生活的结论。)因此,儿童得出的关于世界的结论来自一个狭隘的视角,不可避免的是片面和
偏颇的。儿童不可能说:“我的父母有问题,这对我产生了影响。”儿童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生
活是令人焦虑的,世界是不安全的。
为了尝试理解亲子环境,儿童会用三种基本的方式来解释他们的经历。
(1)儿童会直观地解释他们与父母之间感觉和情感的联结,以此作为对生活的总体感受。
生活是可预测的、滋养人的,还是不确定的、令人痛苦的、危险的?这种最基本的感知会影响
儿童信任感的形成。
(2)儿童把父母的特定行为内化为对自我的陈述。
由于儿童几乎不能客观地体验或者感知父母的内在现实,所以父母的抑郁、愤怒或者焦虑会被
解释为关于儿童的事实陈述。儿童会因此得出结论:“别人怎么看我,怎么对待我,我就是什么
样子。”(一个37岁的男子问他快要过世的父亲:“为什么我们从来都没亲密过?”父亲激动地
说:“你还记得你10岁时把玩具掉在了马桶里,我费了好大劲才把它弄出来吗?”接着还说了一大
堆类似的琐事。儿子走出医院的时候,感到无比自由。他一直认为自己不配得到父亲的爱;而
父亲通过揭露他的盲目,让他获得了新的自我形象。)
(3)儿童目睹了成年人与生活抗争的行为,不仅会内化这些行为,而且会内化他们关于自我和
世界的态度。
儿童会由此得出一个关于如何与世界相处的宽泛结论。(一个女孩的母亲常年焦虑,女孩耳濡
目染,直到去上大学时,她才开始质疑母亲的阴郁和悲观。大一时,她以为其他同学对世界的
糟糕一无所知。到了大二,她开始怀疑自己受困于母亲的焦虑,直到这时,她才开始以更轻松
的心态看待自己和世界。)
根据特定父母回应特定问题的有限经验,个体形成了关于自我和世界的认知。这种经验被一种
魔法思维过度个人化了,即“所有这些都是为我安排的,都是关于我的”;由此得出的结论也过于
笼统,因为人们只能根据已知的事情来评估未知。基于这样一个偏颇的开端——狭隘而充满偏
见,个体开始了一系列的感知、行为和反应,带着一种片面的眼光步入生活。
这种有缺陷的自我感知的特征,以及早期形成人格的策略,根据童年经历的性质而有所不同。
个体会从各种受伤的遗弃感或被压垮的感觉逐渐发展出一种无意识的、反射性的反应。
当一个孩子被压垮时,他会体验到“他者”(the Other)的巨大力量越过脆弱的边界袭来。由于缺
乏选择其他生存环境的能力,甚至缺乏客观地看待问题的能力,也缺少与他人进行经验对比的
依据,因此,儿童会做出防御性的反应,对环境变得极其敏感,并“选择”以被动、依赖或强迫来
保护脆弱的精神领地。儿童学会了千变万化的适应方式,因为对于一个相对无能的自我来说,
生活被视为具有先天的压倒性。例如,一个成年男性,由于母亲不断要求他超越父亲,他成了
一个“成功者”,成了一名技术高超的专业人士,但同时也养成了挥霍无度的习惯,而这导致他的
经济生活和情感生活最终破产。他的成年生活,看起来是一个理性、自由之人的选择,实际上
却是对“他人”压力的被迫服从,并伴随一种无意识的反叛,这种反叛把寻求失败作为一种消极的
抗议。
面对遗弃,也就是不充分的养育,儿童可能会“选择”依赖别人,或者终生沉迷于寻找更积极的
“他者”。例如,一个在童年时期被忽视的女人,后来不懈地追求一个又一个爱人,但总是在幻灭
和挫折中结束一段恋爱关系。一部分原因是她的情感需求把男人都吓跑了,另一部分原因是她
无意识地选择了情感疏离的男人。她的父亲在情感上对她付出甚少,以至于她反射性地形成了
一种自我毁灭的观念,认为自己“不会被给予,这是她应得的”,同时却又孤注一掷地希望下一个
男人能弥补她内心的亲子创伤。
这些创伤,以及内在小孩所采取的各种无意识反应,成为成年人格的重要决定因素。儿童无法
形成自由表达的人格;相反,童年经历塑造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角色。因此,由于童年的创
伤,成年人格与其说是一系列的选择,不如说是对早期经历和生活创伤的反射性反应。
个人情结
荣格心理学认为,这种反射性的、充满情绪的反应与个人情结的性质有关。情结本身是中性
的,尽管它携带着一种与经验的、内化的形象有关的情感。早期经验的强度越大,或者重复的
时间越长,这种情结在我们生活中的影响就越大。情结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成长史。问题不在于我们有情结,而在于情结占有了我们。某些情结在保护人类机体方面很有
用,但有些情结会干扰我们的选择,甚至可能主宰我们的生活。
情结或多或少总是无意识的,它们充满能量并自主运行。尽管它们通常由当前的事件所激活,
但内在运作机制是相似的,好像在说:“这以前什么时候发生过?”当前的刺激可能与过去发生的
事情只有一点相似,但如果是在情感上相似,那么之前引发的反应就会被触发。很少有人在
性、金钱和权力等问题上没有情绪反应,因为它们通常与早期的重要经历有关。
在所有情结中,最具影响力的是那些内化的养育经验,我们称之为母亲情结和父亲情结。父母
通常是我们遇到的两个最重要的人。他们给了我们血肉之躯,是我们出发的港湾。我们耳濡目
染了他们对待我们的方式,以及他们的生活策略。例如,海明威所塑造的一系列硬汉形象,实
际上是那个来自伊利诺伊州橡树园的小孩的过度补偿,因为母亲让他对女人心生恐惧——她想
要他变成一个女孩,甚至在他成年后,对他在情感上仍横加干涉。卡夫卡则被他强大的父亲所
控制,以至于他认为世界本身就是强大、疏离和冷漠的。这并不是说这些人和其他人的创造算
不上伟大的艺术,他们当然创造了伟大的艺术,但他们创造的形式和个人动机是为了克服、补
偿——如果有可能的话——超越原初的父母情结。
因此,我们都带着过去经历的痕迹无意识地生活。即使是在幼儿时期,我们固有的天性和社会
化的自我之间就已出现会不断加深的裂痕。两个世纪前,华兹华斯(Wordsworth)在《不朽颂》
( Ode on 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 )中写道:
在我们幼年,天堂触手可及!
但囚牢的阴影逐渐笼罩
成长中的男孩……
最终,成年人目睹天堂的消逝,
消失在平凡的日子里。
在华兹华斯看来,社会化就是一个与人们先天的自我感逐渐疏远的过程。在尤金·奥尼尔
(Eugene O’Neill)的戏剧《长夜漫漫路迢迢》( 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中,一位母亲
更是悲惨地描述了这一情况:
我们对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无能为力。它们在你有所意识之前就已经结束。一旦它们结束,就会
推动你做其他事情,直到最后,所有事情都横亘于你自己和你想成为的人之间,你便永远失去
了真实的自我。
大约2500年前,古希腊人就意识到了这种分裂。他们创作的悲剧人物并不邪恶,尽管他们有时
可能会做坏事;实际上他们是被自己不了解的东西所束缚。hamartia这个词(有时被翻译成“悲剧
性缺陷”,但我更喜欢译作“片面的视野”)代表了他们做选择的视角。在无意识力量和反射性反
应的累积过程中,人们做出选择,后果随之而来。这些残酷的戏剧所表达的生命悲剧感表明,
我们所有人——个人戏剧中的主角——都可能过着悲剧性的生活。我们可能会被自己不了解的
东西所驱使。希腊悲剧的解放性力量在于,英雄通过苦难获得了智慧,也就是说,内在真实
(性格)和外在真实(神灵或命运)之间的关系得到修正。只有当我们没有意识到自主情结的
作用,以及我们的本性与现实选择之间的裂痕日益加深,我们的生活才会沦为悲剧。
大多数中年危机都是由这种分裂的痛苦所引发的。内在的自我感和后天的人格之间的差距变得
巨大,以至于产生的痛苦无法再被抑制或补偿。心理学家称这种情况为“代偿失调”
(decompensation)。一个人继续使用旧的态度和策略行事,但它们已不再有效。事实上,中年
痛苦的症状是值得欢迎的,因为它们不仅代表着深藏于后天人格背后的本能自我,而且代表了
迎接新生的强烈要求。
中年之路的出现,发生在后天人格和自性 要求之间的可怕冲突中。经历这种情况的人通
常会惊慌失措地说:“我都快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实际上,过去的人格将被未来的人格所取代。
过去的人格必须死亡,难怪会有如此巨大的焦虑。个体在心理层面被召唤,泯灭旧我以迎接新
生。
这种死亡和重生本身并不是终点,而是一条通道。要想更多地实现自己的潜能,获得成熟的活
力和智慧,就必须穿过这条通道。因此,中年之路代表了一种内在的召唤,召唤我们从临时的
人格走向真正的成年,从虚假的自我走向真实的自我。
第二章
中年之路的出现
中年之路是一个现代概念。在20世纪人类寿命突然延长之前,用托马斯·霍布斯的话来说,生命
是“肮脏、野蛮和短暂的” 。医疗保健系统的变革,使20世纪初的平均预期寿命达到了40
岁。只要去早期美国的墓地随便走走,就能看到一排排孩童的坟墓,他们死于鼠疫、疟疾、白
喉、百日咳、天花和斑疹伤寒等,而现代儿童通过接种疫苗避免了这些疾病。(我记得我所在
的那个大约10万人口的城市,曾因为小儿麻痹症暴发而停摆,只能进行基本交易,无法逛公
园、看电影和游泳。)
也许除了寿命的限制,那些活得更久的人还会受到社会体制的巨大影响,比如教会、家庭和社
会习俗。(小时候,就有许多离婚的人用同样的语气对我说,“我好像成了一个杀人犯”。)性别
定义太过清晰甚至绝对,这同时伤害了男人和女人。家庭和民族传统给我们提供了根基感或社
群感,但同时也会滋生近亲繁殖和阻碍独立。女孩被期望嫁人,相夫教子,成为维系和传播价
值体系的中心。男孩被期望长大,接替父亲的角色,成家立业,同时支持和拥护价值观的延
续。
许多传统价值观在过去甚至现在都值得称赞。但是,考虑到这些体制对人们的殷切期望,沉重
的精神暴力也会同时存在。我们不应该在不了解双方灵魂的情况下,自动地为50年的婚姻历程
喝彩。也许他们害怕改变,害怕诚实和受苦。那些满足了父母期望的孩子,可能在成长过程中
失去了自己的灵魂。长寿和价值观的复制带来的并非全是好处。
在当今时代之前,人们很少被告知要自我实现,也不知道自我作为神秘且独特的存在,其价值
观可能不同于亲朋好友。即使是现在,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相当异端的观念。但现代精神的最
大特点是,心理力量已经从传统组织向个人急剧转移。现代世界的意义已经从王权和宗教转移
至个人身上,这比任何一个变化都重要。大一统的意识形态逐渐失去了精神能量,并让现代人
处于孤立的状态。正如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一个多世纪前所观察到的,我们徘徊在
“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亡,另一个无力重生”。
不管是好是坏,精神引力已经从社会体制转向了个人选择。如今中年之路的存在,不仅因为人
们活得够长,还因为在当代社会,大多数人都接受了个人对自己生活的主宰。
内在压力与预警
如前所述,中年之路以一种自下而上的内在压力作为开端。就像地壳板块移动,相互摩擦、累
积压力,然后爆发地震一样,人格层面的板块也会发生碰撞。此时,个体获得的自我感,连同
其内置的观念和情结以及对内在小孩的保护,开始与寻求实现的自性之间发生摩擦。
这些波动可能会被防御性的自我意识所消除,但压力却在不断累积。通常,在人们意识到危机
之前,各种迹象和症状就已经出现了——抑郁、酗酒、吸食大麻,以促进性爱、出轨、反复跳
槽,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否认、忽视或摆脱内在的压力。从治疗的角度来看,这些症状是值得欢
迎的,因为它们不仅是指向伤口的箭头,还显示出一个健康的、自我调节的心灵在运作。
荣格观察到,神经症“最终必须被理解为灵魂尚未发现其意义的痛苦”。 这并不意味着可
以实现没有痛苦的生活,而是说痛苦已经降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必须找到它的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神学家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因反对希特勒而殉
道。他从弗伦斯堡集中营偷偷带出了一些信件和文章。在其中一篇文章中,他苦苦思索一个显
要的问题:上帝是否以某种方式造就了集中营及其可怕的生存环境?他意识到自己无法回答这
个问题,但他明智地得出结论:他的任务在于面对并穿越恐惧,找到上帝在这种情境下的旨
意。
因此,有人可能会说,在承受内心压力的过程中,我们可能无法发现生命的终极意义。但是,
我们必须找到内心冲突的意义,找到中年之路上必然的人格碰撞的意义。在这种命中注定的碰
撞中,在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经历中,新的生命诞生了。我们被邀请重获自己的生命,更加
清醒地生活,并从痛苦中获得意义。
当我们在意识层面受到剧烈冲击时,就会在中年之路上觉醒。我看到许多人在遭遇重大疾病或
丧偶时,开启了中年之路的旅程。但也有人即使到了五六十岁,仍然保持着浑浑噩噩的状态,
被个人情结或集体价值观所支配,以至于中年之路的问题被挡在了门外。(下一章将给出具体
例子。)
中年之路与其说是一个时间事件,不如说是一种心理体验。希腊语中代表“时间”的两个词——
chronos和kairos——体现了两者之间的差别。chronos是指连续的线性时间,kairos则是指深度上
的时间。例如,对于美国人而言,1776年不只是岁月长河中普通的一年,它还决定了美国在以
后每一年的发展。当我们不得不把生命看作超越线性的岁月时,中年之路就出现了。一个人处
于无意识状态的时间越长(这在我们的文化中很容易做到),他就越有可能把生命看作一连串
的时刻,通向某个模糊终点,其意义将在最后变得清晰。当一个人在意识层面受到冲击,垂直
维度与生命的水平维度相交时,人生将以一种深度的视角被呈现:“我是谁?我将何去何从?”
当我们不得不重新询问关于意义的问题时,中年之路便被开启了;这个问题曾经萦绕在孩子的
脑海里,但逐渐被岁月抹平了。当我们踏上中年之路时,会被要求面对以前遮掩的那些问题。
身份认同的问题再次袭来,人们再也无法逃避责任。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问:“除了我的过往以
及我所扮演的角色,我究竟是谁?”
由于把生命历程视为一种自动延续的存在,所以我们很容易被过去所定义和支配。我们已经习
惯于制度化的角色,例如配偶、父母、工薪阶层,所以我们将自己的身份投射到这些角色上。
由此,詹姆斯·艾吉(James Agee)在他的自传体小说开头写道:“我们现在谈的是田纳西州诺克
斯维尔的夏夜,当我住在那里时,成功地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孩子。”
所有的宏大问题都由曾经是孩子的我们提出,当时我们静静地观察这些大人,或者深夜躺在床
上,觉得活着既有点害怕又有点兴奋。但学校教育、父母教育和文化适应过程的权重逐渐磨灭
了孩子的敬畏感,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期望和文化规则。在序言结尾,艾吉回忆了他被大
人抱上床睡觉的情景:“(他们)把我当作家里一个至亲至爱的人,但是(他们)不会,现在不
会,永远也不会告诉我,我是谁。”
这些宏大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价值和尊严。如果我们忘记了它们,就会受限于社会环境,
落入平庸,最后陷入绝望。如果我们“有幸”承受了足够多的痛苦,就会进入一种“勉强的”意识状
态,那些问题将再次回到脑海。如果我们足够勇敢,足够关心自己的生活,就可能会穿越痛
苦,找回属于自己的生活。
虽然有些人通过灾难性的事件才会经历这场命中注定的相遇,但他们实际上很早就收到了预
警。脚下的地面轻微地颤动,一开始很容易被忽视。地震预警是内在压力的先兆,在我们完全
意识到它们之前就一直存在。
我认识一个人,在他28岁的时候,已经实现了他所想要的一切:获得了博士学位、组建了家
庭、出版了自己的书、拥有很好的教职。多年后他意识到,第一次波动的征兆是他感到无聊和
乏力。他做了大多数人所做的事,大同小异。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写了更多的文章,生了更
多的孩子,在更好的岗位上教书。所有这些活动都可以被合理化,因为它们在表面上是富有成
效的,代表了典型的职业阶梯,我们很容易将自己的身份投射到这个阶梯上。当他37岁时,不
断累积的深层抑郁爆发,他经历了近乎彻底的衰弱和意义丧失。他辞掉了工作,离开了家庭,
在另一个城市开了一家维多利亚时代的冰淇淋店。他是否过度补偿了之前的生活?他是否压制
了中年之路召唤他回答的那些有益的问题?或者他靠误打误撞找到了度过下半生的最佳方式?
也许只有时间能证明一切,只有他自己能给出答案。
这种波动通常在近30岁时就会出现,但在那时很容易就被人们忽视。生活被琐事填满,前路向
我们招手,一切变化太快,投入更多的精力总是很容易,于是我们忽略了这些征兆。一个人必
须得绕着一个轨道走好几圈,才能知道它是圆形还是椭圆形。只有当一个人不止一次经历某种
模式时,才会觉察到模式的存在,以及它的代价和副作用。回溯往事时,我们常常对这些错
误、天真和投射感到懊恼,甚至是羞耻。但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成年期:充满疏忽大意、羞
怯、压抑和错误的假设,而且总是受到童年经历的影响。如果一个人没有大步前进、犯下错误
甚至碰壁,那么他可能会一直是个孩子。从后半生的角度来回顾生活,我们需要理解和原谅不
可避免的无意识罪过;但如果在后半生还不够清醒,那就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中年之路的召唤有着明显的特征和体验(详见下文)。它们自主地发生,独立于自我意志之
外。它们日复一日地悄然生长,惊扰了内在小孩的睡眠,而后者把确定和安全凌驾于一切之
上。但中年之路代表了生命不可避免地走向未知的实现,这是一个服从于天性及其神秘的目的
论 的过程,几乎不关心神经紧张的自我的想法。
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如前所述,童年的特点是魔法思维。儿童的自我还没经过战斗考验,还没有明确的边界。客观
的外部世界和内心的愿望世界常常混淆不清。愿望当然可以实现,只是多少的问题。它们代表
了儿童相信自己是世界中心的自我陶醉。这样的思维是膨胀的和妄想的,但在儿童身上却是完
全健康和美妙的。“我会身穿白纱嫁给王子。”“我会成为宇航员。”“我会成为著名的摇滚明星。”
(试着回忆你童年时的魔法愿望,并思考生活对它们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儿童的魔法思维
认为:“我是不朽的。我不仅会变得富有、受人敬仰,而且会远离衰老和死亡。”这种思维会持续
到十岁左右,但强烈程度不如从前。当其他孩子都不以为然的时候,个人优越感和特殊性的幻
觉就会受到沉重打击。(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想我可能会取代乔·迪马吉奥,成为纽约洋基
队的中外野球员。唉,谁知神灵却把必要的技能给了米奇·曼托。 )
经过青春期的痛苦和困惑,儿童的魔法思维被磨平了些许棱角。然而,未经考验的自我依然存
在,并表现出人们现在所谓的英雄思维,其特点是更强的现实主义,但仍然充满相当大的期
望,把辉煌成就的幻想投射于未来。人们可能会看到父母婚姻的残局,并得出结论:“我比他们
懂得更多,会做出更明智的选择。”人们可能仍然期望成为首席执行官,写出伟大的小说,成为
了不起的父母。
英雄思维是有用的,因为如果我们害怕考验或感到失望,谁还会踏上成年的旅途?我还没有被
邀请在毕业典礼上演讲,但如果有人邀请我,尽管这种演讲通常令人讨厌,我仍不忍心说出真
相。谁能忍心对殷切且充满希望的面孔说:“几年后,你可能会讨厌自己的工作,你的婚姻会陷
入泥潭,你的孩子会让你心烦意乱,你可能会经历非常多的痛苦和人生困惑,乃至你想要为此
写一本书。”谁能对那些天真的、准备前往梦想星球的人这样做呢?即使他们将会像自己的父辈
一样,在令人困惑和布满荆棘的路上蹒跚而行。
英雄思维,连同它的希望和投射,几乎没有被世界的运作方式所影响。这种思维帮助年轻人离
开家庭、投入生活,他们必须如此行动。在法国大革命开始时,年轻的华兹华斯横穿英吉利海
峡,激情地写道:“年轻和远方就是天堂。” 而几年之后,他将痛恨拿破仑政权窃取了革
命的成果。饱经战火的T.E.劳伦斯 则看到他荒漠般的希望被和平会议上的老人们出卖。
尽管如此,年轻人还是出发了,就像命中注定那样,跌倒再爬起来,磕磕绊绊地走向与未来的
约定。
当童年的魔法思维和青春期的英雄思维,与一个人所经历的生活格格不入时,他就踏上了中年
之路。那些35岁以上的人遭遇了大量的失望和心痛,其程度甚至超过了青春期的暗恋破灭。任
何一个中年人都见证了投射、希望和期待的坍塌,并体验到天赋、智力以及勇气本身的限制。
因此,中年之路的思维特征,可以通俗地被称为现实主义。现实思维给了我们洞察力。希腊悲
剧表明,主人公最后可能会更加富有,但却会走向毁灭,因为他或她回到了与诸神的正常关系
中。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并非一个坏人;他是一个傻瓜,因为他不知道爱为何物。他对奉承
的需求蒙蔽了他;他得到了荣华富贵,但付出了肉体和精神上的代价。
因此,生活召唤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解决年轻时的狂妄和膨胀,并教导我们区
分希望、知识和智慧。希望通常基于可能发生的事情;知识是有价值的经验之谈;而智慧总是
使人谦卑,永不膨胀。例如,苏格拉底的智慧就是他知道自己一无所知(但他的“一无所知”远胜
过古往今来智者或学者的“确信”)。
中年的现实思维有其必要的目标,那就是恢复平衡,使人与宇宙之间重新建立谦卑而有尊严的
关系。我有一个朋友曾经说过,他知道自己的中年之路是何时开启的。它就像一个想法,脑子
里的一句话,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这个想法就是:“我的生活永远不会完整(无缺),只有各
个部分。”他的心灵在向自己宣布,年轻时膨胀的期望是实现不了的。有人可能觉得这样的认识
是一种失败,但有人却会被触动并提出下一个问题:“那么,我需要做些什么呢?”
身份变化
如果有机会度过完整的一生,人们会经历一系列不同的身份。通过稳定的生活来应对存在性焦
虑,这是自我(the ego)的自然计划。但是,生命的本质显然会预设并要求改变。大约每七到十
年,一个人的身体、社会和心理层面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例如,回想一下你在14岁、21岁、
28岁和35岁时的不同状态。虽然每个人都沿着各自的生命轨迹前行,但我们确实会经历一些共
同阶段。我们可以对这些周期进行概括,并为每个阶段确定一个社会和心理层面的议程。尽管
自我傲慢地认为它掌管着生命,其愿景将持续多年不变,但显然有一个自主的过程,一个不可
避免的辩证过程,它将带来反复的死亡与重生。承认变化的必然性并与之相伴,是一种美妙且
必要的智慧,只是自我有时会拼命保全已完成的东西。
一些年前,盖尔·希伊(Gail Sheehy)的《过渡》(Passages)一书很受欢迎,这证明了周期性变
化这一主题的重要性。然而,正如米尔恰·伊利亚德、约瑟夫·坎贝尔 以及其他社会学家
或人类学家所指出的,现代文化已经遗失了神话的地图,而这一地图有助于我们在更大的背景
中定位自己。如果没有神灵的部落愿景,没有共享的精神网络,现代人就会在没有指导、没有
榜样和没有援助的情况下,漂流到各个人生阶段。因此,中年之路——它呼唤死后重生——往
往是在恐惧和孤立中经历的,因为没有过渡仪式(rites of passage),也没有来自同样漂泊不定
的同龄人的帮助。
除了人生的许多次要阶段(每一阶段都要求某种形式的“死亡”)之外,人生可以分为四个较大的
阶段,分别界定了四种不同的身份。
第一个阶段即童年,最主要的特征是自我依赖于父母的现实世界。身体上的依赖显而易见,但
精神上的依赖,即孩子对家庭的认同,甚至更为重要。在古代文化中,成年随着青春期的到来
而开启。无论各部落在地理上、文化上和意识形态上有多么不同,它们都演化出了有意义的过
渡仪式,使成员从童年的依赖走向成年的独立。
尽管进入成年的方式各不相同,但传统的过渡仪式通常包括六个阶段。简单来说,它们是:
(1)与父母分离,通常经过仪式性的绑架 来实现;(2)“死亡”,童年的依赖性被“杀
死”;(3)重生,无论是否成熟,个体会被赋予新的生命;(4)教导,告诉这个“新人”关于部
落的原始神话,给予他精神上的定位,告诉他这个部落的特权和责任,以及有关狩猎、育儿等
知识——这些是成年生活所必需的;(5)磨难,最常见的是进一步分离,以便“新人”了解到自
己有一种内在的力量来应对外界的任务;(6)回归,一个人带着扮演成熟角色所需要的知识、
神话基础和内在力量,重新进入这个社群。通常情况下,“新人”甚至会被赋予一个新的名字,以
适应这种彻底的转变。
成年仪式希望实现的是:与父母分离;传递部落的神圣历史,以提供精神根基;为成年生活的
责任做准备。在现在的文化中,显然缺少进入成年的有意义的过渡仪式,因此许多年轻人延伸
了他们的依赖性。我们的文化如今如此多样化,无论如何已经失去了它的神话根基,只能传递
20世纪对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和自恋的信仰,外加一些计算机技能,而这一切都无法提供救
赎,无法提供与大地及其伟大律动的联系,也无法为我们的旅程提供深度和意义。
第二个阶段开始于青春期。但是,没有传统的过渡仪式,年轻人会面临精神上的困惑和自我的
不稳定。新生的自我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容易受到同龄人和流行文化的影响,而这两者皆由其
他困惑的青少年组成。(在北美,许多治疗师认为,青春期大致从12岁延伸到28岁。在当了26
年的教授后,我得出结论:大学的主要文化作用是充当一个容器,让年轻人充分巩固自我,以
便更实质性地摆脱对父母的依赖。事实上,他们对父母的爱和厌恶大部分都转移给了他们的母
校。)
所以,第二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巩固自我,年轻人由此获得足够的力量离开父母,走向更广阔
的世界,为生存和实现欲望而奋斗。这个人必须对世界说:“雇用我!嫁给我!相信我!”然后证
明自己的价值。有时,一个人到了中年,仍然没有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摆脱依赖,走向世界。
有人可能仍然和父母住在一起,有人可能缺乏必要的个人力量和自我价值来建立一段关系,还
有人可能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决心来完成工作任务。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的身体可能在线性时
间上到达了中年,但他们在深度时间上仍然处于童年。
我大致上把12岁到40岁这段时间称为第一个成年期。年轻人在内心深处知道他缺乏明确的自我
感,只能试着像其他大人那样行事。一个人觉得言行举止像父母一样,或者反其道而行之,他
就会成为一个成年人,这是一种可理解的错觉。如果一个人有了工作,结了婚,为人父母并成
为纳税人,他会认为成年是自然而然的。事实上,发生的情况是,童年期的依赖性部分隐匿起
来,被投射到成年期的角色上。这些角色就像一条条平行隧道。从青春期的困惑中走出来,人
们假设这些角色会确认自己的身份,提供满足感,并消除对未知的恐惧。第一个成年期,虽然
事实上可能贯穿一个人的一生,但却是一个临时性的存在,缺乏深度和独特性,难以使这个人
成为真正的个体。
这些角色的隧道长短不一。只要被投射的身份以及对它们的依赖仍然有效,这些隧道就会延续
下去。一个30岁的人,工作小有成就,成了家,正打算要第二个孩子,你几乎不可能告诉这个
人,说他仍然处于延长的童年期。父母情结和社会角色的权威,足够吸引一个探索现实世界的
人的投射。如前所述,自性——每个人内心召唤回归自身的神秘过程——经常通过症状来表达
自己,如精力减退、抑郁、突然发怒或过度消费,但投射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可能将
旅程中更大的问题束之高阁。这是多么可怕啊,当投射消失后,这个人再也无法避免自性的暴
动。然后,人们必须承认自己无能为力,失去了控制。实际上,自我从来就不在控制之中,而
是被父母和集体情结的能量所驱动,被投射的力量所支撑——这些投射指向文化为即将成年的
人提供的角色。只要这些角色具有规范的力量,只要这些投射起作用,个体就成功阻止了与内
在自性的约定。
第三个阶段即第二个成年期,是在一个人的投射消解后启动的。背叛感、期望落空、空虚感和
丧失意义,伴随着投射的消解而出现,形成了中年危机。然而,正是在这个危机中,一个人有
机会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超越父母、父母情结和文化制约的决定论。可悲的是,心灵的退行
力量,以及对权威的依赖,往往使一个人受制于这些情结,从而冻结了发展。在分析老年人时
——他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丧失和预期的死亡——显然会遇到两种情况。对有些人来说,余下
的生命仍然是一个挑战,仍然值得好好奋斗;而对另一些人来说,生命充满了苦涩、遗憾和恐
惧。前者无一例外都经历了一些早先的挣扎,体验到了第一个成年期的“死亡”,并接受了对自己
生活的更大责任,他们在最后几年里更有意识、更清醒地活着。那些避免了第一次“死亡”的人则
为第二次死亡所困扰,害怕自己的生活没有意义。
第二个成年期的特征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更充分地讨论。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当临时身份
被抛弃、虚假的自我死亡,第二个成年期才可能开启。这种丧失带来的痛苦可能会被后来的新
生活所补偿,但身处中年之路的人们,可能只会感觉到死亡。
第四个阶段,即走向死亡,包括学习面对死亡的神秘,这也将在后文中进行讨论。不过在第二
个成年期,接受死亡的现实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个成年期“死亡”带来的好消息是,人们可以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还有第二次机会,可以重
获遗留在童年纯真时刻的东西。在与“死亡”的交锋中,我们了解到,个人的选择至关重要,我们
的尊严和深度恰恰来自海德格尔所说的“向死而生”。 海德格尔对我们本体论处境的定义
并非病态,而是承认了天性的目的论过程,承认了生与死的辩证。
另一种看待这些身份变化的方法,是对它们的不同轴心(axes)进行分类。在第一个身份中,也
就是童年,运作的轴心是亲子关系。在第一个成年期,轴心位于自我和世界之间。自我,即一
个人的意识存在,努力将自身投射到现实世界,并在现实世界中创造一片天地。童年期的依赖
已被驱赶到无意识中,或者投射到各种角色上,个体的主要任务是适应外部世界。在第二个成
年期,即中年之路的途中以及之后,轴心连接着自我和自性。自我想当然地认为它无所不知,
并操纵着一切。当它的“霸权”被推翻之后,转而谦卑的自我便开始与自性对话。自性或许可以被
定义为有机体的目的论过程。这是一个我们永远都无法理解的奥秘,但它的展开会提供一幅壮
阔的景象,超出我们短暂一生通常所能体现的。
第四个轴心是自性—上帝,或者说自性—宇宙。这个轴心被宇宙的奥秘包围,它超越了个人所
能体现的神秘。如果我们与宇宙剧本没有某种关系,就会被限制在短暂、肤浅和乏味的生活
中。由于大多数人所继承的文化几乎都没有提供神话地图,将自我安置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中,
因此,个人就更有必要扩大自己的视野。
这些移动的轴心勾勒出了灵魂的巨变。当我们不由自主地从一个轴心跳至另一个轴心时,就会
产生困惑,甚至恐惧。但人性的本质,似乎迫使每个人在这出伟大的戏剧中,走向越来越宏大
的角色。
撤回投射
投射是心灵的一个基本机制,指内心无意识的东西会被投射给外界事物。(projection这个词来
自拉丁文pro+jacere,意思是“扔到面前”。)荣格曾写道:“投射的一般心理成因总是被激活的无
意识在寻求表达。”
在其他地方,他说道:“投射绝不是人为的;它发生了,它就在那里。在我身外的黑暗之中,我
发现了一种内部的或心理的生活,那是属于我的生活,但我没有认出它来。”
面对可怕的外部世界和未知的内心世界,我们自然倾向于将焦虑及其解决全部投射到父母身
上,相信他们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当我们不得不离开父母时,往往将知识和力量投射给
公共体制、权威人物和各种社会角色。我们认为,像大人们一样行事就能成为大人。刚步入成
年期的年轻人不可能知道,大人有时不过是拥有高大身躯和重要角色的孩子。他们当中一些人
甚至相信自己就是这些角色本身。那些不那么膨胀的人更能意识到自己的不确定性,而那些身
处或走过中年之路的人正在经历投射的消解。
在许多可能的投射中,最常见的是那些对婚姻、教养和职业等公共体制的投射。关于投射在婚
姻中的作用,后文会有更多讨论,但也许没有哪种社会结构像婚姻一样,承担了如此多无意识
的包袱。在婚礼圣坛上,很少有人意识到自己的期望有多么巨大。没有人会大声说出那些巨大
的期望:“我希望你让我的生活有意义。”“我希望你永远在我身边。”“我希望你能读懂我的心
思,预知我所有的需要。”“我希望你能包扎我的伤口,填补我生命中的缺憾。”“我希望你能让我
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治愈我受伤的灵魂。”就像在毕业典礼演讲中不能说出那些真相一样,这些
隐藏的议程也不能在婚礼圣坛上说出来。如果人们承认了这些要求,必然会因为它们不可能实
现而感到尴尬。大多数婚姻在这种期望的重压下破裂,而那些坚持下去的婚姻往往伤痕累累。
爱情以距离、想象和投射为食,婚姻则以邻近、在场和共通为饮。
罗伯特·约翰逊在《他》这本书中指出,大多数现代人不再熟悉古老的神话系统,把灵魂的需要
转移到了浪漫爱情上。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从童年起就携带着心爱之人的形象,并投射
到一个能够接受这些无意识材料的人身上。正如波斯诗人鲁米(Rumi)写道:
从第一次听说爱情故事起,
我便开始寻找你,
不知这有多盲目。
爱人不是最终在某处相遇,
而是一直存在彼此心里。
每天和另一个人生活在一起会自动消磨掉投射。我们将灵魂交付给这个人,在亲密关系中向这
个人敞开心扉,最后却发现他和我们一样,只是一个凡人,会害怕,会有需求,也会投射出沉
重的期望。任何一种亲密关系都承载着巨大的负担,因为它们最可能映射了那个“亲密他人”,也
就是曾经的父母。我们并不希望自己的伴侣如同父母,毕竟,我们花了那么多精力远离父母。
但是,当心爱之人变成那个“亲密他人”,同样的需求和动力被投射到他身上,我们根本无从意
识。因此,人们最终会选择与父母非常相似或不同的人,也就不足为奇了,原因就是父母情结
一直在影响着他们。当人们手持《圣经》宣布结婚需要离开父母时, 这比他们想象的要
困难得多。因此,一个人对“亲密他人”的滋养、赋权和疗愈的投射,只能部分撤回。无声的希望
与平凡的现实之间的鸿沟,给中年之路带来了相当大的痛苦。
另一个受到强烈投射的角色是父母身份。大多数人都相信自己知道什么对孩子是好的。我们确
信自己可以避免当初父母所犯的错误。但不可避免的是,我们都会将自己未曾实现的生活投射
到孩子身上。荣格观察到,孩子必须承受的最大负担就是父母未曾拥有的生活。望子成龙、望
女成凤已经见怪不怪,但父母甚至潜藏着对孩子成功的嫉妒。因此,源源不断的信息——公开
的和隐蔽的——轰炸着孩子。这个孩子将承受父母的愤怒和伤害,并遭受各种各样的操纵和胁
迫。最糟糕的是,我们可能会无意识地期望这个孩子能让我们开心,让我们的生活充实,让我
们更上一层楼。
当我们踏上中年之路时,孩子们已经到了青春期,他们满脸青春痘,闷闷不乐,桀骜不驯,通
常和我们曾经在自己父母眼中一样令人讨厌,他们愤怒地抵制我们的投射。如果我们意识到,
父母情结作为个体成长之路上的障碍有多么难对付,就会知道,那些青少年拒绝成为父母的延
伸是正确的。然而,为人父母的期望与家庭生活摩擦之间的落差,给中年之路上的人们带来了
更深一层痛苦。只有当我们想起自己希望父母知道的事情,即孩子只是通过我们的身体和生活
走向他或她自己生命的奥秘,这种失望才会有所减轻。当中年父母能够接受这一点时,教养的
矛盾心理才会得到恰当的视角。
弗洛伊德认为,工作和爱是心理健康的首要条件。我们的工作代表了一个产生意义的重大场
合。如果正如梭罗很久以前指出的那样,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中 ,那么可以肯
定的一个原因是,对许多人来说,工作使人士气低落,让人意志消沉。即使是那些已经获得梦
寐以求的职位的人,也常常会莫名其妙地感到厌倦。我认识很多学生,他们之所以主修商科或
者成为程序员,只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或其他长辈,因为这个浮躁的社会,似乎要求他们这样
做。无论是那些实现了自己欲望的人,还是那些被迫满足他人需求的人,通常都会对自己的职
业渐生厌倦。对于每一个在职业阶梯上雄心勃勃的人而言,背后都有一个精疲力竭的高管在渴
望一种不同的生活。
一个人的职业,就像婚姻和教养一样,成为以下投射的主要载体:(1)身份的投射,人们通过
对专业知识的明确掌握来确认身份;(2)滋养的投射,一个人将被富有成效的工作所滋养;
(3)超然性的投射,一个人通过接连不断的成就来克服精神上的渺小。当这些投射被消解,当
一个人对使用自己精力的不满已无处安放时,他或她就踏上了中年之路。
婚姻越传统,性别角色越固定,伴侣就越有可能听到另一种声音的召唤。丈夫已经抵达职业的
顶峰,公司对他而言只是个停车场,他很乐意放慢速度或者退休。妻子把自己奉献给了家庭生
活,感觉受到了欺骗,既没有得到赏识,也没有充分发展,她希望回到学校或者重新找工作。
对于男性来说,中年时期的工作瓶颈往往会导致抑郁,以及希望和雄心的破灭。而重新开始工
作的女性,常常会对自己的胜任力或竞争力感到焦虑。
同样,这里有坏消息,也有好消息,还有其他东西。坏消息是,每个人都耗尽了投射身份的主
要领域,并希望有一个新的开始。好消息是,这种不满可以带来真正的更新,个人潜力的另一
面会被挖掘出来,为双方都带来利益。更坏的消息是,一个投射可能只是被另一个投射所代
替;但即便如此,人们也会越来越接近与自性的约定。如果夫妻中的一方感受到了变化的威
胁,并加以抵抗,那么毫无疑问另一方会感到愤怒和压抑。在婚姻的炼狱中,变化不一定朝向
更好的方向,但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否则,婚姻可能无法存续,特别是如果它阻碍了任何一方
的成长。
还有,一个在中年必须消解的投射,与父母作为象征性保护者的角色有关。通常人到中年时,
父母的能力在衰退,或者已经离开人世。即使与父母的关系疏远或有隔阂,父母仍然象征性地
存在,提供了一个无形的精神屏障。只要父母的形象还存在,就会有一个心理上的缓冲,抵御
不可知且危险的世界。当这个缓冲被移除时,人们常常会感受到一丝存在性焦虑。一位40岁出
头的患者在她70多岁的父母决定友好离婚时,遭受了惊恐发作。她知道,他们的婚姻从来都不
幸福,但它仍然是她抵抗浩瀚宇宙的无形盾牌。此刻,在他们最终离世之前,离婚打破了这个
无形的屏障,这让她在中年平添了一份孤独和被遗弃感。
虽然有许多其他类型的投射无法在第一个成年期存活下来,但是对于婚姻、教养、职业以及父
母作为保护者的期望丧失,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在《荣格心理学中的投射和重新聚集》( Projection and Re-Collection in Jungian Psychology )一
书中,玛丽-路易斯·冯·弗朗茨(Marie-Louise von Franz)指出了投射的五个阶段。 第
一,人们确信内在经验(无意识的)就是外在现实。第二,人们逐渐认识到被投射形象和现实
之间的差异(例如,一个人在爱情中冷静下来)。第三,人们被要求承认这种差异。第四,人
们被迫得出结论,自己最初在某种程度上错了。第五,人们必须在自己内心寻找投射能量的来
源。在最后一个阶段,即探索投射的意义,总是涉及寻求更深的自我了解。
投射受到侵蚀,它们所代表的希望和期待被撤回,几乎总是令人痛苦的。但这是自我认知的必
要前提。只有知道外界不会拯救自己,我们才会想办法自我拯救。对于每一个充满恐惧、在成
人世界中寻求拯救的内在小孩,都将有一个潜在的成年人为其承担起责任。人们若使投射的内
容意识化,便朝着摆脱童年迈出了一大步。
身体和时间感的变化
第一个成年期的普遍态度是将自己青春的膨胀感投射给模糊的未来。当一个人精力不济时,这
种投射很容易消解。也许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第二天就会精神萎靡,有气无力。然后,轻微
的疼痛和劳累挥之不去。
年轻人总以为自己是金刚不坏之身。身体在那儿提供服务,在需要之时被大加利用,总是会自
我修复。但有一天,我们会意识到,不可避免的转变在发生,超出个人的意志。身体变成了敌
人,变成了我们塑造自我的英雄剧中的对手。心中的希望依然如故,但身体却不再如往常般做
出回应。正如诗人叶芝所感叹的:“把我的心烧尽;它思欲成病/捆绑在一个垂死的肉身上。”
曾经是自我的谦卑仆人,如今变成了一个乖戾的对手;人们感受到肉体的沉重负担。无
论精神多么希望翱翔,哲人怀特海所谓的“身体的共与性” (the withness of the body)都
会将人唤回大地。
时间也是如此,曾经似乎无穷无尽,是永远升起的太阳,现在却如白驹过隙。这种转变,这种
剧情突变,使我们认识到自己不仅是个凡人,终有一死,而且不可能完成内心所有的渴望和追
求。我的朋友总结说:“只有部分,没有完整。”婀娜的身躯,终究是尸骸;无尽的夏天,顷刻变
冬日——正是这种局限和不完整的感觉,宣告了第一个成年期的结束。狄兰·托马斯用令人神往
的优美诗句描述了这种转变:
我心无忧,在羊羔般洁白的日子里,时光
牵着我的手影,在冉冉升起的月光下,
爬上栖满燕子的阁楼,
我并不驰往睡眠
我该听到他与高高的原野一起飞翔
醒来发现,农场永远逃离了没有孩子的土地。
哦,蒙受他的恩宠,我年轻又飘逸,
时光赐我青春与死亡
在镣铐中我如大海般歌唱。
希望的减退
当内心的魔法袋突然收紧,得知自己是个凡人时,生活的局限性就突然呈现在眼前。童年的魔
法思维,以及延长的青春期(即第一个成年期)的英雄思维,被证明不足以应对现实生活。扩
张、专横的自我将童年的不安全感转变成一种夸大感。“我要名扬天下,我将长生不老,我将学
会飞翔。”新生的自我对不朽和成名的希望,与童年对世界的无知和恐惧成正比。同样,中年的
痛苦和抑郁,与童年幻想中投注的能量也息息相关。
自我需要在一个庞大而不可知的宇宙中建立一个立足点。就像珊瑚环礁由骨骼碎片堆积而成,
自我也收集了许多经验的碎片,并把它们塑造成一个结构,以求在汹涌的变化中保持稳定。自
我很自然地得出结论,它必须抵御生活中压倒性的经验,并通过夸大感来补偿不安全感。在不
安全感中,夸大的幻觉可以让我们在夜晚进入梦乡时不被黑暗所困扰。但是,在平凡中挣扎是
中年人的涅槃。即使那些功成名就的人,那些有权有势的人,那些教子“有方”的人,也不比其他
人更有可能免遭限制、收缩和死亡。如果名誉和权力能带来和平或意义,甚至是持久的满足,
我们所投射的幼稚愿望或许会落到实处。
对年轻人来说,另一个与自我有关的希望是对完美关系的期待。虽然我们看到周围许多不甚完
美的关系,但还是倾向于认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更聪明,更有能力做出选择、避开陷阱。《古
兰经》训诫:“你以为你将进入极乐世界,而不用像前人那样经受试炼了吗?” 我们认
为,这样的建议也适用于其他人。关于这一主题,后文会有更多着墨,但这里要指出,中年期
望的第二大坍塌便是遭遇关系的局限性。那个会满足我们的需求,照顾我们,永远陪伴我们左
右的“亲密他人”,现在将被视为一个普通人,就像我们自己一样,也有需求,并将同样的期望投
射到我们身上。婚姻往往在中年时散场,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童年的巨大希望被强加在两个人之
间的脆弱结构上。其他人不会也无法满足那个内在小孩的夸大需要,因此我们感受到了遗弃和
背叛。
投射体现了我们内心未被认领或未知的东西。生活自会消解我们的投射;一个人必须在失望和
惆怅中,开始为自己的幸福承担责任。没有外人能拯救我们,照顾我们,治愈我们的伤痛。但
我们内心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一个我们几乎不了解的人,准备并愿意成为我们永久的伙伴。
只有当我们承认童年的期望已破灭,并接受为自己寻找意义的直接责任时,第二个成年期才会
开始。
我认识一个男人,他承认自己的核心问题是嫉妒。显然,嫉妒是认为别人拥有自己所渴望的东
西。这个男人在童年遭受了真正的剥夺,他现在仍然消极地定义自己:“我所缺乏的,正是别人
富余的。”认识到童年不能重来,历史不能逆转,没有人能神奇地填补内心的空洞,这肯定令人
痛苦,但随后便开启了可能的治愈之路。最困难的是,相信自己的心灵足以疗愈自己。人们迟
早必须信任自己内在的资源,否则就会继续徒劳地追求童年的幻想。放弃那些不朽的、完美的
和夸大的幻想,会暂时伤害一个人的精神和关系。然而,在与自我和他人疏离的体验中,会出
现一种孤独,在这种孤独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己内在的博大。
神经症体验
就像浪漫的爱情可被视作一种短暂的疯狂——恋人们会根据当时的情绪做出永恒的决定,中年
之路带来的动荡可能也类似于精神崩溃,身处其中的人会表现得“疯狂”或离群索居。如果我们意
识到,这个人赖以生存的假设正在崩塌,临时人格的组合策略正在失调,世界观正在分崩离
析,那么这种疯狂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我们理解了情绪的背
景,就不存在所谓的疯狂。情绪不是我们选择的;相反,是情绪选择了我们,它有着自身的逻
辑。
精神病院里有个患者,不停地把椅子砸向窗户。人们认为他想逃跑,便将他捆绑起来。然而,
仔细询问后发现,患者认为房间里的空气正变得稀薄,而他需要呼吸新鲜空气。他在精神上的
封闭感,象征性地转化成了幽闭恐惧症。考虑到这个情绪前提,他想要更多空气是合情合理
的。在搬到更宽敞的地方后,他感到放心多了。这个患者的行为并不疯狂。他只是把封闭和窒
息的心理体验,合乎逻辑地演绎了出来。
因此,在中年之路上,当大量的情绪冲破自我的边界时,我们常常把象征性地受伤害或被忽视
的东西具体化。例如,有个男人与女秘书私奔了,他很害怕自己内心的女性特质枯萎并永远消
失。由于这种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他把内在缺失的女性特质投射到了外在的女人身
上。再如,有个女人患了抑郁症,她将自己内心对不受欢迎的愤怒,全部转向身边至近至亲的
人。尽管别人可能认为他们疯了,但实际上并没有。他们只是在现实情况无法适应内心发展
时,对困扰自己的巨大需求和情绪做出了回应。
关于有意义的疯狂,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短篇小说《狂热者伊莱》(“Eli, the Fanatic”)
中有一个绝佳例子。 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时世界上到处都是流离失所
的人,伊莱是美国郊区的一位知名律师。一群集中营的幸存者被安置在他的小镇上,伊莱被派
去要他们淡化自己的种族身份。但反过来,他发现了自己身份的空虚以及与自身传统的浅薄联
系。最终,他把自己身上的名牌西装换成了老拉比的破旧衣服,一边走在小镇的大街上,一边
念着自己的圣经名字。故事的最后一幕,描绘了他遭到监禁并被注射强力镇静剂。他被判定为
疯了;但实际上,他只是抛弃了自己的临时身份,摆脱了跻身上层社会的陷阱和投射,将自己
重新安置在一个古老的传统中。由于他的新身份与公认的模子不一致,他便被认为“疯了”,他的
“新意识”被药物所治疗。我们可以像华兹华斯评价布莱克(Blake)那样评价他:“有人认为这个
人疯了,但我更喜欢这个人的疯狂,而不是其他人的理智。”
后天获得的自我感及其附带的策略和投射,与埋藏在个人历史之下的自性要求之间的裂缝越来
越大,这种体验众所周知,因为所有人都感到了与自己的疏离。苏格兰医生卡伦(Cullen)在18
世纪晚期创造了“神经症”一词,表明我们正在经历的是神经系统的疾病。但现在,神经症或所谓
的精神失常,实际上与神经学(neurology)并无任何关系。这个术语只是用来描述内心的分
裂,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灵抗议。所有人都有神经症,因为我们都体验到了“我们是什么”和“我们
应该是什么”之间的分裂。神经症的症状性抗议,表现为抑郁、药物滥用或破坏性行为,会被人
们尽可能地否认。但症状会重新聚集能量,并开始自主运作,脱离自我的意志。我们要求症状
消失,就像告诉节食的人不要饿着一样徒劳无功。症状,即使适得其反,也是有意义的,因为
它以象征的形式表达了人们渴望表达的东西。
受到惊吓的人们最希望恢复曾经起作用的自我感。但治疗师知道,这些症状是发现内心创伤的
有用线索,并为随后的治愈指明了方向。治疗师还知道,中年的神经症体验,若是可以面对,
会成为一个巨大的转变机会。正如荣格所断言的:“神经症的暴发不仅仅是偶然的。一般来说,
这是最关键的时刻。它通常是要求新的心理调整、新的适应的时刻。” 这意味着我们的
心灵组织了这场危机,制造了这种痛苦,因为伤害已经造成,改变必须发生。
我经常想起一个女人的梦,她在65岁时第一次接受分析,那时她的丈夫刚刚过世。她自小受父
亲的影响特别大,有着强烈的父亲情结。她的丈夫年长她好几岁。很自然地,她因为失去这两
个人而悲痛欲绝。她向一位牧师寻求安慰,牧师建议她接受心理治疗。起初,她认为心理治疗
可以消除她的痛苦。可想而知,她把大量的权威投射给了治疗师。
接受分析几个月后,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她和已故的丈夫一起旅行。当他们走到有座桥的小溪
边时,她想起自己忘了带钱包。丈夫继续往前走,她返回去拿钱包。当她回到那座桥边时,旁
边来了一个陌生男人,和她一起过了桥。她向这个人解释,她的丈夫在前面,但他已经死了。
她哀叹道:“我好孤独,好孤独。”这个陌生人回答说:“我知道,但这对我来说是件好事。”
在这个梦里以及后来的报告中,做梦者对这个陌生人很生气,因为后者似乎对她的丧亲之痛无
动于衷。我却对这个梦感到很兴奋,因为它显示了明确的心理转变。虽然她的父亲和丈夫实际
上已去世,但他们仍然左右着她的自我定义。父亲情结看似温和,却形成了一种外部权威,阻
碍她找到自己的力量。这座桥构成了从外部权威向内部权威过渡的空间;而这个陌生人代表了
她内在的男性法则,即阿尼姆斯(animus),由于父亲情结的影响,它一直没有得到发展。这是
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心灵奇妙的、自我调节的智慧。她的自我所遭受的痛苦,促使她的内
心生长出不受父亲支配的成分。因此,她在65岁时踏上了中年之路,开始了确认自己身份和发
现自身权威的旅程,两者皆是真正成年的必备条件。
看待神经症的另一种方式是认为痛苦产生于相当大程度的解离 。在回应童年的社会化和
外界现实压力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变得与自己疏远。内在的抗议被外部世界的重担死死压制。
但人到中年,对灵魂的伤害和忽视,可能会使部分心灵极力抵抗进一步的冒犯。这种抗议表现
在症状中。与其用药物来消除它们的信息,不如让它们参与到对话中来,从而实现荣格提到的
“新的适应”。
对那些遭受巨大痛苦、身处灵魂暗夜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即他们的痛苦对他
们是有好处的,如上述梦中那个陌生人所说。不过,在痛苦中也许可以找到前进的道路。因为
生命不是一种疾病,死亡也不是一种惩罚,因此不存在所谓的治愈。但确实有一条道路,可以
通往更有意义、更丰富的生活。
我想起一个经历了巨大痛苦的女人,她艰难地来到这个世上,身体畸形,曾被忽视和遗弃,有
过一系列依赖和耻辱的关系。到了中年,她的世界崩塌了,她向内心寻找那个自己从未认识的
人。她用“碎片化”这个词来描述中年之路的磨难。许多人都遭受过这样的破碎,而且许多人逃往
神经症的大本营,在变化的风暴面前蜷缩起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当我问这个女人,在她感
到支离破碎的时候做了什么,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她是谁,她清楚地告诉我,她会渡过难关,
过上更真实的生活。我记得她说:“我对我的这部分说话,然后我倾听。我对我的那部分说话,
然后我倾听。我试着去了解心灵需要我做什么。”
她说心灵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一个知道什么将指引她的女性。有人可能会说:“她幻听了,她
有精神分裂症。”恰恰相反。可以说,我们都会听到声音;那是情结,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它
们对我们说话,而我们,如果没有注意去听,就会成为它们的俘虏。这个女人正在协调自我和
自性之间的对话,这一对话可以治愈过去造成的分裂。她相信自己的内在过程,这一信任是必
要的,也是稀少的。天性并不反对我们。诗人里尔克(Rilke)优美地指出,内心的恶龙实际上
可能需要我们的帮助:
我们怎么能忘记所有民族之初的那些古老神话,那些恶龙在最紧急关头变成公主的神话;也许
我们生命中所有的恶龙都是公主,只等着看到我们表现出美丽和勇敢。也许一切可怕的东西,
在其最深处都是无助的,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
细致的关怀能将这些恶龙转化为更新的能量来源。
回想一下荣格对神经症的定义:“其意义尚未被发现的痛苦。” 事实上,痛苦似乎是个人
转变的前提。在其他地方,荣格提出神经症是“不真实的痛苦”。 真实的痛苦需要与恶龙
打交道,不真实的痛苦则意味着逃避它们。
如果荣格和里尔克是对的——我认为他们是对的——那么,恶龙就代表了所有我们害怕的、威
胁着要吞噬我们的东西;但它们也是我们自身被忽视的部分,这些部分有可能被证明极具价
值。若它们被认真对待,甚至为我们所爱,会为我们后半生的旅程提供巨大的能量和意义。
第三章
内在的转变
一个人前半生的核心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性 。每个人都知道,有的人从未真正离开过
家。这个人可能如字面意义所说,和他的父母住在一起,彼此照顾;这个人也可能和父母住在
同一个社区,或者远在千里之外,但依旧受父母的控制。在心理上没有与父母分离,仍然跟他
们捆绑在一起。这些人前半生的任务是未完成的。
未获得稳定的自我同一性,会困扰并阻碍个体后半生的发展。要为第二个成年期做准备,不仅
需要与父母保持地理上的分离,我们还必须自给自足、自力更生。这并不意味着有一份有报酬
的工作就够了,而是说我们要感受到任务的挑战,并在完成任务时感到满足。
我们还需要更成熟地投身于亲密关系。在不可避免的关系摩擦中,如果不能坚持自己的立场,
并与另一个人达成妥协,意味着这个人无法达成自己的精神现实。此外,作为一个公民,我们
还应该参与到外部世界中去。每个人都想过从这个疯狂的世界中抽身而出,偶尔的撤退无疑有
助于灵魂的恢复,但如果总是逃避,只会阻碍自我同一性的进一步发展。荣格再次清晰地表达
了这项任务:
生命的自然历程要求年轻人献祭他们的童年,放弃对父母的幼稚依赖,以免他的身体和灵魂仍
被无意识的乱伦所束缚。
恐惧意味着挑战和使命,因为只有鼓足勇气才能挣脱恐惧。如果选择对危险退避三舍,就是对
生命意义的某种亵渎,整个未来就会变成一潭绝望的死水,一束忽明忽灭的火光。
正如我们所见,即使是稳定的自我同一性也会在中年遭到破坏。一段失败的关系带来的心碎,
曾经支持和拯救我们的人的离开,职业发展热情的丧失,都表明迄今为止由它们所维持的投射
和同一性受到侵蚀。无论一个人在巩固自我状态、建构自我世界方面多么成功,中年之路上的
坍塌都会带来困惑、挫败和身份丧失的体验。
通常,当一个人踏上中年之路时,前半生未完成的事务会毫不留情地显露出来。例如,在离婚
的时候,人们就必须面对曾被婚姻掩藏的心照不宣的依赖性。人们可能会意识到他们将父母情
结投射到了伴侣身上,或者发现自己缺乏工作技能或自信。然后,前半生的“未竟事业”就会找上
门来,让我们心生怨恨或指责他人。
中年之路上最有力的冲击之一,就是意识到我们和世界之间并没有签订心照不宣的契约,并不
是只要我们心地善良、意图良好、行为正确,事情就会进展顺利。我们假想和这个世界实现互
惠;只要我们尽职尽责,世界就会报之以歌。许多古老的故事,包括《约伯记》 ,都向
我们揭示了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契约。每个经历过中年之路的人都被迫明
白了这一点。举个例子,如果没有极高的期望和美好的心愿,没有人会踏上婚姻的小船,而不
顾罗盘多么不稳定,潮汐多么起伏。当一个人站在亲密关系的废墟中,他不仅失去了这段关
系,而且常常失去了整个世界观。
也许最大的打击是自我至高无上的幻觉受到侵蚀。无论自我的投射曾经多么成功,如今它再也
不能独揽大权。自我的崩溃意味着一个人并没有真正掌控生活。尼采曾指出,当人类发现自己
不是上帝时,他们是多么沮丧。实际上,意识到一个人甚至不能很好地管理自己的生活,这就
足够了。荣格强调,当我们发现自己不是生活的主人时,自然会不寒而栗。因此,除了震惊、
困惑甚至恐慌之外,中年之路的根本结果是使人谦逊。我们和约伯一起坐在粪堆上,失去了幻
想,想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不过,这种经历可能会带来新的生命。在前半生的斗争中获得的力
量,现在可以用来与后半生周旋了。
如果自我没有足够的力量,就无法从“自我—世界”轴转移到“自我—自性”轴。在自我分离与固化
的过程中未完成的事务,将会变成一个人成长的障碍。
生活会毫不留情地要求我们长大,并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虽然听起来很简单,但长大确实是中
年之路上不可逃避的要求。它意味着最终在没有他人的帮助下,面对自己的依赖、情结和恐
惧。它要求我们不再因自己的命运而责备他人,并对自己的身体、情绪和精神健康承担全部责
任。我的分析师曾经对我说:“你必须把你的恐惧提上议程。”这听起来令人害怕,但我知道他是
对的。这个议程要求我负起责任,要求我全力以赴。
在中年之路上,我们通常还要抚养孩子、养家糊口、尽职尽责。然而,即使外部世界不停地要
求我们付出,我们也必须转向自己的内心,去成长,去改变,去寻找那个作为旅程目标的人。
人格面具与阴影的对话
当自我不再独揽大权,即一个人了解自己和掌控大局的幻觉破灭时,必然会导致人格面具和阴
影之间的冲突。在中年时期,人格面具(persona)和阴影(shadow)的对话,表明了个体要在
社会现实和个人真实之间实现必要的平衡。
人格面具是自我对社会环境或多或少有意识的适应。我们创造了许多人格面具,它们是一些随
机应变的角色。我们在父母面前是一副面孔,在老板面前是另一副面孔,在爱人面前又是一副
面孔。虽然人格面具只是与外部世界连接的媒介,但我们往往会混淆他人的人格面具与其内在
真实,也会把自己的内在与角色混为一谈。如前所述,当我们的角色改变时,我们会迷失自
我。人格面具会伪装成个性,但归根结底,正如荣格所说,它“不是真实的:它只是个体和社会
之间的妥协”。
一旦认同了自己的人格面具,即社会化的自我,当我们从外部世界中抽身而出,面对自己内在
的现实时,必然会承受焦虑。因此,中年之路的一项任务,就是彻底改变我们与人格面具的关
系。
由于前半生总是在建构和维护人格面具,我们经常会忽略自己的内在现实。而我们的阴影,代
表着一切被压抑或未被承认的东西。
阴影包含了所有至关重要但也存在问题的愤怒和性欲;当然,也包含了欢乐、自发性和未点燃
的创造火花。弗洛伊德一针见血地指出,神经症是文明的代价。文明社会的要求,从一个人诞
生的家庭开始,就将心灵的内容分裂,将我们的阴影拉长。阴影代表了社会价值的利益对人类
天性造成的伤害。因此,面对阴影以及对它的整合,可以治愈神经症的分裂,使人得到成长。
正如荣格所总结的,如果迄今为止人们都认为,人类的阴影乃是万恶之源,那么,现在经过更
仔细的研究,可以肯定地说,阴影并非只由那些应在道德上受谴责的倾向组成,它也表现出一
些良好的品质,例如正常的本能、适当的反应、现实的洞见和创造性冲动等等。
人到中年,我们已经压抑了自己的大部分个性。例如,愤怒经常在中年时期爆发,就是因为人
们一直被鼓励压抑它。anger(以及anxiety, angst, angina)的词根是印度日耳曼语系中的angh,它
的意思是“压缩、限制”。几乎所有的文明都代表着对自然冲动的约束,因此,愤怒的日积月累是
可以预料的。但是,那些与自然冲动相关的能量去哪里了?通常,它助长了我们盲目的野心,
促使我们使用麻醉品来减弱其强度,或者导致我们虐待自己或他人。如果一个人被教导发怒是
一种罪恶或道德败坏,那么他就会远离这种真实的体验。但如果愤怒得到了承认和引导,它也
可以成为改变的巨大动力。此后,人们就会拒绝非本真的生活。我们花了一辈子投资人格面
具,愤怒的阴影当然会让人感到不安,但自由地感受真实的自己,是治愈内心分裂的必要步
骤。
遭遇其他的阴影也十分痛苦,因为不得不承认通常不被人格面具所接纳的一系列情感,如自
私、依赖、欲望和妒忌。在此之前,人们可以否认这些品质,并把它们投射到别人身上:他爱
慕虚荣,她野心勃勃,等等。但是,人到中年,已经没了自我欺骗的余地。在清晨照镜子时,
我们看到的敌人是我们自己。虽然面对不那么好的品质会令人痛苦,但承认这些品质可以让我
们撤回对他人的投射。荣格认为,我们能为这个世界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撤回自身阴影的投
射。承认世界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这需要巨大的勇
气。但是在这个谦卑的时刻,我们开始改变、提升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并带来疗愈关系和自己
的机遇。
与自己的约定也意味着回到过去,拾起被丢弃的东西:生活的乐趣,未开发的天赋,童年的愿
望。如果我们把心灵看作一幅镶嵌画,很难计算出这幅画的所有碎片,更别说实现了,但每一
个碎片都无疑能治愈和奖赏受伤的灵魂。因此,想学弹钢琴的人们,想去上大学的人们,或者
想在夏日午后泛舟湖面的人们,都可以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无论当初出于什么原因没有去做。
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心灵构造,但可以选择喜爱或忽视它的内容。然而,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
不能自由地承认自己内心的现实。我们缺乏来自父母的充分肯定,缺乏父母拥抱生活所树立的
榜样;我们内化了这种忽视,内化了阻止我们发挥潜力的禁令。人到中年,允许自己按照真实
内心去生活是至关重要的。人终有一死,时间有限,没有人能将我们从生活的重担中解救出
来,这些事实将促使我们更充分地做自己。
在中年之路上,阴影的暴动是自性纠正功能的一部分,以使一个人能保持平衡。整合阴影,活
出未实现的人生(the unlived life),关键是明白这一需求源于自性,它既不希望进一步地压
抑,也不希望无节制地行动。整合阴影不仅要求我们在社会中负责任地生活,还要求我们更诚
实地对待自己。我们通过人格面具的失效了解到,过去我们过着临时的生活。整合内心的真
实,不管是让人快乐还是不快乐的,对于带来新的生活和意义的重建都是必要之举。
亲密关系问题
如前所述,在中年时,没有什么比婚姻这种长期亲密关系更容易带来失望和伤害了。这种关系承
载了我们的内在小孩。对于亲密关系,我们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太多的需求,收获了太多的失
望。每个人在中年回望过去时,都会对自己几十年前在婚姻、职业上的选择以及做选择时的无意
识不寒而栗。年轻人总是坠入爱河,许下终生承诺,诞生爱的结晶。他们会继续这么做下去。但
在中年之路上,许多人不得不直面自己和伴侣,这给亲密关系带来巨大的考验。事实上,很少有
中年婚姻——如果它们能存活下来——不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要么婚姻成为人们内心压力的主要
来源,要么离婚成为踏上中年之路的起点。
为了更多地了解亲密关系在中年之路上的角色和重要性,我们需要更深刻地思考这种关系的本
质。显然,我们向其交付灵魂的人是十分重要的。此外,现代文化通常认为婚姻和爱情是同义
词。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婚姻都只是维护和传递价值观、种族意识、宗教传统和权力的工
具。被安排的婚姻比那些基于爱情的婚姻有更好的历史记录,而爱情是最难以捉摸的感情状态。
类似地,只要死亡或命运不加干涉,基于相互依赖的婚姻也会维持得很好。(一个以前的同事,
被大屠杀的经历所折磨,娶了一个年龄比他小一半的女人,她接管了他的生活,双方都觉得很满
意。)事实上,根据各种说法来看,基于生活需要的婚姻比基于爱情和相互投射的婚姻更有可能
长久。正如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所说的:
当两个人处于最激烈、最疯狂、最虚幻、最短暂的激情之下,他们被要求发誓将一直保持这种兴
奋的、不正常且令人筋疲力尽的状态,直到死亡把他们分开。
下图展示了人们在异性恋的亲密关系中常见的互动:
在意识层面,两个人的自我建立关系,但人们不会在自我关系的基础上缔结爱情关系。这一“荣
耀”落在了阿尼玛和阿尼姆斯身上,它们是一个人心灵内部无意识的异性成分。
简单地说,阿尼玛代表了男性内化的女性特质,最初受到母亲和其他女性的影响,同时也会被一
些未知的、对他而言独特的东西所浸染。他对阿尼玛的体验,代表了他与自己身体的关系,代表
了他的直觉,他的感官生活以及他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女人的阿尼姆斯则是她对男性法则的体
验,受到父亲和文化的影响,但同样也有一些神秘的独特性。阿尼姆斯代表了她的根基感,她的
潜力,以及她全力以赴实现愿望的能力。
然而,亲密关系的基本真相是,一个人会把自己身上未经意识检验的东西投射到伴侣身上。上图
中的对角线箭头显示了这种从阿尼玛(阿尼姆斯)到自我的投射,以及相应反方向的投射。
在众多异性中,只有少数人会相互吸引,他们都是投射的好钩子,至少能暂时招引投
射。图中这种对角线的动态就是所谓的浪漫爱情。
浪漫的爱情给人一种深刻的联结感,带给人新的能量、希望以及归属感。一见钟情就是这种投射
中最引人注目的。只要对方能暂时维持这个投射,哪怕他/她是一个杀人犯。很明显,在这个投射
背后,只是一个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并且毫无疑问也向我们投射了大量内容。但对我们来说,
这个“他者”是特别的。我们会说,“这个人不一样”或者“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流行文化助长
了这种错觉。如果把音乐排行榜前40首歌曲串烧起来,大概是这样的:“我一直过着悲惨的日
子,直到你出现在我生命里,所有的事物焕然一新,我们站在了世界之顶;有一天你变了心,我
们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一切,你离我而去,现在我过着悲惨的日子,永远不会再爱了,直到下一次
遇见。”这些流行歌曲千篇一律,不同的只是歌手的性别和是否有吉他伴奏。
每天生活在一起,会无情地消磨投射;最后,一个人所面对的只是对方的特性,后者根本无法满
足大量的投射。所以,人们会在中年得出结论:“你不是我当初结婚的那个人。”事实上,他们从
来都不是。他们始终是另一个人,一个我们当时几乎不了解的陌生人,现在也只是稍微了解了一
点。由于我们把阿尼玛或阿尼姆斯投射到那个人身上,因此我们实际上是爱上了自己缺失的那部
分。这种联结感和归属感是如此美妙,并带来大量的希望,以至于失去它时,我们感觉那是一场
灾难。
亲密关系的真相是,它永远不会比我们与自己的关系更好。我们与自己的关系,不仅决定了对
“亲密他人”的选择,也决定了亲密关系的质量。事实上,每一段亲密关系都在暗地里透露出我们
的本性。因此,所有的亲密关系都是我们内心状态的体现,没有任何关系会好过我们与自身无意
识的关系(上文图中的纵向箭头)。
如果我们没有那么多要求,亲密关系就不会如此沉重。但如果这种关系不能满足内在小孩的期
待,那么它的意义又何在呢?荣格指出,人生意义来自:
人们感觉他们过着象征性的生活,他们是神圣戏剧中的演员。这给了人类生活至高的意义;其他
的一切都是平庸的,是可以忽略的。一份职业,生育孩子,与至高无上的事情相比,与你人生的
意义相比,都是幻象。
比如,问题就从期待那个魔幻“他者”来拯救我们,转变为亲密关系在获得人生意义中所扮演的角
色。
显然,我们文化中的亲密关系模式,以及人们第一个成年期的愿望,是希望融合或合而为一,即
相信通过与另一半的结合,自己将得到补全,变得完整。通过结合,我们融为一体;通过结合,
我们变得完好。一个人面对浩瀚的世界,会觉得自己不完整和不足,自然会产生结合的愿望,但
这种愿望实际上会阻碍两个人的发展。当日常生活磨灭了希望以及伴随的投射,人们就会经历意
义的丧失,也就是说,投射到另一半身上的意义烟消云散了。
从中年的视角来看,我们必须替换掉融合模型,因为它根本行不通。如果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心理
健康负责任,那么对于后半生来说,这个适用的模型应该如下图所示:
这个盆状的容器暗示着成熟的亲密关系的开放性特征。每个人的首要任务是为自己的个体化负
责。在这段亲密关系中,人们相互支持、相互鼓励,但不能为对方执行个体化或发展的任务。
(我们将在第五章讨论个体化的重要性。)这个模型抛弃了一个人会被“他者”所拯救的观念。它
假设双方都能接受个体化的邀请,并通过完善自己来为亲密关系做贡献。成熟的亲密关系超越了
融合模型,要求双方都承担起个人责任,否则婚姻就会停滞不前。
要想拥有一段成熟的亲密关系,我们必须能够坦言:“没有人能给我我最想要或需要的东西。只
有我自己可以。但我会赞美这段关系所切实提供的,并为之真心付出。”亲密关系通常提供最多
的是陪伴、相互尊重和支持,以及辩证的对立面。一个用亲密关系来支撑脆弱自我的年轻人,不
可能满足成熟关系对勇气和纪律的要求。从前他需要肯定和认同,现在他必须接受差异和不同;
从前他想要简单的合而为一的爱,现在他必须学习如何爱上差异性。
当一个人放下他的投射和巨大的隐秘议程时,他就可以被伴侣的差异性所扩展。一个人与另一个
人结合,并不像融合模型那样合而为一,此时会产生第三个空间。两个人是单独的个体,他们的
关系形成了第三种力量,迫使他们超越各自的限制。此外,当一个人放弃投射,把重点放在内心
成长上,他就会遇到自己浩瀚的灵魂。“他者”帮助我们拓展了心灵的可能性。
里尔克把亲密关系描述成与另一个人分享自己的孤独。
这显然已经接近真相了,因为我们最终拥有的只是自己的孤独。我们必须承认,投射不会永远持
续,但话说回来,它可能会被更丰富的东西所取代。由于投射是无意识的,我们无法确定自己与
“他者”的关系是否真实。但如果我们为自己承担了主要责任,就不太可能将内在小孩的依赖和不
切实际的期望投射出去。
因此,真正的亲密关系源于一种有意识的愿望,想要与另一个人分享自己的旅程,通过对话、性
和关心的桥梁,走向生命的奥秘。尼采曾经指出,婚姻是一场交谈,一场伟大的对话。
如果一个人没有准备好参与长期的对话,他就没有准备好进入长期的亲密关系。许多年老的夫妻
早已无话可谈,就因为他们停止了作为个体的成长。如果重点在于个人成长,那么每个人都将有
一个有趣的交流伙伴。若一个人阻碍自己的成长,即使这种牺牲是为了另一半好,那你的伴侣也
将注定与一个愤怒且抑郁的人生活在一起。一个人的成长受到另一半的阻碍,同样是不可接受
的。这样的婚姻必须重新开始,否则它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在成熟的婚姻中,在开放和辩证的
婚姻中,我们会经历第64页图中所示的最深层的关系,即两个神秘事物之间的交流,两个内在异
性能量之间的碰撞;这就是灵魂与灵魂的相遇。
因此,爱情是一种经历荣格所提到的象征性生活的方式,是一种遇见神秘的方式,其名称和本质
我们永远无法理解,但如果没有它的存在,我们就会陷入浅薄。到了中年,许多婚姻要么草草收
场,要么苦苦挣扎。在过去,那些撤回投射的人因为巨大的社会压力,无法寻求另一段婚姻。有
些人选择外遇,有些人滥用药物,有些人通过工作和育儿得到升华,还有些人则患上偏头痛或抑
郁症。积极的选择通常是遥不可及的。今天,我们有了这样的选择,尽管每个选择都不容易,但
至少好过被困在一个不利于伴侣个体化的体制中。尽管初心美好,自我意志泛滥,但真相终将大
白于天下。审视那个承载了自己希望和需求的体制需要勇气,但这种勇气同时也会带来治愈,让
人恢复完整,并重获新生。
相信魔幻“他者”是一种残酷的自欺欺人。即使找到了这样的人,肯定也是一种投射。如果过了一
段时间,我们仍然受到“他者”的照顾,那么很可能陷入了对方有意或无意投喂的依赖中。我不是
刻意贬低伴侣在人生旅途中可以发挥的支持作用,而是说,一个人可能会因此逃避对自己的生命
要承担的巨大责任。我认识一个非常能干的女人,她在早上把丈夫送出了家门,下午就把男朋友
领回了家。虽然她在事业上很成功,但她无法尝试跟自己相处,无法与自己对话。
当一个人有勇气转向内在时,他将有机会面对自己人格中被忽视的部分。如果一个人不再急切地
从伴侣身上寻找生命意义,他就会被召唤去激活自己的潜能。
每个人在人生早期都被教导过“男女有别”,最近我就听说了一个经典的性别角色故事。一对夫妻
处在离婚的边缘,他们相互抱怨对方造成了自己现在的生活局面。男人说他努力工作,就是为了
事业成功、养家糊口。他忠实地执行这个计划,却因为没有自己的生活而心生怨恨。他的愤怒在
内心积累,逐渐变得消沉,最后他感觉如果不离开这段婚姻自己就会死。他的妻子则回应说,她
一直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照顾丈夫,照顾家庭和孩子,放弃了自己的职业目标,她也感到很郁
闷。
很明显,这两个人都是受害者。他们都恪守性别角色的教诲,尽己所能地按其要求生活,就像他
们的父母一样;二十年来,他们变得互相憎恨。他们是彼此不快乐的帮凶;但除了完成第一个成
年期的剧本之外,我们还能期待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做什么?他们很好地遵守了婚姻制度,但这
一制度却没有很好地回馈他们。他们能否继续在一起,取决于双方对个人成长的承诺。
关于心灵,永恒不变的真理是:要么改变,要么在怨恨中枯萎;要么成长,要么在内心中死亡。
同样,中年婚姻的悲剧在于,这段亲密关系经常被怨恨所污染,以至于修复的可能性受到致命损
害。美好的初心能否被唤醒,对伴侣的负面投射能否被撤回,始终是个问题。
平衡对他人的义务和对自己的义务,诚然很困难,但我们必须努力。这个问题并不新鲜。易卜生
的《玩偶之家》( A Doll’s House )出乎意料的新潮。当娜拉离开她的丈夫和孩子时,有人提醒
她还有对教会、丈夫和孩子的责任。她回答说,她对自己也有责任。她的丈夫表示不理解。他问
道:“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吗?”娜拉回答说,她也不知道,因为她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而且因为
(实际上)她只是按照第一个成年期的剧本在生活,所以她不确定自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一个多世纪前,当《玩偶之家》在欧洲各大都市上演时,骚乱接踵而至,因为它对婚姻和养育的
体制隐含着巨大的威胁。即使是现在,当你离家出走,甚至只是改变某种约束的模式,仍然面临
社会舆论、模范父母和内疚的阻碍。娜拉走出了家庭生活的圈子,却可能陷入社会排斥和经济困
境,因为法律会剥夺她的财产权、监护权和经济权利。但娜拉知道她必须出走,否则她就会死
去。
双方越早把个体化作为亲密关系存在的理由,这段关系就越有可能持续下去。
人们很自然地认为,时间会以某种方式解决心中烦恼和腹中空虚。当我要求一对夫妻想象十年后
没有任何改变时,他们通常会更明白必须有所改变。如果夫妻中的一方阻止改变,他或她无疑仍
被焦虑所控制,并热衷于第一个成年期的投射。很有可能,这个顽固的伴侣永远拒绝承担必要的
责任;如果是这样,他或她定会因为否定他人的生命而受到惩罚。任何人都没有权利阻碍他人的
发展,这是一种精神犯罪。
如果伴侣能意识到自己的不快乐,并坦率地请求对方的支持,这段婚姻就有可能得到延续。这
时,另一半将不是拯救者,也不是敌人,而仅仅是伴侣。也许夫妻治疗的理想模式是,每个人都
接受单独治疗,更好地解决发展的需求,同时两人也一起参与会谈,修正过去失败的相处模式,
并讨论对未来的希望和计划。这样一来,婚姻就可以成为个体化的容器。
为了达成合作而不是冲突的态度,我经常在伴侣在场时提出某些问题。例如:“在你过去的经历
或行为中,有什么可能会导致冲突或破坏亲密关系?”这让那些认为自己是来寻找帮手对抗伴侣
的人感到震惊。这个问题要求他们开始审视自己,并对亲密关系的维护和滋养承担更大的责任。
另一个很有用的问题是:“你对自己有什么梦想,是什么恐惧阻碍了你?”在听到对方的挣扎和失
望后,伴侣经常会产生同情,并希望支持他们。分享自己的挫败、恐惧和希望,才是真正的亲
密;但很少有夫妻能做到这一点,无论他们结婚多久。性爱是夫妻间的桥梁,孩子是两人之间的
纽带,但真正的如胶似漆是两个人感同身受。
除非我们能切身体会另一半的感受,否则我们永远不可能爱上对方的特性。也许爱实际上是一种
想象他人经验的能力,这种想象是如此生动,以至于我们能肯定对方的存在。真正的对话有助于
这种想象,也是自恋偏执的解毒剂。我曾听到有人质疑:关注个人成长本身是否也是一种自恋?
只要一个人决心实现自己的潜能,并把同样的权利赋予他人,这就不是一种自恋。
这需要一种双重的力量:为自己负责的能力,在想象中验证“他者”真实性的勇气。这两种力量在
我们的文化中都没有很好的榜样,所以我们必须自己去寻找。而另一面恰恰就是许多婚姻的悲惨
处境。我们因为自己不快乐而埋怨伴侣,并私下怀疑自己是同谋。这简直是自掘婚姻的坟墓。
许多人都认为,如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 在《不同的声音》( In a Diferent
Voice )中所见,女性比男性更难确认自己的个体化需求,因为亲密关系对女性提出了苛刻的要
求。女性意识的本质可以被描述为扩散性意识(diffuse awareness),这意味着女性非常了解她的
周围环境,以及其他人对她的要求。因此,吉利根提出,她身边的女性都同意年轻的斯蒂芬·迪达
勒斯(Stephan Dedalus) 的做法;在詹姆斯·乔伊斯的自传体小说《青年艺术家画像》(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中,迪达勒斯宣布——就像乔伊斯本人一样——他要离开
他的家庭,告别他的民族和信仰,因为他不能再忠于那些无益于自己的东西。
但她们也认同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 在《天主教女孩自白》( Confessions of a
Catholic Girlhood )中表述的困境;当她想跃入未知的世界时,却被责任和内疚所束缚、所掣
肘。虽然今天的女性比她们的母亲有更多机会选择自己的道路,但许多人仍然会因为别人对她们
的要求而备感约束。所以,女性为了成就自我必须比男性迈出更大的一步。就像《玩偶之家》中
的娜拉一样,她必须在别人的要求和对自己负责之间找到平衡。最终,做出牺牲的女性,既不是
好母亲,也不是好伴侣。女性成为圣徒的代价,需要她和别人共同承担。
童年的依恋需求在成人内心仍然非常强烈,甚至可以说它们是自然和正常的。但如果一个人的自
我价值和安全感总是依赖于他人,那么他是不够成熟的。“依恋饥渴”(attachment hunger)这个
词,就描述了对他人的自然需求失控时的模式。 当然,人们忘记了,每个人内心都有一
个现成的伴侣,至少是潜在的伴侣。
对许多男性来说,一大问题是他们的内心已经麻木。
大多数男性习惯于回避感情,避免本能的智慧,并凌驾于自己的内在事实之上,他们不管对自己
还是他人来说,都是陌生人,是金钱、权力和地位的奴隶。菲利普·拉金 令人难忘地写
道,他们的
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就像圣诞节一样;他们
无助地背负着承诺、义务和必要的仪式,
漂流在衰老和乏力的黑暗大道上,
被曾经幸福甜蜜的生活所抛弃。
在我们的文化中,几乎没有允许或邀请男性对自己诚实的榜样。当一个男人被问及他的感受时,
他通常会解释自己的想法,或者“外在的”问题是什么。想想每一项体育赛事的电视转播中,啤酒
广告所传递的巧妙而默契的信息。一群兴高采烈的壮汉扛大梁、锯木头或驾驶叉车。(他们从来
不会坐在个人电脑前面或抱着孩子。)哨声响起,老兄们的畅饮时间到了。他们大步走向附近的
酒吧,可以像好兄弟一样碰撞身体。在酒吧里,他们举起酒瓶,伴着一个有象征性的金发女郎,
这表明他们不是同性恋,并代表了即将在欢乐、愤怒或伤感中被召唤出来的阿尼玛。酒精,放松
了男人对内心女性的限制,释放了不被意识承认的东西。
如果男人与自己的女性灵魂都没有处好关系,又怎能期望他们与女人处好关系呢?女人不可能疏
通男人的内心;她们只能接受或部分承受男人对女性的投射。古埃及故事《厌世的男人寻找他的
灵魂》( The World-Weary Man in Search of His Ba )流传至今,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并不新鲜。也
许新鲜的是,在巨大的压力下,在要求扮演战士和经济动物的旧角色时,越来越多的男人被邀请
进入内心,寻找自己真实的样子。
罗伯特·霍普克在《男人的梦境,男人的治愈》一书中指出,男人大概需要一年的心理治疗,才能
够内化并面对自己的真实感受,才能达到女人通常开始治疗时的状态。
我猜测他是对的,有多少男人准备接受一年的治疗,只为了达到这个起点状态。谢天谢地,有些
男人会这样做,但更多的男人却在漂泊和迷失。作为父权制的受害者,男人只知道把权力当作男
子气概的证明。
因此,中年之路上的男人必须重新成为孩子,面对被权力所掩盖的恐惧,并重新提出那些古老的
问题。这些问题看起来很简单:“我想要什么?我有什么感觉?我怎么做才能让自己感觉良好?”
现代男人很少允许自己奢侈地问这些问题。于是,他们一边步履沉重地去上班,一边梦想着退休
后在某个奢华球场打高尔夫,并祈祷这一天在心脏病发之前到来。除非他能谦逊地问这些简单的
问题,让自己的内心说话,否则他是没有任何机会的;他会成为自己和他人的恼人伙伴。
类似地,许多女人也被剥夺了权力,她们天生的力量被内心消极的声音所侵蚀。负面的阿尼姆斯
紧绷喉咙,在她们耳边低语:“你不能这样做。”阿尼姆斯代表了女人的创造能力,她们过自己的
生活、实现自己梦想的能力,但它躲藏在一系列阴影之下,比如母亲的榜样、父亲的鼓励(或打
击)和社会所提供的狭隘角色。在传统上,女性总是被告知通过丈夫和儿子的成就来获得满足
感。
我读过的最伤感的评论之一来自玛丽·本森(Mary Benson)的日记,她是一个彻底的维多利亚时
代女性,作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爱德华(Edward)的妻子,被婚姻和教会的双重制度所束缚。当爱
德华去世后,玛丽开始与自己相会:
我有一种糟糕的感觉,我整个人生都源自并在回应各种永不停歇的要求。我的内心没有任何东
西,没有权力,没有爱,没有欲望,没有主动;他拥有我的所有,他的生活完全支配着我的生
活。上帝啊,给我点个性吧。我想有点个性。怎么把它和寻找自我联系起来?我感觉自己一直过
着一种浅薄的生活,既不是有意为之,也不能说完全错了。但是,我和爱德华这样一个占主导地
位的人在一起……再加上这个职位的巨大要求,我怎么可能找到自我呢?我似乎只是一个回应的
服务器,没有内核。但我必须有一个核心。
读者们,你们的内心是否受到了震动?你们是否也过着和玛丽一样的生活?虽然她的评论令人伤
感,考虑到当时的教会权力,也是可以原谅的,但最终她必须承担责任。个性不是由上帝赐予
的;个性是通过每天与怀疑和反对的魔鬼抗争而得到的,如果不这样做,等待我们的将是抑郁和
绝望。
现代女性不再受性别角色的定义,但她们要为平衡事业和家庭而英勇奋斗,曾经的梦想已经所剩
无几。一个女人在中年时,通常只剩下丈夫和孩子,孩子必然忙碌于自己的生活,丈夫则被工作
所占据,或者被他的阿尼玛所投射的新欢所俘。也许有人会说她有权感受到背叛和遗弃,但话说
回来,如果她能早点有意识地预见并为这些事做准备,她可能会迎来全新的自由。
我认识一位父亲,他在女儿上大学时对她说:“考虑到现在的离婚率,以及男人更短命的事实,
你有80%的概率会独自生活,不管你有没有孩子要抚养,不管你有没有经济能力。因此,你最好
有自己的职业,有足够的自尊,这样你的价值感就不必依赖于身边的男人。”这些话不是乐观的
话语,不是早点结婚的告诫,不是辈辈相传的鼓励依赖。这位父亲并不享受说这番话。这番话唯
一的优点就是它的真实。
当女人在中年感觉被遗弃时,她的内在小孩很快就会“浮出水面”。这是一次痛苦的经历。如果她
寻求治疗,第一年将用来发泄悲伤和愤怒,克服怀疑,接受我们并没有和世界签下心照不宣的契
约这一事实。在第二年,她将为新生活积蓄能量。如果她缺乏经济独立所必需的教育或工作技
能,她会尽其所能去获得它们。从集体的角度来看,她有充分的理由觉得自己被利用了;在心理
治疗中,她可能会承认自己的无意识共谋。
对许多身处中年之路的女性来说,现在是时候实现与自己的约定了,这是多年前就已发出却被错
过的邀请。当脱下养育者的罩衣,女性必须重新询问她是谁,她想用她的生命做什么。除非她意
识到阻碍自己的各种内在力量,以及从父母和文化中获得的情结,否则她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阿尼姆斯的负能量会侵蚀女性的意志、自信和自我信念。阿尼姆斯作为正能量,代表着权力,代
表着为自己想要的东西而战的能力,代表着生命力的主张。阿尼姆斯作为正能量很少是被赐予
的,它是通过努力得到的。鼓起勇气,重新定义自己,重视亲密关系,但不被关系所限制,这是
中年女性的一项任务。
中年外遇
有时,内心力量会以复仇之势崛起,使我们根本无法招架。据报道,外遇的发生率在50%左右,
男性略高于女性。 我想,他们当中很少有人会在早上醒来时说:“我今天要把我的生活
搞砸,哪怕伤害我的伴侣,伤害我的孩子,失去我为之奋斗的一切。”但这确实发生了。
不管第三者事实上有什么优点,他或她肯定都是投射的对象。正如婚姻是内在小孩需求的主要
载体,当伴侣被证明只是个普通人时,第三者就成了阿尼玛或阿尼姆斯投射的全新对象。就在
我写这本书时,某位知名女演员宣布了她的第八次婚姻(也可能是第九次了)。我衷心祝福
她,但我知道,她这么大年纪了,仍然在投射。她现在选择的是一个比她小20岁的壮小伙。我
还得知一个48岁的男人爱上了一个21岁的女孩。我看见他的小船正驶向尼亚加拉大瀑布,但我
知道说什么也阻拦不了。当然,我没见过这个年轻的女孩,也不知道他的妻子有多唠叨,更不
能想象他是不是感觉重生了。无意识的力量有时比逻辑、传统和法律更要求尊重。
弗洛伊德曾要求他的病人,在分析期间不要做任何重大决定,例如结婚、离婚或换工作。也许
这在理论上是合理的,但生活在继续,情绪在发生,决定刻不容缓,我们必须在现实世界中正
常运转。不管投射会不会消解,不管一个人是否被自己困住,生活从未停止,选择已经做出。
当我为夫妻提供治疗时,如果没有第三者,我总是会松一口气,因为我知道他们还有机会真诚
地处理婚姻问题。如果这段婚姻失败了,我们就直接承认这一点,而不是将问题转移到另一条
轨道上,也就是外遇所体现的投射。如果人们正在经历外遇,我会敦促他们尽量暂停联系,以
切合实际地看待自己的婚姻。有时,这个策略是有效的,丈夫或妻子能够切实地处理婚姻问
题。但大多数时候,我都是在浪费口舌。被无意识支配的个体是不可能注重实际的。
中年外遇的真正力量在于,它会将人拉回到成年早期的黄金时光。我常听到女人抱怨丈夫和一
个甜美的年轻女孩有染,我也看到过一些女性和年长的男人交往。这告诉我们什么?这表明阿
尼玛发展不充分的男性,会被类似水平上的女人所吸引;这还表明阿尼姆斯发展不充分的女
性,会被拥有世俗权力的年长男性所吸引。男人和女人都缺乏成年仪式,无怪乎这么多人在寻
求人生指导,甚至让爱人指点迷津。男人追逐年轻的女性,反映了他们不成熟的阿尼玛;女人
仰慕有地位或年长的男性,是对她们自身阿尼姆斯发展不足的补偿。难怪外遇具有这么大的“神
圣性” (numinosity)。它实际上拥抱了一个人失落的灵魂。然而,外遇往往会带来更多
的悲伤和丧失。睿智的心理治疗师梅·罗姆(Mae Rohm)曾说过:“你所得到的麻烦不值得你这
样做。” 但是,你试着把这话告诉一个正发生外遇的人,试着告诉一个被配偶外遇所伤
害的人,他们才不会相信。
前面讲过,第一个成年期的婚姻模式是追求合一,现在我们明白了,亲密关系究竟有多么复
杂。亲密关系的存在本身就令人惊讶。鉴于强大的无意识力量、投射、父母情结等,一个人怎
么可能会与另一个人诚实地建立关系?一开始,我们可能会说,放眼过去,人们做得挺好;然
后我们被迫承认,根据历史和自己的经验来看,他们做得也不怎么样。亲密关系从来都是一团
巨大的,令人困惑、伤心的混乱。
我倾向于把人看作一个多面体,一个有很多面的球体,而不是作为融合模型的一半在寻找另一
半。即使完美小姐和了不起先生在一起,也不可能将两个多面体的所有面都对齐,最多只能对
齐其中的一些。这是外遇的理由吗?是的!但这是一个坏理由。我知道一些所谓的开放式婚
姻,有些是由极度清醒的人经营的,最后全都以失败告终,部分原因在于,不管协议是多么理
性,人总是有情感的。即使在最理性的契约中,也会存在嫉妒、渴望和竞争。因此,如果多面
体的比喻合理的话,那么我们只能将其中几个面与某个人匹配。诚然,这为结交不同的朋友提
供了理由,但这只有在不涉及爱情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
承认我们是一个多面体,虽然可能威胁到伴侣,但却解放了我们自己,这也可能是发展的契
机。对于处于第一个成年期的人们来说,另一半是最主要的支持来源,多面体模型是一种威
胁。自然地,考虑到内在小孩及其各种需求,解决方案存在于外部,“会有一个‘外人’来治愈和
修复我”。但是,当一个人经历了外遇的兴奋、疲惫,以及最终的沮丧,他可能会质疑这一切意
味着什么。在这么多人都有外遇的情况下,人们必然会说这种模式意义重大。我认为,这种意
义既是弥散的(在情绪上)又是非常明确的(在概念上)。
中年外遇的意义是迫使我们回到过去,拾起自己成长过程中落下的东西。由于未被发展的东西
在意识之下躁动,所以它仍然是未知的。在无意识的神秘扫描中,这些未被发展的东西被投射
到一个“情投意合”的人身上。我们寻求的是完整,是完成。这种对完整性的追求有什么可惊讶
的?但是,你试着把这些解释给一个坠入爱河的人听!外遇会继续下去,因为浩瀚的未知依然
存在。是的,外遇中的第三者也有可能被证明是一个绝妙人选,是真正的灵魂伴侣。如果他或
她没有一些这样的特质,那么投射一开始就不会发生。如果这种新的关系能够幸存下来,那么
我们有可能整合了第一个成年期缺失的东西。我们可能非常幸运,也可能会大失所望。
也许最困难的任务是,学会接受和肯定自己在关系中的分离性。在我们的讨论中反复出现的主
题是,一个人除了对他人做出热切回应,还必须对自己的幸福负责。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我们
获得了更高的独立性,依恋需求仍然存在。外遇能够满足一个人在婚姻中未被满足的需求,而
婚姻则因未被满足的需求而充满怨恨和愤怒。世界上最简单的事就是埋怨他人。有外遇的人经
常会说:“我可以跟你说,但我跟家里那个人没法说。”
事实上,一个人跟伴侣说的话要比跟一个相对陌生的人说的话多。只是婚姻中的对话已经被压
抑、重复和失望所包裹,以至于我们放弃了在伴侣的平凡中遇见“他者”的希望。此外,外遇中的
神秘“他者”无疑吸引了我们的多面体自我中未发展部分的投射。当一个人与自己灵魂的倒影相遇
时,会有一种“上天安排”的感觉,这时,婚姻几乎是没有胜算的。因此,夫妻双方必须有强大的
意志力,从外遇中抽身出来,把那些失去的时光,那些未曾尝试的对话,带回到最初的伴侣关
系中。
我见过太多的人,只有到了治疗室或离婚法庭上,才开始真正分享感受、愿望和从前的伤痛。
与其说婚姻失败了,不如说从未真正尝试过。如果像尼采所说,婚姻是一场伟大的对话,那么
大多数婚姻都不合格。很少有人真正分享自己的内心感受,对另一半诉说自己的心事。人们一
起生活、生儿育女、共同养家,却从未真正理解伴侣的神秘性。这样的局面令人感到无比悲
伤。
婚姻完全有可能进入中年之路的漩涡,如果(我是说如果)夫妻双方愿意再次“分离”,并就这种
分离彼此对话,那么它就会解构和重组。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悖论:要使婚姻水乳交融,首
先必须有更大的分离。婚姻治疗可以解决冲突,识别和纠正不良策略,并制定一项成长的议
程。这些显然很重要,有助于提升婚姻的体验;但只有婚姻中的个体改变了,真正的新生才会
开始。在关系发生转变之前,每个人都必须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个体。一段婚姻不会比身处其中
的任何一个人更好。
因此,中年婚姻的转变包括三个必要的步骤:
(1)双方必须对自己的心理健康负责。
(2)双方必须承诺分享自己的经验世界,不因为过去的创伤或未来的期望而埋怨对方。同样,
他们也要不带防御地努力倾听对方的经验。
(3)双方必须承诺长期保持这样的对话。
这三个步骤要求很高。而另一种选择是,婚姻要么磕磕碰碰,要么解体。敞开的对话是长期承
诺的意义所在。不管有没有结婚宣誓,真正的婚姻都离不开敞开的对话。只有敞开地对话,充
分分享做自己的感觉,同时倾听对方的内心感受,才能实现对亲密关系的承诺。而一个人只有
对自己负责,有一定的自我意识,并有足够的弹性来承受与“他者”的真实相遇,他才能参与敞开
的对话。
爱上另一半的特性是一件非凡的事,因为一个人由此进入了关系的真正奥秘,在这个奥秘中,
一个人被带到了第三个空间——不是你加我,而是我们,是超越彼此的共同体。
父母情结的影响
前文提到,中年之路的特征之一,是个体与父母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我们不仅在新的赋权背景
下与父母打交道,同时还看到了他们的衰落;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学会了把自己与父母区别开
来。也许在中年,没有什么任务比摆脱父母情结更重要了;原因很简单,父母情结强烈地影响
了前面提到的虚假自我,即在第一个成年期形成的临时人格。除非我们意识到第一个成年期的
特征是反应性而不是生成性的,否则我们并不会真正成为自己。
无论一个人的童年经历是糟糕还是美好,这个世界的力量都是“外在的”,在那些大人身上。小时
候,看到父亲从他手上拔出鱼钩,既没有畏惧也没有哭泣,这让我惊讶不已。我得出结论,要
么是成年人对疼痛不那么敏感,要么更有可能是,他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的疼痛。我希望他能教
我那些奇妙的技巧,因为我知道自己多么害怕疼痛。
同样,在对青春期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注意到,八年级过后,那些大孩子突然发生了身体上
的变化,去了一个叫作高中的地方,并对世界有了我所缺乏的了解。我不知道这种神秘的转变
是如何发生的,但我猜想,有人把这些年轻人带到一边,教他们如何成为大人。我偶然发现,
我们需要成年仪式,这些仪式帮助过我们的祖先,却在我们这个时代消失了。读者可能和我一
样失望:我们愉快地进入成年人的世界,却没有得到任何启示,而是发现脸上长满粉刺,遭遇
性困惑,并逐渐意识到大人也不懂任何魔法。
因此,第一个成年期的形成,不是基于我们对自己和外界的了解,而是基于我们对父母及各种
体制的指导或模式的依赖和困惑。正如大卫·瓦格纳(David Wagoner) 在《单面英雄》
( The Hero with One Face )中所写:
我选择了,被告知要选择的:
他们温柔地告诉我,我是谁。
我等待着,不知该学些什么:
此刻,再次失明,宛若初生。
人到中年,必须解决父母情结在几个方面的影响。首先,在最本质的层面上,教养的经验是关
于生活本身的原始信息——它是支持性的还是伤害性的,它让我们感到温暖还是冷酷。父母的
形象缓解还是加剧了孩子与生俱来的焦虑?这就是个体核心焦虑的形成,它是我们所有态度和
行为的基础。
其次,亲子经验是个体与权力和权威的初次接触。人到中年,找到自己的权威是当务之急;否
则,后半生仍被童年的变化无常所支配。我们依靠怎样的权威(规范性价值观)来生活?是谁
在命令我?大多数成年人都花费很多时间来“检查”(checking in),因此,一个人必须努力抓住
内心所有的对白,并使之意识化。一个人要向头脑中无形的存在咨询或请求允许多少次?内心
的对话比人们想象的更根深蒂固、更隐蔽。那个“检查”的“我”是谁?“发号施令”的又是谁?这些
内在的权威,很可能是母亲、父亲或他们的代理人。
这种“检查”的反射性质令人震惊。只有当一个人因某个决定或冲突感到苦恼时,才会注意到它,
进而与之对抗。
如果一个人能够停下来,扪心自问:“此刻我是谁?我有什么感觉,我想要什么?”那么,他就不
是在反射模式中,而是活在当下。“检查”的潜在本质是一个人生活在过去。我认识一个人,每当
他要吐露一些私事或谈论别人时,就会小心翼翼地张望,甚至在私密的治疗会谈中也如此。他
称这是“德国式回望”(the German glance)。他在纳粹时代长大,像他同时代的人一样,学会了
在说任何私事或可能违反权威的话时都要回头张望。尽管已经过去了50年,离他年少时的居住
地有四千英里,但他的身体和心理仍然记得要“检查”。可见,我们都会反射性地向过去生活中的
权威“报到”。
宗教指令对许多人起着这样的作用,他们充满了罪疚感,因不能自由地表达情感而显得极不成
熟。我曾见过一些专制和无意识的神职人员,他们对人们造成的伤害可能比带来的益处更多。
罪疚感和被社群排斥的威胁,对个人的发展具有强大的威慑作用。[古人认为流放是对一个人最
严厉的惩罚,这绝非偶然。正统的犹太人吟唱卡迪什(Kaddish),为死者祈祷,为离开社群的
人祈祷;阿米什人(Amish)则“回避”那些离群的人。]从群体中被流放是来自权威的巨大威胁。
没有一个孩子能够承受没有父母的认可和保护,所以他会反射性地学会抑制自然冲动。这种对
被排斥的焦虑的防御,被称作“罪疚感”(guilt)。失去家庭的威胁如此之大,失去父母的恐慌如
此之强,以至于所有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持续地“检查”。不管我们的身体有没有移动,“德国式回
望”都发生在我们身上。
如果没有能力活在当下,做一个自我定义的成年人,那么一个人就仍是过去的囚徒,与自己的
本性和成年人格相去甚远。意识到这种不真实性,起初会令人沮丧,但最终会让人解脱。承认
内心对外界权威(投射到了伴侣、老板、教会或国家身上)的依赖,是多么令人羞愧。即使在
今天,选择自己的道路也常常显得可怕。正如一位分析家最近说道:“我曾被告知,考虑自己就
是自私。直至今天,当我提到‘我自己’或使用‘自我’这个词时,我仍然感到内疚。”
与处理父母情结和争取个人权威相对应的是,一个人把自己的身份认同投射到子女身上。许多
父母都将他们未曾实现的生活投射到孩子身上。前面提到有许多表面上望子成龙和望女成凤的
父母。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 自杀后,她的母亲甚至试图经营女儿的事
业。孩子经常从这样的父母那里收到矛盾的信息。“你成功了会让我高兴,但不要太过成功,以
至于把我抛在脑后。”因此,孩子体验到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
父母对同性孩子的身份认同通常是最强烈的,尽管他们经常会无意识地通过异性孩子来实现阿
尼玛或阿尼姆斯。正如盖尔·戈德温(Gail Godwin) 在《忧郁父亲的女儿》( Father
Melancholy’s Daughter )中描述的那样,许多男孩不得不承担母亲的抱负,许多女孩不得不背负
父亲的阿尼玛。这种投射的极端情况表现为性虐待,在这种情况下,父母的阿尼玛或阿尼姆斯
的功能是幼稚的。
父母是充满爱心地养育和保护子女,还是不恰当地借由孩子来生活,两者之间似乎只有一线之
隔。正如荣格所指出的,孩子最大的负担就是父母未曾实现的生活。例如,当父母的生活被焦
虑所阻碍时,孩子会发现自己也很难克服阻碍,甚至可能会无意识地忠于父母的发展水平。但
是,过着自己生活的父母就不会无意识地嫉妒,也不会将期望和约束投射到孩子身上。父母越
个体化,孩子就越自由。诗人E.E.卡明斯(Edward Estlin Cummings) 描述了这样一种
关系:
没有什么比真实更重要的了
——我说,尽管仇恨是人们呼吸的原因——
因为我的父亲活出了他的灵魂
爱是他的全部,胜过一切。
林肯曾说过:“既然我不愿做奴隶,我也就不愿做主子。” 我们希望父母赋予我们做自己
的自由,我们也就必须给孩子这样的自由。我们为做自己而努力奋斗,常常希望父母能意识到
我们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分道扬镳。所以,我们必须给予孩子自由。据观察,青少年与父母之间
的摩擦是打破相互依赖的自然方式。当孩子上大学、找工作或结婚时,虽然大多数父母都感到
很高兴,但许多人仍然感到丧失了一部分自我,而这部分与孩子紧密相关。我认识一些父母,
他们每天都给已成年的子女打电话,有时一天打好几次。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相互依赖,而且
对子女没有任何好处;它阻碍了后者对第一个成年期的掌控。后者对第一个成年期的掌控。
许多父母对孩子感到失望,因为他们没有上对的大学、没有和对的人结婚,或者没有拥护正确
的价值观。父母越是将孩子视为自己的延伸,而不是可以独辟蹊径的生命,就越容易感到失
望。如果我们真的爱孩子,能为他们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尽可能地让自己个体化,这样他们
才能自由地做同样的事。
与流行的假设相反,分析师并没有制订患者应该如何个体化的计划。分析师试图促进患者的内
心对话,相信自性的声音将会显现,并希望患者相信自己的内在真实。这种方法将患者视为值
得尊重的人,能使神秘的召唤现身,而这种召唤的展开就是生命的目的。我们也应该如此对待
孩子,他们值得与众不同,他们对我们没有任何义务;他们不是来照顾我们的,我们才是要照
顾自己的。就像在婚姻中一样,我们的任务是爱上另一半的特性。
为自己没有成为完美父母而感到内疚,或者试图保护孩子免受生活的考验,这对孩子都没有好
处。渴望控制孩子,让孩子活出我们未竟的人生,让孩子复制我们的价值体系,这些都不是
爱;这是自恋,它阻碍了孩子的人生旅程。一个人个体化已经很难了,为什么他还要承担我们
的需求?在中年之路上对孩子放手,不仅对他们有帮助,对我们来说也是必要的,它为我们进
一步的个人发展释放了能量。
人到中年,另一个必须面对的父母情结的方面是,我们与父母的关系如何影响自己的亲密关
系。孩子所接触的亲密关系模式具有关键性的影响。青春期的孩子通常会认为,他或她会选择
与父母不一样的伴侣,采用不同的相处模式,从而避免父母婚姻的困境。再往深处猜,只要父
母情结在起作用,人们就会选择同一类型的人,或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只有随着时间的推
移,这一点才会变得明显。
因此在中年时,意识到自己比想象中更像父母,自己的关系遵循着熟悉的模式,我们会感到震
惊。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年时改变自己,可能需要认真审视自己的亲密关系。我们内在的改变
往往需要关系中的附带变化,无论伴侣是否有相同的倾向。可悲的是,有时父母情结的影响过
于深刻,以至于不可避免地“污染”了婚姻。(父母情结对婚姻的影响,类似于军方描述平民伤亡
时所说的“间接伤害”。)
回想一下荣格关于情结的概念。情结代表了心灵中充满情绪的能量群,部分从自我中分离出
来,因此可以自主运作。情结本质上是一种情绪反射,其影响力取决于源头的强度或持续时
间。尽管我们倾向于关注生活中消极的情结,但也有些情结是非常积极的。毋庸置疑,父母情
结非常强大,因为他们在早期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许通过一位诗人的作品,可以戏剧
性地说明积极和消极的父母情结。
许多现代诗人已经抛弃了文学前辈所持有的观念,即他们可以表达整个时代的精神。相反,他
们倾向于反思自己的个人生活,在那里寻求某种意义,并希望通过文字的力量来触动他人的生
活。这样的诗通常被称为“自白”(confessional),既因为个人而私密,又因为人类相同的境况而
普遍。现在,让我们以美国当代诗人斯蒂芬·邓恩(Stephen Dunn) 的三首诗为例。第一
首是《家务事》(“The Routine Things Around the House”):
母亲去世时,我想,
我要写一首悼亡诗了。
真不可原谅
但后来我原谅了自己
就像被母亲深爱过的儿子
能做的那样。
我凝视着棺材
知道一辈子很短,
要是有几辈子多好
重温甜蜜的回忆。
很难确切地知道
如何让自己走出悲伤,
但我记得12岁时,
1951年,在这个世界
展露面目之前。
我问母亲(颤抖着)
能否看她的乳房
她带我进了房间
没有尴尬或害羞
我盯着它们看,
不敢要求更多。
多年后的今天,有人告诉我
没有母爱的巨蟹座人
注定不幸,而我,一个巨蟹座,
再次感到福分。多么幸运
曾有位母亲
给我看了她的双乳
那时候,我同龄的女孩
乳房发育得各有千秋,
多么幸运
母亲没有挫败我
一切恰到好处。
如果我要求碰触,
或许还会吮吸,
她会怎么做?
母亲,已故之人
她让我能够
轻易爱上女人,
这首诗
献给
我们逗留的地方,献给
我们完美的缺憾
献给你守口如瓶,
在屋里屋外
开始做家务。
在这里,邓恩显然是在处理母亲情结,因为他不仅记得过去,而且能够看到它对现在的影响。
意识到这些经历及其无声的影响,是中年之路上的一项必要任务。
在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母亲在许多方面的积极影响。首先,在感受到母爱之后,诗人
能够接受甚至原谅自己。只有得到父母的肯定,我们才能够爱自己。其次,诗人意识到他对女
性的初次体验如此积极,因此他可以将这种信任和爱过渡到其他女性身上。很明显,他在这里
踏上了危险的境地,甚至作为一个孩子冒险进入了禁区。接触“他者”就像造访一个陌生的星球。
如果一个人的初次接触得到了支持和鼓励,那么以后的接触大抵也会如此。母亲情结的前两个
影响是被爱的体验和与“他者”的神秘相遇,第三个是母亲所具有的智慧。例如,她知道在不破坏
神秘感或隐私的情况下,如何尊重孩子的求知欲。还需注意的是,诗人回忆的是基于一个普通
的情境,这意味着其非创伤性以及在心理上积极的影响。
除了维护孩子的安全,父母最深层的角色是原型。也就是说,无论孩子在父母身上体验到什
么,父母都是孩子的榜样,并激活了孩子自身相似的能力。
自然,父母往往也是“不完整”的父母的孩子,只能示范和传递自己有限的经验。因此,受伤的、
残缺的灵魂遗产代代相传。孩子的两大需求是养育和赋权。养育意味着这个世界为我们服务,
与我们达成妥协,在身体和情感上支持和喂养我们。赋权意味着使我们能够迎接生活的挑战,
并为自己渴望的东西而奋斗。虽然父亲或母亲都可以提供养育和赋权,但在原型上,养育与女
性原则有关,赋权与男性原则有关。
在一组名为《遗产》(“Legacy”)的长诗中,邓恩追溯了他父亲在家族故事(mythos)中的角色
演变。第一首诗的标题是《照片》(“The Photograph”),代表了孩子与潜在赋权原型的相遇。
我父亲在“斯塔恩船长” ,
大西洋城的一家餐厅。
那是1950年,
我11岁,也在那里。
他卖了很多冰箱,
比任何人都多。所以我们在那里,
一切都是自由的。
在屋里的人开始窃窃私语之前,
在传唤证词之前,
在生活被毁之前。
父亲在微笑。我也在微笑。
在我们面前,
有一碗小虾。
我们穿着相同的衬衫,
短袖上有小帆船。
这是在粗俗和幸福之间
开始产生差异之前。
很快我会起身
弟弟仍挨着他坐。
妈妈会按下快门。
我们相信公平,
我们依然相信美国
就像祈祷,就像圣歌。
虽然父亲头发逐渐稀疏
但从他的脸色看,
什么也阻挡不了他。
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的怀旧之情(nostalgia)。相机捕捉到了一个瞬间,那个瞬
间的真相,并不是唯一的真相,但仍然是个真相。这个世界该如何衡量?对诗人艾略特来说,
“我们用咖啡勺、我们唯一的纪念碑、混凝土公路和无数丢失的高尔夫球,来衡量我们的生命”
。而对这位父亲来说,对这个孩子来说,是比别人的爸爸卖掉更多的冰箱。即使失去了
童年,失去了虔诚的美国,但“从他(父亲)的脸色看,什么也阻挡不了他”。我们能感觉到父亲
将生活的真相传递给了孩子,即使母亲通过揭示神秘使这个未来之人得到解脱。
没有目睹过这些神秘(真相)的孩子步入成年后会有多么不同呢?当父母的榜样是谨小慎微、
恐惧、偏见、依赖、自恋和无能为力时,子女的第一个成年期就会被这些信息所支配,或者不
顾一切地寻求补偿。将自己的认知与父母的信息分开,是我们进入后半生的必要前奏。
邓恩的另一首诗阐明了梳理关键问题的任务。“我在哪些方面像我的母亲?”“我与母亲有哪些不
同?”“我有多像我的父亲?”“我与父亲有何不同?”“谁对我的影响更大?”“事情发生时,另一个
人在哪里?”“若在不同时空,我的人生旅程会有何不同?”这些都是必要的问题。答案不一定立
即呈现,因为激发我们的东西往往是无意识的,我们只能通过重复、治疗或顿悟来辨别其中的
模式。在十年后写的第三首诗《无论如何》(“Regardless”)中,邓恩开始了这一过程。
有一次,飓风来袭
父亲带我去洛克威
看大海的翻腾,
这让母亲很生气,她的爱
是周全的,是袒护的。
我们看到木制防波堤崩塌,
看到海水涨到了木板路上,
感受到了海浪的狂野。
那天晚上:晚餐时很沉默
一场更冷、更熟悉的空气风暴来临。
父亲总是因令人愉快的错误
惹来麻烦。
母亲警觉地等着它们,
就像被压迫者
等待他们的历史性时刻。
工作日,六点过后,我会骑着自行车
到舰队街小酒馆,
叫他回家吃晚饭。他所有的朋友
都在那儿,兴致勃勃的孤独的爱尔兰人,
充满了欢声笑语。
他在那儿令人羞愧,催他回家令人羞愧。
那时我只是一个小男孩
一个学会了爱上风的人
无论如何,风都会走自己的路。
我以为当时发生的情况
就是伤害。
我们再次看到,父亲为孩子揭开了生活的奥秘,在风暴肆虐的大海面前,父亲是精神领袖,指
引我们走近奇观。母亲的保护意识虽然周全,但也意味着束缚,是另一种形式的爱,也是孩子
所需要的。于是,两种形式的爱(eros)在餐桌上碰撞,孩子夹在中间。飓风的隐喻暗示了其他
更黑暗的风暴。因此,孩子夹在父母中间,叫父亲回家令人羞愧,成为传话筒也令人羞愧。羞
愧是孩子内化的记忆,关于夹在父母之间、爱着双方、需要双方的记忆,是无论如何也要跟随
内心的风的记忆。多年以后,这些发生的事情被识别为伤害。我们要问:伤害了什么?有什么
影响?这在今天是如何影响你和其他人的?其他的诗也揭示了其他的问题。
只要一直保持无意识状态,我们就会继续背负着父母的悲伤、愤怒或未实现的生活。羞愧也是
如此,因为羞愧意味着一个人觉得自己与他人的创伤有牵连。最后,我们只能根据一个人的品
质来评判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自己和他人没有造成伤害。在斯蒂芬·邓恩的这三首诗中,我
们看到了积极和消极的父母情结在起作用。再次强调,情结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过
去。我们过去没有意识到的东西,会渗透到现在,会决定我们的未来。我们感受到被滋养的程
度,直接影响了我们养育他人的能力;我们感受到被赋权的程度,直接影响了我们过自己生活
的能力。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冒险建立关系,乃至想象它是支持性的而不是伤害性的,这是我
们和父母情结的有意识对话的直接结果。
许多人的父母都曾受过伤害,他们无法满足我们对养育或赋权的原型需求。在中年时期,研究
这段个人的历史很有必要。我听到有人说,心理治疗就是把自己的痛苦归咎于父母,其实不
然;我们对人类心理的脆弱性越敏感,就越有可能原谅父母造成的伤害。最严重的罪行是保持
无意识状态,这是我们无法负担的罪过。无论在过去的历史中发现什么创伤和缺陷,我们都有
义务养育自己。
自然,要实现我们内心在原型上没有被激活的东西非常困难。但没有巨大的风险,任何事都难
以完成;因为我们必须冒险进入一个充满恐惧的未知世界。如果我经历过父母的背叛,就会发
现很难去相信别人,因此也更难冒险建立关系。我可能会害怕异性。我可能会破坏自己与他人
的关系,甚至从一开始就做出错误的选择。如果我的价值没有得到肯定,我就会害怕失败、避
免成功,让自己陷入一个不断逃避生活任务的循环中。即便我觉得脚下无路可走,仍然必须步
步向前,一步一个脚印,直至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如果不辨别这些重要信息的来源,不辨别它们源于别人的生活,我们就不会取得任何成就。我
们的任务是更充分地生活,如果没有来自早年的明显支持,在某种程度上便不会实现。荣格曾
经说过,除非我们能够将父母视为其他成年人,否则我们无法长大;父母在我们的生命中肯定
是特别的,也许还曾受过伤,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只是那些踏上或没踏上自己心灵旅程的人。
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旅程,这足以让我们超越个人历史,发挥全部的潜能。
职业世界:工作与使命
到了中年,没有人需要被提醒经济现实。人到中年,我们肯定都听到过这样的陈词滥调:金钱
不是万能的,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但是,就像第一个成年期的其他投射一样,金钱到头来
只是流通的金属或纸片,虽然有用,但在任何终极意义上都不值一文。因此,每个人都背负着
经济任务和经济创伤。对许多辛苦持家的女性来说,经济自由是她们所没有的权利。对许多中
年男性来说,承担着孩子的正畸账单和大学学费,经济就像一件紧身衣,根本脱不下来。
为了满足这些现实,大多数人不得不一辈子工作。对一些人来说,工作是一种情感寄托;而对
另一些人来说,退休的梦想就像沙漠中的绿洲一样在招手。弗洛伊德认为,工作是健康的必要
组成部分。但什么样的工作才算呢?工作和使命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工作是我们为了养活自己
而不得不做的事情。使命(vocatus)则是我们被召唤用生命能量去做的事情。感受到创造力是
个体化的必要部分,而不回应召唤则会损害我们的灵魂。
实际上,我们并没有选择使命,而是使命选择了我们。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如何回应它。使命
可能与挣钱毫无关系。有人可能被召唤去栽培其他人。在不提倡艺术的时代,有人可能被召唤
成为一名艺术家,尽管遭遇忽视,甚至被拒绝,但仍然坚持不懈。
卡赞扎基斯(Kazantzakis) 的小说《基督最后的诱惑》( 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
)就着力描写了这种困境。拿撒勒人耶稣原本只希望像他父亲一样,做一个为罗马当局制作十
字架的木匠。他想娶抹大拉的玛丽亚,住在郊区,驾着健壮的骆驼,生两个孩子。但他内心的
声音,也就是使命,却召唤他去另一个地方。体验到被父亲抛弃的凄苦后,他面临的最终诱惑
是放弃自己的使命,成为一个普通人。当他想象以这种方式生活时,他意识到他会背叛自己,
背叛自己的个体化。当他对“使命”俯首称臣时,耶稣最终成为基督。因此荣格说,正确地模仿基
督,不是像从前的拿撒勒人那样生活,而是完全地活出个性,活出使命,就像耶稣活成基督那
样。 [就如圣保禄(St.Paul)所说:“我没有成为基督,但基督活在我心中。”]
职业很少是一条笔直的道路,而是充满了曲折和坎坷。有媒体报道,在最近任何一年中,都有
近40%的美国人更换职业;不只是换工作,而是改变职业生涯。 当然,这种流动性和转
型,在一定程度上是经济机遇的结果,但也有许多人是为了改变他们的生活。今天,我们活得
更久了;没有什么能阻止一个人从事多种职业,每份职业都激活了多面体自我的一个方面。
当然,经济上的必要性不能忽视,但也要考虑自己的选择。一个人可以在经济奴役中度过一
生,也可以说:“这是我谋生的方式,是用来支付账单的;那是我补给灵魂的方式。”例如,我认
识一个有哲学硕士学位的人,他每天从凌晨3点到上午8点负责送报纸。这是一份无须动脑只为
支付账单的工作,但在一天剩下的时间里,他是个自由人。他在工作和使命之间找到了平衡,
且两者都为他服务。
有些人能够把工作和使命结合起来,尽管他们可能要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有时强烈的使命甚至要求牺牲自我的欲望。但对使命来说,我们无法提出要求,只能对其臣
服。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来自“俯首称臣”。自我并不主宰生活,它所知甚少。正是自
性的神秘,令人惊讶地指引我们变得完整;而我们决定如何使用自己的能量,在生命旅程中起
着重要的作用。
当认识到并撤回金钱和权力所代表的投射时,我们就不得不扪心自问:“我的使命是什么?”这个
问题必须被时常提出,我们也必须虚心听取答案。在个体化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被召唤使许
多种能量现身。正当达到一定程度的稳定时,我们可能会受到由内而外的破坏,并被召唤转向
新的方向。无论我们的社会负担如何,无论我们的经济约束如何,我们都必须不断地问自己:
“我的使命是什么?”然后,依靠计划、代价和足够的勇气,我们必须找到完成使命的方法。
牺牲自我以及它对物质享受和安全感的需求,无疑令人痛苦,但这种痛苦远不及我们回顾生活
时对于没有回应召唤的后悔。我们的使命是尽可能地成为自己,我们的任务是找到实现的方
法。评判我们的标准,不仅有内心是否善良,还有我们是否勇敢。放弃奋力争取的安全感也许
令人恐惧,但它根本比不上否认我们自身使命带来的恐惧。灵魂有它自己的需要,工资和福利
并不能满足它。
劣势功能的显现
现代世界的复杂性催生了各个领域的专家,以更好地满足其需求。因此,从小学开始,我们就
根据能力和资质被分组,并被引向越来越专业化的方向。我们在专业化上走得越远,人格受到
的损害就越大,灵魂也就越迟钝。在商业和专业培训的重压下,人文科学的重要性被大大削
弱。因此,我们逐渐被狭隘的学术背景所束缚。荣格对神经症最简单的定义是“自我分裂”,即人
格的片面性。 这一定义将涵盖我们所有人,特别是因为之前讨论过的后天人格的反应
性,也因为西方社会教育过程的本质。我们接受的训练越多,人格就越狭隘。
1921年,荣格出版了一本书,描述了八种人格类型,说明了我们处理现实的不同方式。
他的术语“内向”和“外向”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语言。思维、情感、感觉和直觉这四种功能,人皆
有之,只是比例不同。所谓的优势功能,是我们为了适应现实而本能地求助的功能。类型学
(typology)似乎有一个遗传基础,尽管肯定会受到周围人的影响。内倾或外倾的态度描述了我
们倾向于将现实视为“内在”还是“外在”来处理。因此,一个外倾感觉型的人,很可能会被外部世
界所吸引,成为一名工程师或厨师;而一个内倾思维型的人,可能会成为一名学者,但绝对不
擅长做推销员。
我们的优势功能通常很早就出现了,而且我们都倾向于尽可能地使用这些功能。此外,如上所
述,我们很快就会根据我们所擅长的领域被分类,并进一步蜷缩进自己的专业领域。我们接受
的训练越多且越成功,视野和人格也就越狭隘。社会为此奖励我们,而我们也串通一气,因为
遵循我们的优势功能,比使用那些笨拙的或回报较少的功能更容易。
优势功能的概念并不意味着更好,仅仅意味着更发达和更多地被利用。劣势功能是指人们最少
求助的处理现实的模式,也是让一个人感觉最不舒服的模式。一个思维型的人不是没有情感,
但审视事物的含义,如何理解它,如何处置它,是思维型发挥作用的自然方式。这个人的情感
生活会以更原始、更简单的方式展现出来。
在中年之路上,心灵中不太发达的部分会要求得到关注。荣格认为弗洛伊德是一个情感型的
人。他用聪明的头脑想出许多合理化的方法,来为他充满激情的情感辩护。当他的同事提出异
议并离去时,他认为他们是精神分析的叛徒。他没有冷静地阐述他的理论并将其交给众人评
判,而是用它们来捍卫对生活的情感导向。与之相反,荣格是一个外倾直觉思维型的人,他的
思维范围涵盖了精神分裂症、炼金术和飞碟等主题。他拥有直觉型的“发散思维”,但缺乏感觉型
的顺序逻辑。为了增进他的感觉,他烹饪、雕刻和绘画,所有这些都旨在将劣势功能带入意
识。
人到中年,我们会遇到很多苦恼,有些是外在的,有些是内在的。部分内在的苦恼源于这样一
个事实:我们和社会串通一气,忽视了个人的完整性。我们在容易的事情上就“驾轻就熟”,我们
被奖励的是生产力而非完整性。在梦境中,我们活出了人格的另一面,因为劣势功能是通往无
意识的活板门。如果我们要作为个体发展,如果我们要加强人际关系,就必须认真对待类型学
的问题。
荣格的类型学理论不仅仅是另一种将人归类的方式。类型学的知识主要在两个方面对我们有帮
助。首先,人与人之间冲突的最大原因是他们根据不同的类型导向而行动。尼尔·西蒙(Neil
Simon) 的经典话剧《古怪的一对》( The Odd Couple )讲了一个老生常谈的笑话,它
基于两个对立类型的相互对抗。主人公奥斯卡(Oscar)和菲利克斯(Felix)处理现实的方式截
然相反:一个人认为凌乱的房间是一片狼藉,另一个人则认为所有的东西都触手可及;两个人
都坚信自己是正确的,而另一个人是固执己见。众所周知,人际关系尤其是婚姻,会因不同的
性格类型而受到困扰。认识到伴侣可能是另一种类型的人,可以提升我们的善意,并大大减少
误解和紧张。
对一个人的优势或主导功能的了解,也是对一个人处理现实的劣势或不足的了解。它告诉我
们,为了更好地适应外部世界和平衡心理,需要发展自己人格的哪些方面。具体来说,我们需
要能够完成那些通常我们会避免的任务,比如说经常要求伴侣为我们打掩护的事情。
在任何关系中,我们都应该去问:“我期待这个人替我去做些什么?”这个问题不仅适用于内在小
孩的情感议程,也适用于类型学的问题。认识到相互依存的关系,其意义远甚于分清谁割草、
谁管账等琐事。它的意义在于让我们能够自给自足,并且能为另一半的特性喝彩。
在中年之路上,看到成功的一面是如何禁锢和束缚整个人的,这是很有用的。例如,慢跑和积
极参加运动,不仅仅是应对压力的一种手段,它们还代表了在办公桌前度过一周后,再次与感
官世界取得联系。对于体力工作者来说,心灵的生活则可以唤醒他的劣势功能。一开始,这个
不太适应的过程会让人觉得别扭,但最终,心灵会产生一种更坚实的幸福感。
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个平衡心理发展的过程不能指望老板甚至家人的合作。因此,我们更需要
在这里或那里挤时间。当爱好被看作用于滋养灵魂而不是充实时间时,我们可能会更认真地寻
找常规运作之外的替代方式。然而,对于尝试新方向而非遵循老路的担忧,可能会阻止我们为
被忽视的心灵部分提供能量,无论其潜在的回报多么丰厚。
重新找回那些因专业化、忽视或禁止而被遗弃的自我,这是我们在中年之路上与自己相会的一
部分。对类型学的考虑远不止告诫我们要培养一项爱好。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使过于片面的
人格恢复平衡的唯一方法。
阴影入侵
前面谈到,自我为了应对社会化,为了获得人格面具而花费了巨大的精力。人格面具代表了呈
现给外部世界的必要面孔,它也保护着我们的内心生活。但是,正如对优势功能的依赖代表了
一种偏倚,人格面具也只是自性的一个碎片。人格面具在处理外部现实时是必要的,但与此同
时,更广阔的、未被探索的心灵在等待着被发现。
读者应该记得,阴影是指个体身上被压抑的一切。我们在某个特定的自我形象上投入越多,我
们对现实的适应就越片面。我们对中年生活投入越多的安全感,阴影的入侵就越有必要,也越
令人不安。
大多数人都会为自己做过的事情感到窘迫。也许是陷入婚外情、滥用药物,或是离开那些依赖
我们的人。谁没有在凌晨4点醒来,发现床脚有个龇牙咧嘴的魔鬼呢?我们所有的反常行为都代
表着对更多生机和新生的盲目追寻,尽管它们的后果可能对自己和他人是有害的。如果我们足
够诚实,就能分辨自己的自私、依赖、恐惧、嫉妒,甚至是破坏力。这不是一幅美丽的画面,
但比我们光鲜的人格面具更加丰满,更有人情味。人类最睿智的话语之一出自拉丁语诗人泰伦
斯(Terence) 之口:“我是人类,人类的一切对我来说都不陌生。” 当我们把这
句格言用在自己身上时,它是令人不快的。
阴影不应等同于邪恶,而应等同于被压抑的生命。正因如此,阴影蕴藏着丰富的潜能。意识到
阴影,会让我们更有人情味,更有趣味。一个没有阴影的人是非常乏味和无趣的。愿意让我们
最黑暗的冲动、被压抑的创造力浮出水面并得到承认,是整合它们的前提。负面的阴影内容,
如暴露、欲望、生气等,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表现出来,可能是破坏性的,但如果有意识地予以
承认和引导,它们则可以提供新的方向和新的能量。
具体来说,无论是无意识行为,对他人的投射,还是抑郁或躯体疾病,阴影都会显现其中。
阴影体现了所有未被允许表达的生命。它体现了我们失去的敏感,这种敏感一旦被否认,我们
便会被感情牵着鼻子走。它代表了我们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一旦被抛弃,我们将陷入厌倦和
衰弱。它体现了我们的自发性,这种自发性一旦被压制,我们的生活将变得僵化和乏味。它代
表了一种尚未被利用的生命力,比我们有意识的人格更加强大,而它一旦被阻挡,将会导致我
们的活力和热情的减退。
人到中年,有意识地与阴影相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不管怎样都会隐秘地运作。我们必须审
视自己嫉妒和讨厌别人什么,并承认那些只是自己的投射而已。这有助于防止我们因自己未做
之事而责备或嫉妒他人。它鼓励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生命潜能只被挖掘了一小部分,而我们常
常过于自鸣得意,对自我的成就过于自信。它还揭示了能量、创造力和个人发展的其他来源。
通过与自身的阴影对话,我们可以消除对他人的敌意或嫉妒,而这些来源于我们的投射。过好
自己的生活已经够难了;如果我们专注于自己的个体化,而不是纠缠于别人的事务,每个人都
会更加舒适。
如果生命的意义与意识和个人发展的范围直接相关,那么中年时期的阴影入侵就是必要的,并
且具有潜在的治愈作用。我对自己了解得越多,就可以发挥更多的潜力,我的个性就会更加丰
富,我的生命体验也会更加多彩。
第四章
文学案例研究
但丁曾说:“在人生的中途,我迷失了方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黑暗的森林。” 然后,
他开始了精神朝圣之旅,修正自己生命的意义。
在本章中,我将讨论一些文学案例,而不是临床案例。正如亚里士多德在2500年前所说,艺术
有时比生活更清晰,因为艺术包含了普遍性。 艺术家能够像但丁一样,坠落至地狱,然
后带着旅途中的故事归来,以一种特别清晰的方式呈现我们的处境。我们不仅会去认同一个特
定的角色,还会将其看作人类普遍处境的戏剧化表现。既然我们共享了相同的处境,就可以从
他们的局限、洞见和行动中了解自己。
诗人艾略特曾指出,我们唯一优于过去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容纳过去,并因过去而博大。
换句话说,通过文学和艺术,我们可以容纳人类所面临的更多可能性,并拥有进一步成
长和发展的空间。举个例子,哈姆雷特必须去念为他而写的台词。我们都有哈姆雷特情结,即
知道应该做某事,却做不了。但与哈姆雷特不同,我们有机会通过意识来改变剧本。
《浮士德》与《包法利夫人》
19世纪初期歌德的《浮士德》和中期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这两部截然不同的经典作品,
戏剧化地描述了一个人的困境:这个人的成年早期充满着各种投射,到中年时却陷入了困惑、
沮丧和惆怅。
博学的浮士德体现了文艺复兴的理想,即掌握了丰富的知识。他精通法学、哲学、神学和医
学,但他却说:“尽管我满腹经纶,也并不比从前聪明。” 凭借他的优势功能——思考,
浮士德达到了人类学习的顶端,尝到的却不是甘甜,而是苦涩。有多少首席执行官(CEO)和
他一样感到失望?他获得的成就越多,他的劣势功能和情感就越被压制。他的情感——思维有
多复杂,情感就有多原始——最终咆哮而出,使他陷入深深的抑郁之中。他的学识令人惊叹,
但他的阿尼玛却备受压抑。他的抑郁如此严重,以至于他不止一次考虑自杀。他意识到内心有
两个灵魂在斗争,一个渴望创作出绝妙的音乐,另一个则被平庸和杂务所束缚。在这个极度紧
张的时刻,在一个现代人会精神崩溃的时刻,梅菲斯特找到了浮士德。
在歌德的笔下,梅菲斯特并不邪恶,而是体现了浮士德的阴影。“我是部分的一部分,部分原本
是大全;我是黑暗的一部分,黑暗孕育了光明。” 梅菲斯特将阴影描述为整体的一部
分,它被忽视和压抑,却是最终带来整体的辩证所必需的。
歌德的《浮士德》内容极其丰富,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解读,其中之一便是中年自我与其分裂部
分的对话。浮士德从自杀的边缘被拉了回来,他与梅菲斯特打赌,而不是约定——他们将踏上
体验世界的神奇之旅。因为浮士德代表了人类对求知的永恒渴望,所以他说,只要他在旅程中
有朝一日感到永远满足,梅菲斯特就可以拥有他的灵魂。
正如我们所知,无意识的东西总是折磨内心或者向外投射。浮士德最初处于有自杀倾向的抑郁
状态,他与阴暗的梅菲斯特的相遇是一次重生的机会。但他必须首先进入自己的内心,体验在
片面的第一个成年期中被压抑的一切。
浮士德的核心遭遇是与他的阿尼玛迟来的相会,后者是他内在的女性特质,是情感、纯真和欢
乐的中心,其外在形式是一个名叫玛格丽特的淳朴农家女孩。她对这位知名学者的广博知识感
到震惊,而浮士德也被她迷住了。他用通常表达宗教情感的词语来描述她,他对她的喜爱如同
青春期的热恋。这表明了在这位学者的教育中,阿尼玛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他们之间复杂的关
系导致了玛格丽特的母亲中毒,兄弟被谋杀,而玛格丽特也最终精神崩溃。充满罪恶感的浮士
德,被梅菲斯特带去探索更大的世界。
这种肤浅的情节概括有点像一部以浮士德为反派的肥皂剧。的确,在引诱和毁灭玛格丽特的过
程中,浮士德绝不是无辜的,但他的无意识程度和中年变化的意义才是我们的关注点。就此而
言,故事揭示了一个人以牺牲他的阴影和阿尼玛为代价,发展了他的优势功能,即他的聪明才
智。阿尼玛没有充分发展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就像中年外遇经常表现的那样。我们不知道的东
西会伤害我们自己,也会伤害他人。浮士德并非不道德,但他在无意识中具有破坏性。
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一个人的每个部分会一起成熟。西方社会在核毁灭和延长寿命方面突飞猛
进,但道德成熟的脚步却滞后不前。同样,浮士德在外部世界中的角色大获成功,但他的内心
生活却遭到忽视。与他的聪明才智相比,他的阿尼玛是无意识的、原始的,所以后者表现为一
个淳朴的农家女孩。这种新生的迫切需要,最初以一种准宗教的形式呈现,实际上是要求把被
忽视的女性特质带入意识之中。每个人都很难认识到自己所需要的是内在的疗愈。在外面的世
界里寻求安慰和满足要容易得多。
浮士德的困境让人想起了美国现代作家约翰·契弗(John Cheever) 的短篇小说《乡居丈
夫》(“The Country Husband”)。一个商人在一次飞机失事中幸存下来,发现他的城郊生活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死亡的气息唤醒了他的阿尼玛。他对妻子和她的朋友大发脾气,爱上了青
春年少的保姆,并跑去接受心理治疗,然后被告知自己正遭遇中年危机。诊断结束之后,他有
了一个爱好,在故事的结尾,他在地下室里摆弄木头。在他的内心深处,没有任何问题得到解
决,没有任何东西被了解或整合;就像行星在太空中旋转,轨道一成不变。
浮士德和契弗笔下的主人公都在中年时遭遇了抑郁和死亡恐惧;两个人都通过一个年轻女孩寻
求阿尼玛的治愈。两个人都在受苦,却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正如荣格所说,神经症是一
种尚未发现其意义的痛苦。我们与中年的相会既包含痛苦,也包含对意义的追寻。然后,成长
才成为可能。
在福楼拜的书中,艾玛·包法利(Emma Bovary)就是那个农家女孩。当她见到当地医生查尔斯·
包法利时,便设法诱惑他,从农场搬到了他的小镇上。她把一切投射到婚姻和地位上,期盼自
己从平凡中得到拯救。但婚后不久,她就怀孕了,并对乏味的丈夫感到厌倦。受19世纪法国天
主教文化的限制,她既不能堕胎,也不能离婚,更不能像几十年后易卜生笔下的娜拉那样离家
出走。她阅读爱情小说(相当于今天的肥皂剧)消磨时间,在脑海中幻想着自己的情人,期待
他们把她从平庸的生活带入上流社会。她怂恿查尔斯做了一个复杂的手术,不幸以灾难告终;
她开始了一系列的外遇,并借钱来支持她疯狂的消费行为。她的阿尼姆斯的发展,首先投射在
查尔斯身上,然后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那里,她沉浸在被他人营救的浪漫幻想中。像浮士
德一样,她寻求超越自己的局限性,却不明白必须从内心着手。
我们越处于无意识状态,我们就越向外投射。艾玛的生活是一系列不断升级的投射,每一次都
无法令人满意。她甚至在通奸中发现了“婚姻的所有陈词滥调” 。最后,她被情人抛弃,
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对寻找梦中情人感到绝望,计划结束自己的生命。她看过的小说告诉
她,女主人公如何在天使和天籁的陪伴下升入天堂。她服下毒药,这是最后的超越,最后的投
射。福楼拜一语破的地说道:“八点钟,呕吐开始了。” 她最后看到的不是天堂,而是一
个盲人的脸。她曾经在赴约路上遇到的那个盲丐再次出现,象征着她的内在男性,即阿尼姆斯
的盲目。
浮士德和艾玛并不邪恶。未曾经历的生活迫使他们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他们将内心的异性元素
投射到外人身上,没有意识到自己所追求的东西最终是在内心。虽然他们的故事是由伟大的艺
术家创作的,但他们的“中年之路”对所有人来说并无二致。
《地下室手记》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 Notes from Underground )描写了一种截然不同的中年境
遇。该书出版于1864年,控诉了人们对进步论、改良论的狂热崇拜,以及人们认为理性能够根
除世界灾难的天真乐观主义。但它不仅是对时代精神的分析,更代表了与阴影的深刻交锋。很
少有人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对内心的黑暗有如此坦诚和深刻的洞察力。
《地下室手记》以不太典型的维多利亚文学的抒情语句开头:“我是一个病人,一个刻薄的人。
但实际上,我对我的病一点也不了解;我甚至不清楚我得了什么病。”这个无名之人开始了自恋
的独白:“那么,一个正派的人最喜欢谈论什么呢?当然是自己。所以我也要谈谈我自己。”在接
下来的篇章中,他描绘了自己的恐惧、投射、愤怒、嫉妒,以及那些人们往往会否认的过于人
性化的特质,并狡黠地指出:“所有人都在为自己的疾病炫耀,而我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地下室的人让我们意识到,所有人在第一个成年期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对生命创伤的反
应。我们建立了一套基于创伤的行为,并以合理化的方式来实践我们受局限的认知。但这个地
下室的人不会放纵自己,也不会纵容我们合理化。读者希望更好地了解他,因为他的自我控诉
牵连到我们所有人。但是,就像他说的:“一个像我这样头脑清醒的人怎么可能尊重自己?”
他把人类定义为“忘恩负义的两足动物,但这还不是他主要的缺点,他主要的缺点是永
不悔改” 。
这个地下室的人拒绝让自己变得可爱或者可原谅。他既不放过自己,也不放过读者。他的自我
分析读起来并不令人愉快,但他很有先见之明地称自己为第一个“反英雄”(antiheroes)。
他的英雄在于他的反常,他的诚实使读者不得不自我反省。因此他告诫:
我不过是把事情推向了极致而已,而你们连做到一半的胆量都没有,你们还把自己的懦弱当作
理智,自欺欺人并聊以自慰。因此,较之你们,我可能还更有活力一些。
卡夫卡曾写道,一部伟大的作品应该像一把斧子,可以劈开我们内心冰封的海洋。 《地
下室手记》就是这样一部作品。有些人仍然质疑它的文学价值,认为它主要是对一个肤浅的乐
观主义时代的控诉。但我们也可以把《地下室手记》看作一个人在中年时为了与自己相会而做
出的努力。从霍桑 、梅尔维尔 、爱伦·坡 、马克·吐温,到史蒂文森
的《化身博士》,再到康拉德 的《黑暗的心》,在文学作品中,与阴影相遇并
不罕见,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我们进入了野兽的腹地。他描画出了人们竭力想要隐藏的劣等领
域。然而,我们越努力压制和分离这硕大的阴影,它就越会在投射和危险的行为中显现,就像
我们在浮士德和包法利夫人身上看到的那样。
尽管与阴影的相遇可能令人痛苦,但它让我们与人性重新连接。它包含着原始的生命能量,如
果有意识地加以处理,可以为我们带来改变和新生。当然,要把自恋转变成有用之物很困难,
但至少它可以得到控制,使其他人不受伤害。用与其同时代的波德莱尔 的话来说,这个
地下室的人就是“我的同类,我的兄弟”。
诗人与诗歌
以艺术为使命的人,经常会有意或无意地塑造和重塑他的神话。伟大的诗人叶芝就经历了无数
次的转变。据说,一些朋友会在某个时刻抱怨,他们刚刚习惯诗人的老样子,诗人就出现了新
样子。他回答说:
每当我重写我的诗歌
那些认为我做错事的朋友
应该知道什么是关键所在
我所重写的,正是我自己。
接下来的三位诗人代表了重塑个人神话的自觉努力。随着权杖和法冠的伟大神话逐渐消退,王
权和教会失去稳固之力,个体只能在荒原上自行开辟道路。许多现代艺术证明,虽然我们需要
在过去的废墟中寻找答案,四处挑选一件仍然适用的象征性斗篷,但主要还是从个人经验中提
取意义。如果过去的精神源泉对今天的艺术家来说普遍不可用,那么他们将不得不从自传的碎
屑中摸索灵魂的经度和纬度。在这些碎屑中,最重要的通常是父亲母亲、童年环境和文化熏
陶。
在上一章中,我们看到了斯蒂芬·邓恩在处理他的父母情结。我们发现,另外三位现代美国诗人
——西奥多·罗特克 、理查德·雨果 和黛安·瓦科斯基 ——也在“记忆宝
库”中筛选,试图拼凑出一个连贯的自我意识。
正如我们所见,人们最迫切的两个需求是养育和赋权,前者让人感觉生活以某种方式为我们提
供帮助和服务,后者则让我们感觉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西奥多·罗特克在密歇根州的萨吉诺度
过了他的童年,他的父亲在那里拥有一个温室。温室成为罗特克许多诗歌的发源地,因为它不
仅象征着他字面上的家,而且象征着对“绿色世界”伊甸园般的记忆。养育和赋权的原型力量,通
过父母的形象得以传播。当父母能够携带这些强大的力量并将其传递下去时,它们就会在孩子
体内被激活。如果孩子在父母身上找不到这些力量,他们就会在替代者身上寻求。多年以后,
罗特克回忆了他父亲手下的三名仆人,她们帮助他填补了孩子的原型需求:
三位老太太走过
踩得温室的楼梯嘎吱作响,
拿出白色的绳线
缠绕,缠绕
香豌豆卷须,卵叶天门冬,
旱金莲,攀缘而上的蔷薇,
挺直的康乃馨,红菊花;
坚硬的茎秆,节理像玉米,
她们将其捆绑收拢,
她们就像是保育员。
比鸟儿迅捷,她们蘸取
泥土,筛掉泥土;
她们泼洒摇晃;
她们跨越管道,
她们的裙子在棚子里翻腾,
她们的手汗湿得闪闪发亮;
她们像成排飞行的女巫
自由自在地创造;
她们用卷须做针
用茎秆缝补空气;
她们挑拣因寒冷而沉睡的种子,
她们的生活是线圈、圆环和年轮。
她们为太阳搭起花棚;她们忘却了自身。
我记得她们如何将我抱起,一个瘦弱的小孩,
掐捏我细细的肋骨
直到我躺进她们的怀里,大笑,
柔弱得像只小奶狗;
此刻,我孤单寒冷地躺在床上,
她们仍在我脑海里盘旋,
三位古老坚韧的老太太,
她们的头巾被汗水凝固,
她们的手腕被荆棘刺伤,
她们沉重的气息轻轻吹过
在我第一次睡着的时候。
这三个女人,就像琥珀里的苍蝇,被冻结在时间中,仍然滋养着诗人的内在小孩。在诗人经历
对抗抑郁和丧失的艰难时期,她们的工作,她们对内在小孩的照顾,此刻似乎提供了一块圣地
(temenos),守护着诗人受伤的心灵。她们不仅仅是仆人,还是成长中的事物的保姆,不论是
对植物还是孩子来说。诗人的记忆再现了那些简单事物的神奇,比如,翻腾的裙子、女巫般的
动作、被汗水凝固的头巾、被荆棘刺伤的手腕、沉重的气息,这些转喻打开了通往过去的大
门。在孤单和寒冷的艰难当下,诗人重新与一段滋养的、充满生机的时光联系在一起。记忆的
作用是维持甚至喂养饥饿的灵魂。正因如此,我们在中年时期面对的生活的广漠、旅途的孤
独,可能部分地被某段生命得到支撑和维持的记忆所调和。
诗人理查德·雨果则很难找到这种栩栩如生的记忆:
你记得詹森这个名字。她似乎老了,
总是一个人在屋里,苍白的脸贴在窗户上,
邮件一直没寄来。两个街区外,格鲁布斯基一家
疯了。复活节,当他们升起旗帜的时候,
乔治吹起坏了的长号。
野玫瑰提醒你道路未铺,都是碎石和空缺。
贫穷是真实的,无论是金钱还是精神,
每一天都像礼拜一样缓慢。你还记得角落里
俗套的教会团体,对星星
大声疾呼他们的信仰,那些激动的圣教徒
租用谷仓,进行他们一年一度激动的演唱
当你从战场上归来,谷仓已被烧毁。
得知你认识的人都已离世,
你试图相信这些铺就的路得到了改善,
你不在的时候,搬进来的邻居很好看,
他们的狗也喂得很好。你仍然需要
惦记许多空地和蕨类植物。
修剪整齐的草坪使你想起妻子乘坐的
那趟火车,一去不返,前往某个遥远的空城,
你永远记不住这个奇怪的名字。时间是6:23。
日期是10月9日。年份仍然模糊不清。
你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这个社区。
在模糊的记忆中,格鲁布斯基一家贬低你
无法弥补。你知道你必须再演奏一次
詹森太太又苍白地站在窗口,一定听到了
刺耳的音乐盖过了路上的车水马龙。
你很爱他们,但他们仍然无事可做
没有钱也没有心愿。爱他们,而阴郁
是他们的疾病,你携带着额外的食物
以防你被困在某个奇怪的空城
需要饥渴的爱人做朋友,需要感觉
在他们建立的秘密俱乐部里,受欢迎。
雨果的童年在穷街陋巷里度过,那里物资匮乏、精神贫瘠。对孩子来说,时间过得很慢,但又
如此之快,似乎难以解释后来所有的变化。生活确实得到了改善。街道铺得平整,草坪修剪整
齐,宠物喂养妥善。但另一些画面则浮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人们来了又去,有些亲近,有些不
那么亲近,唯一不变的是诗人试图弄明白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诗人觉得童年的轨迹、邻里
的关系,导致了现在的局面。
如果诗人认为他的生活是失败的,那么生活的起点也会被牵连,童年的美好愿望遭遇贬值。然
而,雨果和罗特克一样,在黑暗的日子里,仍然会回到他的出发地,以便弄清楚自己是谁,生
活的意义是什么。即使是现在,“阴郁/是他们的疾病,你携带着额外的食物”。如果没有资源支
持,一个人很难踏上通往未知世界的漫长旅程。既然我们知道,朋友和爱人都有自己的旅程,
只能与我们同行一段路,诗人就不得不将记忆的碎片作为灵魂食粮。
雨果和罗特克都是上一首诗最后提到的“秘密俱乐部”的成员。这是一群资源枯竭的人,他们不得
不重新组织起来,以获得神话的支持。詹姆斯·希尔曼 指出,所有的个案历史都是虚构
的。 一个人生活中的事实,比起我们如何记住它们,如何内化它们,如何被它们驱动,
或者如何处理它们,本身倒没那么重要。
每天晚上,当我们的无意识搅动日常生活的碎屑时,神话的制造过程就开始了。记忆也是如
此,视情况而定,可以维持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固着在童年,或者欺骗我们。回到童年的场
景,无论是字面上还是想象上,都有助于人们与所谓的现实建立一种成熟的关系。参观儿时的
学校,就会发现,本来高大的课桌、令人生畏的走廊、无尽的操场,都成比例地缩小了。同
样,过去的创伤可能会被携带着内在小孩的成年人所同化,并允许记忆中的痛苦或快乐被成年
人的知识和力量所重塑。
当我们发现不知道自己是谁,没有救援人员,也没有父母的帮助,而旅途伙伴却能很好地生
存,我们就踏上了中年之路。当我们承认自己来到这个关键的时刻,也许接下来能够理清生命
的脉络,找到从过去走到现在的路径。
黛安·瓦科斯基试图通过检查她过去的模糊照片来发现自己是谁:
妹妹穿着一件剪裁考究的丝绸衬衫,递给我
一张父亲的照片
身穿海军制服,戴着白色帽子。
我说:“哦,这是妈妈以前放在梳妆台上的那张。”
妹妹控制着表情,偷偷地看向母亲,
一个老女人,全身臃肿,
就像二手市场的床垫,虽然没有破洞和裂缝,
妹妹说:“不是。”
我又看了看,
发现父亲戴着婚戒,
他和母亲住在一起时
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婚戒上刻着:
“致我最亲爱的妻子,
爱你
士官长。”
我意识到这张照片是他第二任妻子的,
他离开我们的母亲好去娶她。
我母亲说话了,她的脸就像北达科他州的
无人区一样平静,
“我也可以看看吗?”
她看着它。
我看着那穿着考究的妹妹
和穿蓝色牛仔裤的自己。在我为数不多回家的一天
或是陪伴家人的一天,我们在这里分享这些照片,
是想伤害我们的母亲吗?因为她满脸愁容,
此刻不是她惯常的痛苦,
而是一种无以言表的神情。
我转过身去,说我得走了,因为我要和朋友共进晚餐。
但我从惠蒂尔一路开到帕萨迪纳,
都在想着母亲的脸;我永远无法爱她;
我父亲也不爱她。但我知道我继承了
这具破旧不堪的身体,
冷冰冰的脸和斗牛犬的下巴。
我一边开车,一边想着那张脸。
杰弗斯 的加州美狄亚激发了我的诗歌灵感。
我杀死了我的孩子,
但当我在高速公路上换车道时,我向后视镜里
一瞥,我看到了那张脸,
即使不像幽灵,却一直在我身边,就像放在爱人钱包里
的照片。
我多么憎恨我的命运。
与助人遗忘的舒缓香薰不同,照片能使人提取无意识中的记忆。三个女人,母亲、妹妹和诗
人,通过一张旧照片被拉到了一起。在表面之下,潜藏着过去的创伤和紧张。诗人穿越时间,
就像孩童踩在池塘的冰面上,不知道哪块冰坚固、哪块冰易碎,但仍然要试着走过去。在另一
首诗中,瓦科斯基讲述了她如何“选择”乔治·华盛顿作为她的父亲,因为她的亲生父亲当了“30年
的士官长,总是离家在外”。 她选择了那个过去生活在弗农山庄、如今静立在美元钞票
和孩童记忆中的男人,因为“我的父亲造就了我/一个孤独的女人/没有目标/我就像是一个孤儿/没
有父亲” 。
瓦科斯基对她母亲的体验,如同雨果对老邻居的体验一样,就像二手市场的床垫,就像空旷的
北达科他州,令人望而生畏。她的妹妹穿着考究,与“穿蓝色牛仔裤的自己”形成对比。当她开车
回家时,无论家在哪里,她知道自己都是独自旅行的人。他们所有人,士官长、母亲、妹妹、
她自己,都是孤独的旅人。不像罗特克可以从温室里的三个老太太身上汲取养分,也不像雨果
甚至可以从阴郁的灰色中汲取养分,瓦科斯基知道,她无法从照片所描绘的时光或人物那里得
到力量、安慰或滋养。她承认自己无法爱她的母亲,也无法爱那个士官长父亲。然而,在后视
镜里的那张脸上,在她自己的身上,携带着母亲的影子。她从惠蒂尔到帕萨迪纳,经历了各样
的心灵历程,但她母亲的影子一直跟随着她。
就像另一个被诅咒的悲剧女性美狄亚 一样,她杀死了自己内在的潜能。在受局限的视角
下,她构建了自己的生活。她越想摆脱惠蒂尔的过去,过去就越侵入她的内心。她总结道:“我
多么憎恨我的命运。”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区分宿命(fate)和命运(destiny),就像2500年前的雅典悲剧作家所做的那
样。当然,瓦科斯基没有选择她的父母,就像他们没有选择她一样。但是,他们在时空交汇处
遭受宿命的折磨,彼此伤害着对方。由于这些创伤,我们发展了一系列的行为和态度,以保护
那个脆弱的小孩。这些态度和行为,经过多年的强化,成为后天的人格,化身虚假的自我。瓦
科斯基准确地回到了她的根源,去了解她是如何发展而来的。然而,她所看到的却让她感到厌
恶,因为从后视镜中回望到的是那个她和士官长都无法爱上的女人。只要她是她无法爱上的人
的影子,她就无法爱自己。
然而,命运并不等同于宿命。命运代表了一个人的潜能,代表了内在的可能性——可能实现也
可能不会实现。命运邀请人们做选择。没有选择的命运无异于宿命。瓦科斯基想要超越她日益
憎恨的事物,而这些东西仍将她与她所鄙视和否认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只要她把自己定义为母
亲的女儿,她就与自己的宿命绑在了一起。尽管这首诗有其局限性,没有提供多少超越宿命的
希望,但另一方面,创作这首诗所固有的自省,却代表了必要的意识觉醒和个人责任,从而使
命运的展现成为可能。
如果不努力走向意识觉醒,一个人就会永远固守创伤。在西尔维娅·普拉斯著名的忏悔诗《爸
爸》(“Daddy”)中,她回忆起站在黑板前的教授父亲,突然把他看作“把我漂亮的红心咬成两
半”的恶魔,并补充道,“20岁时,我试图死去/然后回到,回到,回到你身边”。 她父亲
的罪过是在她10岁时去世,那时她的阿尼姆斯需要父亲的帮助,把她从对母亲的依赖中解救出
来。就像瓦科斯基一样,她被父亲抛弃了,被留在母亲身边,被困在伤害之中。普拉斯的愤怒
和自我憎恨反复拉扯着她,直到最后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一个人固守创伤时,他会憎恨镜
子里的那张脸,因为它与那些造成伤害的人如此相似;并且会为自己未能摆脱过去而自我憎
恨。
艺术家通过表达普遍性的能力,往往能比传记事实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阿波利奈尔
(Apollinaire) 写道:“记忆是狩猎的号角,它的声音随风消逝。” 我们的传记
则是陷阱,是欺骗性的诱惑,把我们冻结在看似真实的过去中,让我们固守创伤,成为被宿命
左右的动物。
在中年之路的秘密俱乐部里,有一个盛情邀请,让人们拥有更强的意识和更大的选择空间。有
了更强的意识,就会有更大的机会去宽恕他人和自己,并且通过宽恕,从过去中解脱出来。我
们必须更加自觉地塑造个人神话,否则永远不会超越那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第五章
个性化:荣格的当代神话
中年之路的体验,就像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只身在一艘颠簸的船上,目之所及,不见港湾。此
刻,我们面临三个选择:继续睡觉,弃船而逃,或握住船舵继续航行。
选择与决定
在决定的那一刻,灵魂的崇高冒险从未如此清晰。握住船舵,我们便承担了旅程的责任,不管
它有多么可怕,看起来多么孤独或不公平。松开船舵,我们便被困在第一个成年期,困在我们
自己都厌恶的神经质人格中,因此,我们会自我疏远。一旦我们回应了灵魂旅程的召唤,相比
被众人围绕却倍感孤独,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真实、更正直。在这个时刻,正如克里斯托弗·弗
莱(Christopher Fry)戏剧中的一个角色所说:“事情上升到了灵魂层面,感谢上帝!”
荣格在其自传中写道:
我经常看到,当人们满足于自己对生活问题的不充分或错误的答案时,他们患上了神经症。他
们追求地位、婚姻、名誉、外在的成功或金钱,即使他们得到了所追求的东西,他们仍然不幸
福,仍会患上神经症。这类人通常被限制在太狭窄的精神视野内。他们的生活没有充足的内
容,没有充足的意义。如果他们能够发展出更广阔的人格,神经症通常就会消失。
荣格的观点至关重要,因为所有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经历的狭窄范围内。为了
过上更丰富的生活,我们必须了解自己成长中的局限。我们文化中隐含的假设,即通过物质主
义、自恋或享乐主义可以获得幸福,显然已经破产。那些信奉这种价值观的人并不幸福,也不
完整。
我们需要的不是未经审视的“真理”,而是活生生的神话,也就是一种价值结构,以符合我们本性
的方式引导灵魂的能量。虽然从过去的废墟中寻找与我们对话的人物往往很有用,但要完全领
会另一个时空的神话却不大可能。我们必须找到自己的神话。
毫无疑问,要找到自己的道路,但这条路上荆棘密布、困难重重。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年之路上
的典型症状。它们是无聊、反复更换工作或伴侣、药物滥用、自我毁灭的想法或行为、不忠、
抑郁、焦虑和不断增长的强迫倾向。这些症状的背后有两个基本事实。第一个是有一股巨大的
力量由内向外涌现。它是如此迅猛,极具破坏性,承认它让人感到焦虑,压抑它让人感到抑
郁。第二个基本事实是,将这种内在紧迫感拒之门外的旧模式,随着焦虑的增加而不断重复,
但效果却大不如前。从长远来看,改变一个人的工作或关系并不能改变他的自我感觉。当内在
的压力越来越大,旧有的策略逐渐无法控制时,一场自我身份的危机就会爆发。除了社会角色
和心理反射之外,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怎么做才能减轻压力。
这些症状表明一个人的生活需要实质性的改变。痛苦会使人觉悟,而新的意识会带来新的生
命。这项任务是艰巨的,因为人们必须首先承认,没有外人救援,没有父母来改善一切,也没
有办法回到以前。自性通过使自我精疲力尽的策略来寻求成长。一个人曾经努力创造的自我结
构,现在被证明微不足道、担惊受怕、毫无头绪。在中年时,自性迫使自我结构陷入危机,就
是为了纠正航向。
在中年之路的典型症状背后,有一个假设,即我们能通过寻找和联系外部世界中的新事物或新
人而得到拯救。唉,对于溺水的中年水手来说,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救援。在灵魂的波涛中,虽
然周围有许多人,但我们需要靠自己的力量游泳。真理很简单,我们必须知道的必然来自内
心。如果能使自己的生活遵循这一真理,无论这个世界有多么大的磨难,我们都会感受到治
愈、希望和新生。童年早期的经历以及后来的文化经历,使我们疏远了自己。只有重新联结内
在真实,我们才能回到正轨。
1945年12月,一个阿拉伯农民在洞穴内的大罐子里发现了一些古代手稿。这些手稿似乎是诺斯
替教派的经文,它们更像是个人披露的经验,而不是教会的官方声明。其中一份手稿名为《多
马福音》。据传说,它包含了耶稣私下说过的话,如果是这样,这些话就揭示了一个与众不同
的耶稣。耶稣有句话可谓一语中的,如果我们要在中年经历转变,就必须接受这一观点。他
说:“若将你内在的东西活出来,它们必能拯救你。若不把你内在的东西活出来,它们必将毁灭
你。”
因为内在的东西被压制了,所以我们生病了,自我疏离了。因为内在的东西很少被肯定,所以
我们很难发现自己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也就是适合自己的道路,一直就在那里。尽管设想这项
任务的艰巨性令人恐惧,但知道自己拥有必要的内在资源,无须依赖他人来充分地生活,也是
一种终极意义上的解放。正如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Hölderlin)在两个世纪前所写的:“神灵
近在咫尺,却难以把握;然而,越是危险之地,拯救也越在生长。”
因此,这不是有没有神话的问题,而是选择哪个神话的问题,因为我们总是有意或无意地被意
象所引导。我们可能会认同一些符合集体价值观的信仰和行为,比如追求财富或遵守规范,但
这种适应的代价是神经症。或者,我们可能活在一个错误的神话中,比如:“我必须永远做一个
好孩子,要避免愤怒,要为他人服务。”这样一个引导性的意象可能是无意识的,以致我们总是
以这种方式反应,几乎无法想象另一种反应。外在的服从和内在的顺从都无法使人完整。事实
上,一个人被反复地要求服务于外界,而且当冲突发生时,他仍要继续服务于原来的期望。再
一次,社会的稳定得到维持,但代价是个体的牺牲。1939年,荣格在伦敦牧师心理学协会演讲
时指出,我们被迫在外部意识和个人神经症之间做出选择,但只有个体化的道路才是可行的选
择。 这句话至今仍然正确。
个体化的意义
个体化的概念代表了荣格的当代神话,它是一组引导灵魂能量的意象。简单地说,个体化是每
个人发展的要务,即在命运限制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成为完整的自己。再说一遍,除非有意识
地面对命运,否则我们就会被命运束缚住。我们必须把自身的本性与所获得的东西分开,把真
实的自我与虚假的自我感分开。“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并没有决定我是谁;我的选择才决定了我
是谁。”如果我们不想成为命运的俘虏,就必须每天谨记这句格言。这种困境,以及意识的必要
性,在作者不详的《人生的五个篇章》(“Autobiography in Five Short Chapters”)中有相当幽默
的表达:
一
我走在街上
人行道上有个深坑
我掉了进去
我迷失了……我很无助
这不是我的错
我不知道花了多久才爬出来
二
我走在同一条街上
人行道上有个深坑
我假装没看到
我又掉了进去
我不敢相信还在同样的地方
但这不是我的错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爬出来
三
我走在同一条街上
人行道上有个深坑
我看到它在那儿
但我仍然掉了进去……这是一种习性
我的眼睛睁着
我知道我在哪儿
这是我的错
我立刻爬了出来
四
我走在同一条街上
人行道上有个深坑
我绕道而行
五
我走在另一条街上
我们永远无法确定自己有多自由或坚定,但正如存在主义者所提醒的,我们必须像拥有自由一
样去行动。这种行动恢复了一个人的尊严和目的,否则他只能继续做一个受害者。从纽约起飞
后,一名飞行员只要对飞机的航向稍做修正,就能抵达欧洲或者非洲。因此,即使是轻微的修
正,也能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就必须每天与自己的内心保持
联系。正如荣格所解释的,个体拥有先验的无意识的存在,但只有当他意识到自己的特殊本性
时,才会有意识地存在。我们需要一个有意识的分化过程,或个体化的过程,把个性带入意
识,也就是说,使个人脱离对客体的认同。
荣格所指的对客体的认同,最初是一个人对现实与父母的认同,后来是对父母情结和社会制度
的权威的认同。只要仍然在根本上认同外部客观世界,我们就会与自己的主观现实相疏远。当
然,我们始终是社会性存在,但我们也是精神性存在,有自己的终极目标或神秘目的。在保持
对外部关系忠诚的同时,我们必须更充分地成为自己要成为的那个人。事实上,我们作为个体
的分化程度越高,人际关系就会越丰富。所以荣格认为,由于个体不只是一个单独的、分离的
存在,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以集体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个体化的过程必然导致更强烈和更广泛
的集体关系,而不是导致孤立。
个体化的悖论在于,我们为亲密关系服务的最佳方式是充分发展自己,不需要依赖他人。同
样,我们为社会服务的最佳方式是成为个体,为任何群体的健康发展提供辩证的一面。在社会
这幅马赛克画面中,每一块碎片都因其独特的色彩而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当我们有一些独特的
东西,有最充实的自我时,我们对社会是最有用的。荣格再次说道:
个体化使人脱离了从众性,因此也脱离了集体性。这是个体化的人留给世界的罪过,这是他必
须努力弥补的罪过。他必须提供赎金来代替他自己,也就是说,他必须提供一种价值,来替代
他在集体的个人领域的缺席。
因此,对个体化的关注并不是自恋;它是服务社会和支持他人个体化的最佳方式。那些与自己
和他人疏离的人,那些饱受痛苦又给别人带来痛苦的人,都不会为这个世界提供服务。个体化
作为一组引导性的意象,既是目标又是过程,它为人类服务,而人类又贡献于文化。荣格写
道:“目标仅仅作为信念存在是很重要的,更本质的事情是通往目标的‘伟业’,它才是终生的目
标。”
当我们站在船长的甲板上,手握船舵,几乎不知道方向,只知道必须将这件事完成,那么我们
就活在灵魂的崇高冒险中。从长远来看,这是唯一值得进行的旅程。前半生的任务是获得足够
的自我力量,离开父母,进入世界。这种力量在后半生可用于灵魂的更广阔的旅程中。然后,
轴心会从“自我—世界”转向“自我—自性”,生命的奥秘会以不断更新的方式展开。这不是对我们
社会现实的否认,而是对生活中宗教本质的恢复。因此荣格建议,我们必须问一个人:
他是否与某种无限的事物有关?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理解并感觉到,此生我
们已经和无限有了联系,那么欲望和态度就会改变。归根结底,我们之所以有价值,只是因为
我们所体现的本质;如果我们没有体现出本质,那么生命就荒废了。
我们能够与比自我更大的事物保持关系,并且会由此发生转变。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入口
处,祭司们刻下了这样的箴言:“认识你自己。”根据一份古老的文献,内室的入口有附带铭文:
“汝是。” 这些训诫很好地捕捉到了个体化的辩证法。我们要更充分地认识自己,在更大
的谜团中认识自己。
第六章
航海与孤独
我们每个人都被召唤着实现个体化,尽管不是所有人都会听到或留心。如果我们不朝着自己的
旅程前进,就可能会错失促人成长的生命力,并且失去生活的意义。既然我们航行在灵魂的大
海上,为什么不尽可能地清醒和勇敢呢?
最后一章介绍了一系列任何人都可以应用的态度和做法。尽管正式的治疗关系很有用,但下面
的内容对接受或不接受心理治疗的人都适用。
从孤独到独处
美国诗人玛丽安·摩尔(Marianne Moore) 曾写道:“独处是治疗孤独的良药。”
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孤独和独处有什么区别?
孤独不是当代才有的事物,对孤独的逃避也不是。17世纪哲学家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在他
的《思想录》中指出,宫廷小丑的发明是为了让国王摆脱孤独,因为尽管他是国王,但如果他
反思自我,就会变得烦躁和焦虑。因此,帕斯卡尔认为,所有的现代文化都是一场尽兴的娱
乐,让我们远离孤独,不去思考自我。 类似的,尼采在100多年前写道:“当我们安静地
独处时,我们害怕有人在耳边低语,所以我们讨厌静默,用社交生活来麻醉自己。”
一个人对他与自性的关系没有敏锐的认识,就无法面对或疗愈自己的灵魂。要做到这一点,就
需要独处,即一种完全面对自己的精神状态。如果一个人要从孤独走向独处,以下是一些必须
面对的问题。
消化分离的创伤
无论是出生创伤(一种原始的分离),还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都很难完全理解。亲子关系越
健康,人们就越能自给自足,也越能适应孤独。矛盾的是,与父母的关系越有问题,个体通常
就越依赖于关系。养育的环境越不稳定,我们就越容易从他者的角度来定义自己。荣格写道,
父母“应该始终意识到,他们自己是孩子神经症的主要原因”,这使父母陷入了困难的境地。
我们引用这句话,不是为了让父母感到内疚,而是为了提醒自己,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被
父母和他们的替代品(如社会制度)所定义。
为了进入必要的独处状态,使个体化得以进行,我们必须每天扪心自问:“我为何如此害怕,以
至于逃避自我,逃避自己的旅程?”相互依赖的成年人已经学会了逃避自己的存在。人们常说“了
解自己的感受”,实际上是要求我们从内在真实而不是外部环境来定义自己。我们必须进一步检
视自己对他人的反应,“此刻,父母潜伏在哪里?”然后,我们才可能基于个人的完整性来行动。
童年的创伤越大,我们对现实的感觉就越是幼稚。我们很难了解真实的自己,并以之为基准来
行事。冒着孤独的风险来实现与自己合一,我们称之为独处;如果一个人要在中年之路上幸存
下来,这是必不可少的。
经历丧失和撤回投射
人到中年,往往会遭遇重大的丧失:孩子离家,朋友去世,婚姻破裂。失去那个必要的他者,
可能就像孩子失去父母一样,在生存上是令人恐惧的。中年人不仅感到焦虑,而且感到身份的
丧失。(有一首流行歌曲哀叹:“如果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这告诉我们,生活中有多少意
义和身份被投射到他者身上,无论是配偶、孩子,还是人格面具。是的,有些人因为离婚或孩
子离家而感到自由,但也有很多人没这种感受。重要的是,通过感受丧失来尊重这段关系,同
时也要认识到,我们一直都有一个比任何一段关系都重要的承诺。
一个遭遇丧失并撤回投射的人,将与困扰所有人的依赖性做斗争,但也会追问下一个问题:“未
知的我有多少被绑在那个人或那个角色上?”当我们能够承认丧失,并收回曾经向外投注的能量
时,这些能量就可以用于下一段旅程。
直面恐惧的仪式
人们如此害怕孤独,以至于紧紧抓住糟糕的关系和压迫性的职业,而不愿冒险放弃他者。归根
结底,面对孤独所必需的勇气是无可替代的。尼采指出,我们害怕听到的东西可能是有用和使
人解放的。但是,除非我们冒着独处的风险,否则永远听不到内心的声音。对一些人来说,设
计一种具有私人意义的日常仪式是很有用的,它迫使人们收心静坐,没有电话,没有孩子,什
么都没有,倾听寂静的声音。这样的仪式起初可能显得勉强和做作,但坚持下去就会让寂静开
口。当我们孤单一人而不感到孤独时,我们就抵达了独处的境界。恐惧使我们无法与自己进行
这种必要的会面。
仪式的目的是将一个人与更大的生活节律联系起来。当仪式代代相传时,仪式就成了例行公
事,失去了最初的力量。因此,对个体来说,更有理由创造一个具有私人意义的仪式,将以前
用于依赖的能量来投资它。我们的目标是让心灵的交通平息下来,让纷扰的思绪平静下来。如
果我们害怕孤独,害怕寂寞,就永远无法真正面对自己。自我疏离在很大程度上是当今世界的
通病,只有通过个人行动才能改变。
因此,在每天的某些时候,冒险彻底地面对自己,遵循一种安静的仪式,远离内外纷扰的交
通,这是颇有好处的。当寂静开始言语时,一个人就获得了自己的陪伴,从孤独走向了独处,
这是个体化的一个必要前提。
联系失落的孩子
童年早期对第一个成年期的影响,早就被心理学家注意到了。但是,早期经验作为中年之路的
潜在疗愈资源,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这并不是说我们有一个内在小孩,一个受伤的、害怕的、依赖的或者退缩的小孩,而是说有一
群孩子,一个名副其实的幼儿园,包括了小丑、艺术家、叛逆者、与人打成一片的孩子。几乎
所有的孩子都被忽视或压制了。因此,通过恢复他们的存在感,个体可以得到疗愈。当然,这
同样是耶稣的观点之一,即一个人要进入天国,必须再次成为孩子。
无疑,我们也必须面对自恋的孩子、嫉妒的孩子、愤怒的孩子,他们的爆发往往令人尴尬且具
有破坏性。但是,我们更可能忘记了曾经生活中的自由、美妙的天真,甚至是快乐。中年时期
最具腐蚀性的经历之一是例行公事带来的徒劳感和无趣感。而且,坦率地说,我们携带的自由
小孩(the free child)在办公室里很少受到欢迎,甚至在婚姻中也不受欢迎。
因此,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要疗愈自己,就必须问内心自发的、健康的小孩想要什么。对一
些人来说,与自由小孩相会是容易的;对另一些人来说,这项工作十分困难,因为这个自由小
孩被否认、被深埋。当荣格经历中年之路时,他坐在苏黎世湖畔,堆建沙堡,玩人偶,雕刻石
头,将他丰富的智力和直觉与灵魂中被忽视的部分联系起来。 在邻居看来,他可能是疯
了;但荣格知道,当我们陷入困境时,会被内在的东西所拯救。如果不有意识地接近这个自由
小孩,我们就会在无意识层面爆发,而且往往具有破坏性。这是变得天真烂漫,也就是与内心
的孩子接触,与变得幼稚是有区别的。
到了中年,人们最终必须问内在小孩需要什么,想要什么。在第一个成年期的自我建构过程
中,我们遗忘了对世界的自然喜好,以及与之相伴的许多天赋、兴趣和热情。在工作和亲密关
系中,我们都因专业化而得到奖励。当被遗忘的天赋浮现并被使用时,它就会带来疗愈。鉴于
自性万花筒般的特性,存活下来的只会是几个方面。这种不完整是存在主义悲剧的一部分,但
如果存活下来得越多,我们的生活就会越丰富。
我们注意到,人到中年,情感的流动经常被无聊或抑郁所阻断。这实际上在说,我们自己的本
性过于狭隘,已经阻塞不通了。哪里有游戏,哪里就有生命力。为什么电影中的许多求爱场景
都是一对情侣在公园的秋千上荡来荡去,或在海浪中跳来跳去,表现得像个孩子一样?这种老
套的场景也有其道理。激发出这种新关系的,是与自由小孩重新联系的需要和希望。
中年之路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机会,让我们去问:“我的内在小孩喜欢什么?”是回去上音乐
课;是上美术课,管他天资如何;还是重新发现游戏?我的一位朋友曾经采访过一些退休人
员,他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希望在办公室里花更多时间。没错,我们需要应对外在的职
责和关系,但我们也必须为失落的孩子腾出时间。
激情的生活
当被问及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时,约瑟夫·坎贝尔喜欢说:“追随你的极乐(bliss)。”
坎贝尔知道,我们大多数时候都是按照父母和文化的指令在生活,一路走来失去了自己最好的
部分。有些人对“极乐”这个词感到困惑,把它等同于自恋或一些不切实际的天堂之旅。我理解坎
贝尔说的是灵魂的旅程,包含所涉及的痛苦和牺牲。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倾向于说:“追随你的
激情。”
激情是我们的燃料,就像使命一样,与其说是一种选择,不如说是一种召唤。当雕塑家亨利·摩
尔(Henry Moore) 进入耄耋之年时,有人问他为何还能创作出如此丰富的作品,他回
答说,他有一种巨大的激情,以至于无法停歇。 同样,叶芝甚至在临终前还在写诗。在
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将自己描述为“狂野的老顽童”。 而希腊小说家卡赞扎基斯建议:
“不要给死亡留下任何东西,除了几根骨头。” 我引用艺术家或文学家的名字,不仅因为
他们青史传名、流芳百世,更因为他们一直都在火堆旁生活。任何真正富有创造性的人都知道
创作是多么艰苦的工作,痛苦如何不可避免,但进展和完成的感觉又如何令人欣喜。
在中年之路上,我们受邀去寻找自己的激情。我们必须找到那些深深吸引我们进入生活和自己
本质的东西,因为那些经历改变了我们。
那些相信轮回的人认为,我们可能会有来世,还有其他机会去实现其他的可能性,但即便如
此,那也是另一生,而不是此生。我们被召唤活在当下,要活得充实。在接近死亡和年老衰弱
时,我们不能犹豫不决、心怀羞愧,然后抱怨过去。如果我们要做完整的自己,那么现在就是
最佳时机。
寻找并追随自己的激情,并不一定要像高更去塔希提岛那样决绝,因为我们要信守承诺,我们
的决定会影响他人的生活,而且我想说,我们有道德责任坚持下去。然而,我们仍有义务活出
自己的激情,以免我们的生活变得琐碎和局促,仿佛有一天一切会变得清晰,选择会变得容
易。生活很少会变得清晰和容易;然而,正是选择定义和肯定了我们的生活。
内心深处的恐惧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得到许可吗?人到中年,应该紧紧抓获许
可,而不是请求许可。我们的敌人是恐惧,而不是别的东西。但如果我们害怕自己的内心,害
怕自己的激情,那么应该更害怕没有活过的生命。
这里有一些箴言需要记住:
(1)没有激情的生活,是没有深度的生活。
(2)激情是生命力的表现,虽然它对秩序、可预测性和理智来说是危险的。
(3)如果不冒险去过神性所要求的、激情所提供的广阔生活,就不能接近神性,接近原型的深
处。
(4)寻找并追随自己的激情,有助于我们的个体化。
当我们意识到生活的广阔性,超越童年和个人优越感的局限,就必然会积极回应自己的旅程,
并甘愿冒一切风险。里尔克写了一首题为“古阿波罗残像”(“The Archaic Torso of Apollo”)的
诗,在这首诗中,叙述者正在观察一尊古代雕塑,欣赏石像的每一道缝隙和曲线。然后他意识
到,反过来,他也正在被雕塑“注视”。这首诗以突然而震撼的语气结尾:“你必须改变你的生
活!”
我对此的理解是,当一个人面对真正的创造力、大胆的想象力时,他就不能假装无意识。类似
地,这个人会被伟大的灵魂、大胆的行动所召唤。寻找并追随我们的激情——那些深深地触动
我们,让我们感到痛苦又适宜的激情——有助于激发我们内心的潜力,实现个体化。与使命一
样,自我对其并没有发言权;它只能逃避或表示同意。“并非我的意愿,而是你的意愿。”当旧的
生活变得陈腐时,热情洋溢的生活能使人焕然一新。充满激情地生活,是热爱生活的唯一途
径。
灵魂的沼泽地
个体化的目标是尽己所能地达到完整,而不是自我赢得胜利。几年前,我在一节早课上惊讶地
发现,如果我们活得足够长,我们所爱的每个人都会离开我们;由此推论,如果我们活得不够
长,我们就会离开所爱的人。
虽然这种逻辑无可争辩,但课堂的反应是默不作声,暗含抗议。当然,这种抗议不是来自认知
思维,而是来自内在小孩,他们总是依赖他者的存在。丧失我们想要的东西,是对自我的重大
颠覆;就像推翻第一个成年期的假设,会使我们不情愿地踏入中年之路。这些幻觉中最大的一
个是,有一种叫作“幸福”的终极状态,人们可以发现它并永久生活在其中。可悲的是,我们的命
运更多的是在灵魂的沼泽地里打滚,受到各种各样的阴郁居民的伤害。
沼泽地里的居民有孤独、失落、悲伤、怀疑、抑郁、绝望、焦虑、内疚和背叛等等。但幸运的
是,自我并不是它自以为是的全能指挥官。心灵有一种目的性,超出了意识的控制能力,而我
们的任务就是经历这些状态,并找到它们的意义。例如,悲伤让我们有机会承认所经历过的事
物的价值。因为已经经历过,所以不会完全失去,它被保存在骨子里和记忆中,服务和指导未
来的生活。或者以怀疑为例。需求被称为发明之母,但其实怀疑才是。怀疑具有一定的威胁
性,但怀疑始终是开放的。人类理解上的所有重大进步都来自怀疑。即使是抑郁,也传递了一
个有用的信息,那就是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已经被“压抑”了。
我们不是要逃离沼泽地,而是要涉足其中,看看有什么新生命在等待着我们。每一片沼泽区域
都代表一股心灵之流,如果我们足够勇敢去驾驭它,就可以发现它的意义。当中年之路上的船
只陷入沼泽时,我们必须问:“这对我意味着什么?我的心灵在告诉我什么?我应该怎么做?”
直面自己的情绪状态并与之对话需要勇气。但这就是个人完整性的关键所在。在灵魂的沼泽地
里,蕴含着意义和扩大意识的召唤。接受这个挑战是人生最大的责任。只有我们自己能够掌握
船舵。当我们这样做时,恐惧就会被意义、尊严和目的所补偿。
伟大的辩证
荣格采用了一个复合德语单词“Auseinandersetzung”(交换意见),来描述我们与自己之间必要
的对话。有人可能会把这个概念翻译成“将一件事与另一件事对立起来”,形象地描述了一种对抗
或辩证。例如,那些发生在分析师和分析对象之间,以及每个人的无意识中的事情。
如何推进这一对话呢?我们的建议包括一些日常提问:“在这种情况下,我是谁,我听到了什么
声音?”以及日常的冥想,也许还有更积极的反思方式,比如写日记。
在本书的开头,我曾说过,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是透过童年和文化的棱镜来观察得到的,这个棱
镜会折射光线,扭曲我们的视野。生活中的某些经验会被内化、强化或分裂,然后当它们作为
情结侵入并压倒意识时,就会宣称对当下的控制。然后,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明显的问题:“如
果我不是我的自我,也不是我的情结,那么我是谁?”为了应对这一困境,我们必须开始伟大的
辩证。当我们从“自我—世界”轴心上移开时——它使我们的前半生充满活力,我们就需要进行
“自我—自性”的对话。正如我们所见,自性通过许多提示表现出它更大的目的性。无论是身体上
的、情感上的还是想象上的,这些提示都是我们需要回归正轨的表达。
也许参与内心对话的最有用的技术是分析梦境。我们生活在一种日益蔑视内心生活的文化中,
因此看不到梦境所蕴含的价值。但是,心灵通过梦中的意象说话,这些意象对自我来说可能怪
异,但它们体现了自性的能量和目的论。当我们能够理解这些意象的意义时,就获得了难以置
信的丰富智慧,这种智慧在任何书籍或制度中都找不到。这是我们自己的真理,而不是别人
的。如果我们能够追随并理解一些梦境,就能更好地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正确的,真正的本性要
求我们做什么。除了深夜所呈现的丰富的个人神话,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关于自己的如此
准确的信息。
荣格还发展了一种叫主动想象(active imagination)的技术。这不同于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法
(free association),也不是一种冥想形式。它是一种激活意象的方法,通过绘画、玩黏土、舞
蹈或其他方式,以便个体与意象携带的情绪建立关系。这种类型的“交换意见”,不仅有助于意识
在梦境中找到意义,还会促进自我与自性之间的对话。
在我治疗的过程中,我每周听到大约40个梦。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辨识出反复出现的主
题。然而,就在自我认为一切都很清晰时,心灵会绕弯子,干扰理解。这样的工作会使人谦
卑,但它也是最丰富的,因为我们与灵魂直接联系,与所有人身上运行的宇宙的神秘目的直接
联系。任何分析师都能提供数百个梦境,我在这里说两个梦,不可否认,它们比许多梦都更具
故事性和连贯性。
第一个梦来自一个42岁的女人,她在抚养孩子长大后回到大学深造。因离开教室多年,她感到
有些不安,这完全可以理解。在课程学习的早期,她很快对X教授产生了强烈的爱慕之情。“坠
入爱河”几个月后,她梦到:
我走在走廊上,看见Y教授在办公室。她示意我进去。奇怪的是,她有一个阴茎,我们在办公室
的地板上做爱,而且门还开着。我很震惊,但觉得这是对的。之后,我回到走廊上,看到X教授
向我走来。我会意地笑了笑——这让他很困惑——然后继续走过去。
这个女人对这个梦感到尴尬,犹豫着要不要把它带到治疗中,因为她害怕这个梦的直白和对同
性恋的暗示。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梦,表明情况已经出现了转折。对X教授的迷恋,代
表了她在以前的生活中尚未发展的部分——她的阿尼姆斯,她对事业和新视角的需要。她并不
熟悉的Y教授,对梦者而言,是一个女性的典范——既发展了阿尼姆斯,又保持了女性气质。因
此,在主观层面上,与Y教授做爱实际上是一种连接,是将男性和女性的原则整合在一起。这种
连接,通过做爱在她的无意识中发生,使她可以了解自己的一些特别之处,这样就没有必要将
其投射到X教授身上。通过象征性地处理这个梦,并讨论她内心保持两个对立面的平衡是什么感
觉,使梦者对她的个人发展任务有了更好的认识。
一个36岁的男人梦见他来到一座美丽的豪宅,那里正上演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但被演
成了一种色情的芭蕾舞。有人邀请他一起舞蹈,他加入了;直到母亲给他打电话,坚持要他回
去解救她。在梦结束时,他对自己想做的事情被打断感到很愤怒,但又觉得不得不答应母亲的
要求。
在现实中,做梦者与母亲之间远隔重洋,但在心理上,他仍然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他反复遭受
抑郁症的折磨,被消极的阿尼玛所淹没,并害怕在关系中做出承诺。自性把这个梦当作礼物送
给他,这是一张描绘他内心世界地形的地图。他虽然已经离家千里,但仍然向父母“报到”,仍然
是受压迫童年的受害者。与此同时,他错过了“生命之舞”——这是他对梦中芭蕾舞的联想。这些
意象的力量证实了他受伤的程度及其后果。简而言之,这个梦强调了他需要从母亲情结中解放
出来,解放他的阿尼玛——荣格称之为“生命本身的原型”。
人们越是理解这样的梦境,就越会相信荣格所说的内在神秘力量,即自性。在这个浩瀚的宇宙
中,我们并非孤立无助,缥缈虚无,我们有丰富的、能引起共鸣的无意识,它通过日常生活中
的症状,通过梦境和主动想象向我们说话。我们在中年之路上的任务是合作,询问梦中的意
象:“它们来自我的什么地方?我的联想是什么?它们对我的行为有什么要说的?”
真正修正一个人自我感的唯一方法,就是在自我和自性之间进行这种对话。我们并不一定要接
受正式的治疗,只需要有勇气和日常纪律来“倾听”。当我们能够包容和整合所学的东西时,就不
会在孤身一人时感到孤独。当我们能够内化与内心的对话,同时保持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时,就
会体验到先前由古代神话和宗教提供的与灵魂世界的连接。我们重新学习了我们祖先所知道
的:黑暗会发光,寂静会说话。当我们有勇气和纪律进入内在,体验灵魂世界的伟大辩证时,
我们就会在永恒中重新站稳脚跟。
牢记死亡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 ,19世纪英国社会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从各种标准来
看都是一个杰出的人。直到几年前,如果你很幸运,可以在伦敦大学学院“一睹芳容”。边沁先生
在其遗嘱中预留了一笔津贴,用于每年以他的名义举办一场晚宴。这一切都很好。但有一项规
定是,要把他经过防腐处理的遗体推出来,放在桌子的最前面。人们不禁会想,在这样的晚宴
上,可能有怎样风趣的谈话。如果发现主人看起来很憔悴,客人们会不会很尴尬?
杰里米·边沁的故事反映了西方文化的现状。随着神话的基石被侵蚀,自我价值转向物质获取和
地位升迁,现代文化已经将死亡视为敌人。据说,现在在鸡尾酒会上,死亡是唯一不合适的话
题。正如杰西卡·米特福德(Jessica Mitford,《美国式死亡》)、欧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拒斥死亡》)和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Elizabeth Kubler-Ross,《论死亡与濒死》)
等社会评论家所观察到的,美国人尤其介意这个关于生命的核心事实,即我们都在走向死亡。
这个明显的事实充满了暗示。在中年之路上,人们对时间和有限性的严峻认识,取代了童年的
魔法思维和成年早期的英雄思维。爱欲带给我们生命,同时,这一力量也在吞噬我们。正如狄
兰·托马斯(Dylan Thomas)简洁的表达:“通过绿色茎管催动花朵的力,是我的毁灭者。”
年轻时的爱欲,就像一根燃烧的导火线,到中年时,对自己的死亡感到震惊。难怪那些
老男人会和“可爱的年轻女人”私奔;这些女人会做胶原蛋白治疗,会做整形手术来掩饰时间的流
逝,会在温泉疗养中心酣畅淋漓。正是对衰老和死亡的恐惧激发了这些行为。
我们为什么希望保持年轻?把身体的某些部位变得更灵活也许是件好事,但为什么人们希望回
到更幼稚的过去呢?答案显而易见:人们宁愿把生命看作固定不变而不是向前发展的,人们没
有准备好面临一系列的死亡和重生,人们不愿意完成整个旅程而宁愿蜗居在舒适的空间里。因
此,整形手术取代了生命战役,青春气息主宰着整个文化。
希腊神话中的提托诺斯(Tithonus) 是一个永生之人,但他的身体仍会衰老。当他的身
体衰弱时,他向诸神祈求死亡,最终如愿以偿。这就是杰里米·边沁和我们所有人的故事。时间
让我们归于尘土。
在中年时,精力的减退和苦心经营的一切被摧毁,自然会让人感到苦恼。但在这种苦恼之下,
有一个盛情邀请。它邀请我们为接下来的旅程换挡,从外部获取转向内在发展。从第一个成年
期的角度来看,后半生是一场缓慢的恐怖表演。我们失去朋友、伴侣、孩子、社会地位,然后
是生命。然而,如果真的如所有宗教所证明的,万事皆有神启,那么我们必须接受这个过程中
更大的智慧。我们不能只从青春的角度出发,只从自我的角度来想象安全,更大的成就当然是
获得足够的心理弹性,去肯定我们整个生命中更大的节奏。
我有幸见过一些在临终前比大多数人都更清醒的人。其中一个人,安吉拉,曾坐在我此刻身处
的房间里,她说:“我不希望它以这种方式发生在我身上,但这是发生在我身上最好的事情。”她
承认,癌症摧毁了她的身体,但最终唤醒了她的生命。她过着美好、负责任、受尊敬的生活,
但她从未了解过自己。在分析过程中,她激活了自己未触及的部分;她学习音乐、空手道和绘
画。我敬佩她的勇气、日益增长的谦卑,以及她朴素的智慧。到她去世的时候,她已经获得了
比自己本身更大的成就:生命旅程中美妙的谦卑和壮丽。这个向我求助的人后来帮了我很多
次。
中年之路上的痛苦可以转化为这样的收获。讽刺的是,失去从某个角度来看意味着得到,因为
放弃旧的自我确定性,会使人遇到一个更大的现实。如果我们是不朽的,就没有什么真正重
要,没有什么真正算数;但我们不是永生的,所以每个选择都很重要。正是通过做出选择,我
们才成为人,并找到个人的意义感。那么,矛盾在于,人类存在的价值和尊严、恐惧和希望,
都依赖于必有一死。这就是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 所说的“死亡是美丽之
母”。 美来自恐惧,对确定的欲望也是。有如此多的恐惧,所以有如此多的美。
当我们不再执着于自己是谁,不再追求名利或青春的外衣时,我们知道已经走过了中年之路。
通过放弃旧有的自我依恋,肯定自己逐渐步入神秘之中,生命作为一种缓慢消逝的感觉,一种
不可替代的丧失体验,得到了转变。
像往常一样,诗人捕捉到了这一悖论,也就是耶稣在两千年前曾指出的:要赢得生命,我们必
须学会失去生命。里尔克在他的第九首《杜伊诺哀歌》中谈到了我们生命的循环:
你永远是对的,你神圣的
启示就是亲密的死亡。
瞧,我还活着。依靠什么?
童年和未来都不会
减少……盈余的存在
涌上我的心头。
悖论在于,只有通过放弃我们所追求的一切,我们才能超越安全和身份的虚假保证,放弃所有
的追求。接着,最奇怪的是,剩余的存在会充盈我们的内心。然后,我们从头脑中的知识——
尽管它有时重要——转向心灵的智慧。
生命是一束光
据我所知,对于生命,没有谁比荣格的定义更为精妙,他说:“生命是两个巨大的谜团之间的一
束光,而这两个谜团是一体的。” 我们狭隘的意识所能了解的奥秘,并不是全部的奥
秘。我们永远不会最终明白并确定这段旅程是怎么回事。我们只是被召唤尽可能有意识地生
活。
现代希腊诗人卡瓦菲斯(Cavafy) 捕捉到一个悖论,即旅程的目的可能就是旅程本身。
他的诗名为《伊萨卡岛》(“Ithaca”),这座城市既是奥德修斯 的出发地,也是他的目
的地;而奥德修斯是所有人心中流浪者的原型。诗人劝诫奥德修斯祈祷他的旅途漫长、充满艰
险,并且敦促他不要急于返程。当他最终驶入故乡的港口时,请记住:
伊萨卡赐予你如此美妙的旅程。
没有她,你永远不会走这条路。
但她再没有更多的东西给你了。
如果你发现她乏善可陈,伊萨卡没有欺骗你。
凭借你所获得的智慧,凭借你丰富的经验,
到那时,你一定会明白伊萨卡的意义。
我们的伊萨卡不是抵达或休息之所,而是激活和推动旅程的能量。在生命的后半段,无论它何
时到来,旧的自我世界可能仍然需要忠诚,但是一个人的现实感对它的依赖要少得多。是的,
各种角色的丧失是一种死亡,但有意识地放手也可能开启一个转变过程,明智的做法是协助而
不是阻碍它。当我们转过这个精神拐角之后,许多旧的自我要务似乎不再重要。
一个人没有完成中年之路的标志是,他或她仍然陷在第一个成年期的自我建设活动中。人们还
没有认识到,这些活动只是对有限和不可靠的权威的投射。它们是虚幻的偶像,虽然在生命早
期是必要的,但后来可能会使我们在旅程中迷失。当然,旅程本身是象征性的,是运动、发
展、爱神战胜死神的意象,是努力创造意义。我们在中年的任务是变得足够强大,能够放弃前
半生的自我要务,向更大的奇迹开放自己。
中年危机的体验不是核心自我的崩溃,而是一系列假设的崩溃。当我们环顾四周的过来人时,
我们自然会寻找行为和态度的范例。我们的假设是,如果我们遵循前人的道路,我们最终会确
定自己是谁,并将了解生活的意义。当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时,我们会感到幻灭、焦虑,甚至是
背叛。我们了解到,没有人真正知道生命的意义,也没有人知道生命的奥秘。那些吹嘘自己知
道的人,要么仍然在向外投射,要么就是在自吹自擂;充其量,他们是在证明自己的真理,而
不是我们的真理。因此,没有什么大师,因为每个人的道路是不同的。
荣格提醒我们,人们感受到痛苦,是因为“满足于自己对生活问题的不充分或错误的答案”
,灵魂因此遭罪。所以,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生命是受限的,我们的视野是受限
的,我们要么跳船,要么拥抱旅程。有些人担心自己的旅程会影响他人,对此我们需要记住,
我们帮助他人的最好方式,就是清醒地过自己的生活,这样他人才能自由地过他们的生活。荣
格觉得,这一点对于父母和孩子来说尤其正确。里尔克写道:
有时,一个人在晚餐时站起来
走到屋外,一直走下去,
因为在东方某处有一座教堂。
孩子们对他说祝福的话,好像他已死去。
而另一个人,他留在自己的房子里,
待在那里,消耗在碗碟和杯子里,
这样,他的孩子们就得远走他乡
走向那座他所遗忘的教堂。
走过中年之路,没有人知道这段旅程将把我们带到哪里。我们只知道,我们必须对自己负责,
别人走的路不一定适合我们,我们最终要寻求的东西在内部,而不在外部。正如几个世纪前圣
杯传说所言:“走别人走过的路是一件可耻的事。” 只有听从自己的内心,我们才能感受
到灵魂的激励,正是这种对内在而非外在真理的强调,区别了第一个成年期和第二个成年期。
荣格再次提醒我们:“一个人只有自觉地认同内在声音的力量,才能成为一个有个性的人。”
有意识的行为是核心,否则我们就会被情结所淹没。每个人心中的英雄都必须响应个体化的召
唤。我们必须远离外部世界的喧嚣,倾听内心的声音。当我们敢于从心而活,我们就有了个
性。对于那些自以为了解我们的人,我们可能会变得陌生,但至少我们对自己不再陌生了。
对中年之路的有意识体验,需要将我们是谁与我们的内化经验分开。然后,我们的思维会从魔
法思维到英雄思维,再到人性思维。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变得不那么依赖,对他人要求更少,对
自己要求更多。我们的自我受到打击,必须重新定位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职业、人际关
系,以及权力和满足的来源。在对自己要求更多时,如果他人没有提供他们无法提供的东西,
我们也不再失望;我们会承认,与我们一样,他们的主要责任是走完自己的旅程。我们会越来
越意识到身体的有限性和人类所有事物的脆弱性。
如果我们还有勇气,中年之路会让我们与生命失联之后重获新生。奇怪的是,除了所有的焦
虑,还有一种令人敬畏的自由感。我们甚至可能会意识到,只要与自己有着重要的联系,外面
发生的事情并不重要。新发现的与内在生命的关系,足以平衡外部世界的损失。灵魂旅程的丰
富,至少与世俗成就一样有价值。
回想一下荣格的中心问题:“我们是否与某种无限的事物有关?” 我们要么体现出某种本
质,要么就荒废了生命。一种巨大的神秘能量在孕育时就体现出来,在世间停留片刻,最后去
了别的地方。让我们做仁慈的主人,让我们有意识地赞同这生命散发的光芒。
最后,让我们用里尔克的话作为墓志铭:
我生活在不断扩大的圈子中
逐渐覆盖世界上所有的事物。
也许我永远无法抵达终点,
但那将是我努力的目标。
我环绕着上帝,环绕着古老的塔,
我已经盘旋了一千年,
而我仍不知道我是一只猎鹰,一场风暴,
还是一首激昂的歌谣。
Select Bibliography
精选参考书目
On Midlife
论中年
Sharp, Daryl. The Survival Papers:Anatomy of a Midlife Crisis.Toronto:Inner City Books,1988.
Sheehy, Gail. Passages:Predictable Crises of Adult Life.New York:Bantam,1977.
Stein, Murray. In Mid-Life:A Jungian Perspective.Dallas:Spring Publications, Inc.,1983.
On Women
论女性
Carlson, Kathie. In Her Image:The Unhealed Daughter’s Search for Her Mother.Boston: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1988.
Godwin, Gail. Father Melancholy’s Daughter.New York:Morrow,1991.
Johnson, Robert. She:Understanding Feminine Psychology.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7.
Leonard, Linda. The Wounded Woman:Healing the Fa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Boston: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1983.
McNeely, Deldon Anne. Animus Aeternus:Exploring the Inner Masculine.Toronto:Inner City
Books,1991.
Perera, Sylvia Brinton. Descent to the Goddess:A Way of Initiation for Women.Toronto:Inner City
Books,1981.
Woodman, Marion. Addiction to Perfection:The Still Unravished Bride.Toronto:Inner City Books,
1982.
Woodman, Marion. The Pregnant Virgin:A Process of Psychological Transformation.Toronto:Inner
City Books,1985.
Woodman, Marion. The Ravaged Bridegroom:Masculinity in Women.Toronto:Inner City Books,
1990.
On Men
论男性
Bly, Robert. Iron John:A Book About Men.Reading, Mass: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1990.
Corneau, Guy. Absent Fathers, Lost Sons:The Search for Masculine Identity.Boston: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1991.
Hopcke, Robert. Men’s Dreams, Men’s Healing.Boston: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1989.
Johnson, Robert. He:Understanding Male Psychology.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7.
Keen, Sam. Fire in the Belly:On Being a Man.New York:Bantam,1991.
Levinson, Daniel J. The Seasons of a Man’s Life.New York:Ballantine,1978.
Monick, Eugene. Castration and Male Rage:The Phallic Wound.Toronto:Inner City Books,1991.
Monick, Eugene. Phallos:Sacred Image of the Masculine.Toronto:Inner City Books,1987.
Moore, Robert and Gillette, Douglas. King, Warrior, Magician, Lover:Rediscovering the Archetypes
of the Mature Masculine.San Francisco:Harper and Row,1990.
On Relationship
论关系
Bertine, Eleanor. Close Relationships:Family, Friendship, Marriage.Toronto:Inner City Books,
1992.
Sanford, John. The Invisible Partners:How the Male and Female in Each of Us Afects Our
Relationships.New York:Paulist Press,1980.
Sharp, Daryl. Getting to Know You:The Inside Out of Relationship.Toronto:Inner City Books,
1992.
Typology
类型学
Keirsey, David and Bates, Marilyn. Please Understand Me:Character and Temperament Types.Del
Mar, CA:Prometheus Nemesis Press,1984.
Sharp, Daryl. Personality Types:Jung’s Model of Typology.Toronto:Inner City Books,1987.
Inner Work
内在工作
Abrams, Jeremiah. Reclaiming the Inner Child.Los Angeles:Jeremy P.Tarcher, Inc.,1990.
Carotenuto, Aldo. Eros and Pathos:Shades of Love and Sufering.Toronto:Inner City Books,1989.
Hall, James. Jungian Dream Interpretation:A Handbook of Theory and Practice.Toronto:Inner City
Books,1983.
Hall, James. The Jungian Experience:Analysis and Individuation.Toronto:Inner City Books,1986.
Jaffe, Lawrence W. Liberating the Heart:Spirituality and Jungian Psychology.Toronto:Inner City
Books,1990.
Johnson, Robert. Inner Work:Using Dreams and Active Imagination for Personal Growth.San
Francisco:Harper and Row,1986.
Storr, Anthony. Solitude:A Return to the Self.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88.
General Bibliography
普通参考书目
Agee, James. A Death in the Family.New York:Bantam,1969.
Alighieri, Dante. The Comedy of Dante Alighieri.Dorothy Sayers trans.New York:Basic Books,
1963.
Apollinaire, Guillaume. In An Anthology of French Poetry from Nerval to Valery in English
Translation.New York:Doubleday Anchor Books,1962.
Aristotle. Poetics.Francis Ferguson ed.and trans.New York:Hill and Wang,1961.
Arnold, Matthew. Poetry and Criticism of Matthew Arnold.New York:Houghton Mifflin,1961.
Baudelaire, Charles. In An Anthology of French Poetry from Nerval to Valery in English
Translation.New York:Doubleday Anchor Books,1962.
Bernbaum, Ernest, ed. Anthology of Romanticism.New York:The Ronald Press Co.,1948.
Berthoud, Roger. The Life of Henry Moore.New York:Dutton,1987.
Bonhoeffer, Dietrich. 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Eberhard Bethge trans.New York:MacMillan,
1953.
Campbell, Joseph. The Power of Myth.With Bill Moyers.New York:Doubleday,1988.
Campbell, Joseph. This Business of the Gods:In Conversation with Fraser Boa.Caledon East, ON:
Windrose Pubns,1992.
Cavafy, C. P.The Complete Poems of Cavafy.Rae Dalven trans.New York:Harcourt, Brace and
World,1961.
Cheever, John. The Stories of John Cheever.New York:Alfred A.Knopf,1978.
Cummings, E. E.Poems 1923-1954.New York:Harcourt, Brace and Co.,1954.
de Troyes, Chretien. The Story of the Grail.R.W.Linker trans.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52.
Dostoyevsky, Fyodor. Notes from Underground.Andrew R.MacAndrew trans.New York:Signet,
1961.
Dunn, Stephen. Landscape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New York:W.W.Norton and Co.,1991.
Dunn, Stephen. Not Dancing.Pittsburgh: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 Press,1984.
Eliot, T. S.The Complete Poems and Plays.New York:Harcourt, Brace and World,1952.
Eliot, T. S.In 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Hazard Adams ed.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1970.
Ellmann, Richard. Yeats:The Man and the Masks.New York:Dutton,1948.
Flaubert, Gustave. Madame Bovary.Paul de Man trans.New York:W.W.Norton and Co.,1965.
Fry, Christopher. A Sleep of Prisoner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
Gilligan, Carol. In a Diferent Voic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Faust.Walter Kaufmann trans.New York:Anchor Books,1962.
Halpern, Howard M. How to Break Your Addiction to a Person.New York:Bantam,1983.
Heidegger, Martin. Being and Time.John Macquarrie trans.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2.
Hillman, James. Healing Fiction.Barrytown, NY:Station Hill Press,1983.
Hobbes, Thomas. Selections.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30.
Hölderlin, Friedrich.An Anthology of German Poetry from Hölderlin to Rilke.Angel Flores ed.New
York:Doubleday Anchor Books,1960.
Hugo, Richard. Making Certain It Goes On:The Collected Poems of Richard Hugo.New York:
W.W.Norton and Co.,1984.
Ibsen, Henrich. A Doll’s House and Other Plays.New York:Penguin,1965.
Jung, C. G.Letters(Bollingen Series XCV).2 vols.R.F.C.Hull trans.G.Adler, A.Jaffé ed.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
Jung, C. G.The Collected Works(Bollingen Series XX),20 vols.R.F.C.Hull trans.H.Read,
M.Fordham, G.Adler, W.M.McGuire e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1979.
Jung, C. G.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trans.A.Jaffé ed.New York:
Vintage Books,1965.
Kafka, Franz.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Franz Kafka.Willa and Edwin Muir trans.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1952.
Kazantzakis, Nikos. 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60.
Kazantzakis, Nikos. The Saviors of God.Kimon Friar trans.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60.
Kean, Sam and Valley-Fox, Anne. Your Mythic Journey.Los Angeles:Jeremy P.Tarcher, Inc.,1989.
Lincoln, Abraham. The Lincoln Treasury.Chicago:Wilcox and Follett,1950.
Moore, Katharine. Victorian Wives.London:Allison and Busby,1987.
Moore, Marianne. The Complete Prose of Marianne Moore.New York:Viking,1986.
Nietzsche, Friedrich. The Portable Nietzsche.Walter Kaufmann trans.New York:Viking,1972.
O’Neill, Eugene. Complete Plays.New York:Viking,1988.
Pagels, Elaine. The Gnostic Gospels.New York:Vintage Books,1981.
Pascal, Blaise. Pensées.New York:Dutton,1958.
Plath, Sylvia. The Collected Poems.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1.
Price, Martin. To the Palace of Wisdom.New York:Doubleday,1964.
Rilke, Rainer Maria. Duino Elegies.C.F.MacIntyre tra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Rilke, Rainer Maria. Letters of Rainer Maria Rilke.Jane Green and M.D.Herter Norton trans.New
York:W.W.Norton and Co.,1972.
Rilke, Rainer Maria. Letters to a Young Poet.M.D.Herter Norton trans.New York:W.W.Norton and
Co.,1962.
Rilke, Rainer Maria. Selected Poems of Rainer Maria Rilke.Robert Bly trans.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1.
Roethke, Theodore. The Collected Poems of Theodore Roethke.New York:Doubleday and Co.,1966.
Roth, Philip. Goodbye, Columbus and Fives Short Stories.Boston:Houghton Mifflin,1959.
Stevens, Wallace. The Collected Poems of Wallace Stevens.New York:Alfred A.Knopf,1954.
Terence. Comedies.Chicago:Aldine Publishing Co.,1962.
Thomas, Dylan. Collected Poems.New York: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1946.
Thoreau, Henry. The Best of Walden and Civil Disobedience.New York:Scholastic Books,1969.
Untermeyer, Louis, ed. A Concise Treasury of Great Poems.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42.
von Franz, Marie-Louise. Projection and Re-Collection in Jungian Psychology:Refections of the Soul.
LaSalle, IL:Open Court,1988.
Wagoner, David. A Place To Stand.Bloomington, I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58.
Wakoski, Diane. Emerald Ice:Selected Poems 1962-1987.Santa Rosa, CA:Black Sparrow Press,
1988.
Whitehead, Alfred North. Nature and Life.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68.
Wordsworth, William. Poetical Works of Wordsworth.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0.
Yeats, William Butler. The Collected Poems of W.B.Yeats.New York:MacMillan,1963.
前言
对意义的探寻
真理是神圣的,它不是直接就能掌握的东西。唯有在反思中,在例证和象征中,在单一或相关
的表象中,我们才能领悟到它。它以“令人无法理解的人生”的面目出现,可是我们却无法摆脱想
要理解它的欲望。
——歌德(Goethe)
有一种观点,或许应该称之为反复出现的幻想吧,认为人生的目的就在于获得幸福。毕竟,就
连美国的《独立宣言》也做出了“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许诺。有朝一日,能在阳
光灿烂的草地上逗留、休憩,无忧无虑,幸福快乐——谁不向往这样的情景呢?
可是,大自然,或者说宿命、上天,却另有打算。它不断地打破人们的幻想。我们向往的图景
和实际的遭遇(困顿)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这道裂隙总是在西方人的脑海中闪现。在帕斯卡
(Pascal)看来,我们不过是脆弱的芦苇,轻易就能被漠然的天地摧毁,然而我们也是会思考的
芦苇,能够想象宇宙洪荒。歌德笔下的浮士德(Faust)说起胸臆间那两个相争的精魂,一个执
着于尘世,另一个向往天堂。尼采(Nietzsche)让我们想起发现自己并非上帝并悲悼于这个事实
的那一天。散文家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观察到:
人是唯一会笑会哭的动物;皆因唯有人会因为“事情实际是怎样”与“事情理当是怎样”之间的差异
而备受打击。
在黑塞的《玻璃球游戏》中,主人公约瑟夫·克乃西特(Joseph Knecht)慨叹道:
啊,要是能让人们理解,该有多好……要是能有一个令人坚信不疑的信条该有多好。样样都相
互矛盾,样样都只是稍微沾点边,不能切中要害;再也没有确凿无疑……难道就没有真理可言
吗?
在期望与真实之间的裂隙中升起的感慨简直多到无穷无尽。是坚毅地忍受下去,还是像英雄般
做出回应,抑或是哀叹自己时运不济?这似乎是一个艰难的但又绕不过去的选择。但荣格心理
学,以及它倡导的“自律的自我成长”,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其前提是:人生的目的不是
追求幸福,而是探寻意义。
我们大概都充分体验过幸福的瞬间,但它们总是稍纵即逝,既不能凭着许愿成真,也无法靠希
望永存。不过,荣格心理学,以及荣格曾经从中汲取洞见的、诸多宗教与神话方面的丰富传统
都主张,正是灵魂的沼泽地、痛苦的大草原为人们提供了情境,促发人们去探索,并最终寻获
意义。正如两千五百年前的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发现的那样,神祇颁布了庄严的律令——
经由痛苦,世人悟出智慧。
若是没有痛苦——它似乎是心理与灵性达到成熟的必要条件——人会停留在无意识的、幼稚
的、依赖的状态中。然而,我们的诸多成瘾问题、意识形态层面的依恋,还有神经症,都是对
痛苦的逃避。四分之一的北美人信奉正统基督教派的信仰体系(fundamentalist belief systems),
希望借助过于简单的、黑白分明的价值观,让人生旅程变得没那么沉重;他们不喜欢灵性问题
中存在模棱两可,于是寻求领袖人物带来的确定感,或是抓住现成的机会,把人生中的矛盾投
射到邻人身上。还有四分之一到一半的人沉溺于形形色色的上瘾行为,将存在性焦虑暂时麻
醉,结果却发现它执拗地又在次日重返。余下的人选择了神经症,也就是说,运用诸多直观的
防御手段去对抗人生中的创伤。但这些防御同样会令灵魂陷入困局,即让人始终只会做出被动
的反应。而这会让一个人滞留在过去,而不是活在当下。
有句老话说,宗教是为那些害怕下地狱的人准备的,而灵性是为那些去过地狱的人准备的。除
非我们能够正视“向往的图景”与“实际的体验”之间的差距,除非我们能有意识地承担起灵性成长
的任务,否则我们就会永远滞留在逃避或否认的状态,或是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尖酸刻薄地对
待自己和他人。
荣格心理学的思想、动机及实践就是:并不存在阳光灿烂的草地,并不存在让人松弛小憩的绿
荫;真正存在的是灵魂的沼泽地。而大自然,还有我们的天性,有意做出了安排,使得我们的
旅程有很大一部分需要在此停留,人生中许多有意义的时刻将会从这里诞生。正是在这样的沼
泽地里,灵魂被渐渐锻造成型;在这里,我们遇到的不只是生命的庄严感,更有它的目的、它
的尊严,还有它最深层的意义。
对于疗愈的艺术来说,其遭遇到的最大讽刺无疑就是心理学实践中“灵魂”这个概念的日渐销蚀。
弗洛伊德(Freud)与布洛伊尔(Breuer)出版《癔症研究》( Studies in Hysteria )距今才不过
一百年而已。19世纪末的医师们不得不着手处理这样一类患者的痛苦:他们既不能从宗教传统
中找到慰藉或投注情感,也无法被医学方法治愈。跌入现代主义裂隙中的人越来越多,可对他
们来说,关于灵魂受苦的科学尚不存在。
如荣格所说,在所谓的社会科学中,心理学是最后一个进化的,因为此前维持它的是那些伟大
的神话和制造神话的机构。心灵(Psyche)是希腊语中“灵魂”的意思,从词源学上讲,它可以追
溯到两个并存的源头:一个是“蝴蝶”,借助这个比喻,那神秘、优美却又飘忽不定的特质将我们
对灵魂的体验戏剧化地呈现出来;另一个则是动词“呼吸”,类比的是那一阵看不见的气息,在人
们出生时降临,又在死亡时离去。
然而,事实是多么讽刺啊,现代心理学往往只处理这样的问题——能被人观察并转换为统计模
型的行为,或是能被再次设定的认知,要么就是能被药物矫治的、生物化学方面的异常现象。
虽然这些治疗手段确实效果显著,对患者很有帮助,可它们却极少面对现代人最为深切的需
求,即让人生旅程变得有意义。无论是何种疗法,无论在初始时能多么有效地缓解症状,只要
它不去解决灵魂的问题,到最后必定也只是肤浅的。
荣格指出,神经症“最终必须被理解为:一个尚未发现其意义的灵魂所遭受的痛苦”。 请
注意,他并没有把痛苦排除在外,他强调的是,神经症防御和对抗的是人生的“没有意义”。类似
地,他认为神经症属于“不真实的痛苦”(inauthentic suffering),而真实的痛苦是对“存在”
(being)之伤痛做出的现实反应。若是这样的话,那么治疗的目的就不在于消除痛苦,而在于
从痛苦中穿越出来,走向更为广阔的意识,这个被拓展了的意识能够涵容生命中对立的两极。
正如奥尔多·卡罗德努特(Aldo Carotenuto)观察到的:
心理疗法不是搭建出各式各样的模型,然后根据这些模型把人类的痛苦分门别类,贴上标签;
它是对痛苦的检视,是发现外部事件与内在事件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人的人生都
是由这样的联系构成的。
荣格认为,神经症不只是对人生创伤的防御,更是一种想去疗愈这些创伤的无意识的努力。因
此,暂且不谈它的后果,我们至少应该尊重它的意图。出现症状,其实是患者在表达想要获得
疗愈的愿望。我们不该压抑它们或消灭它们,而是应当去理解它们所代表的创伤。这样一来,
创伤,以及渴望获得疗愈的动机,就有可能帮助患者拓宽自己的意识。卡罗德努特也指出:
“(一个人)决定借助心理疗法来处理痛苦,而不是求诸某个全能的神灵,即是主动选择了意
识。” 尽管代价甚巨,但这种清醒的意识会让我们的内在变得更加宽广、丰盈。
令荣格心理学焕发出生命力的核心思想就是“无意识”的存在。这个观点似乎已经不稀奇了,但那
些不认同心理动力论的心理学派实际上并不认可它;绝大多数人也不认为它会出现在自己的日
常生活中。对于这股在内心中自主运作的力量,极少有人意识到它的深刻,人们基本上没有能
力理解它,也无法凭着意愿让它消失,甚至都没法预测它。因此,源自我们内心的那些强迫行
为、上瘾、情结的投射就被转移到了外部世界中,在无意识的状态下给他人造成了重负——虽
然我们自己也抱怨它们的沉重。
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存在一股巨大的、睿智的、天生就有的力量。这个想法理应令人感到踏
实和欣慰,可实际上它往往让人心神不宁。儿时的经历、脆弱、面对外界环境时的无力感,还
有依赖的正当性,我们对这些东西太熟悉了,它们深深地镌刻在我们心里;而这一切的对立
面,也就是个体的自由、个体的责任,都令人望而生畏。
心理动力学疗法希望推广的,是以一种崭新的态度来对待心灵。心灵力量中那些令人望而生畏
的东西,同时也带有疗愈的动机。如果我们能够与这种内在的力量建立联结,而不是每次都根
据外部力量做出条件反射式的调整,从而加剧与自我的疏离感,那么我们心中就会感到非常踏
实,就好比稳稳地站在某种深层次的真相之上,站在我们最自然的天性之上。在这种与深层真
相建立关联的时刻,即与荣格所说的“自性”(Self)相遇之时,人会感受到一种联结与支持;要
想缓解普遍性的、对被抛弃的恐惧,这种联结感与支持感必不可少。正如卡罗德努特所说:
成熟其实并不意味着不会被抛弃,而是我们主动地抛弃了一些幻象……如果我们能够承担得起
独处的焦虑,全新的地平线会铺展开来,而且我们终将学会不依赖他人也能独立存在。
独处的概念很容易理解,我们也都声称自己很渴望它,可人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我们都在
逃离这种焦虑——彻底地、全然地面对自己,毫无遮掩地暴露在天地之间。文化,正如我们所
设计的那样,似乎只是一种余兴表演,其目的就是避免孤独。实际上,人们最不情愿放弃的幻
想就是这个念头(另一个不愿放弃的幻想是永生不朽)——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会治愈我
们,照顾我们,让我们免于踏上那趟向我们发出召唤的、令人生畏的旅程。难怪我们要逃避这
趟旅程,把它投射给某位上师,而且从来不愿与自我融洽从容地共处。
千方百计地避免灵魂陷入阴郁状态,这个行为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痛苦。这是因为,一个从来
不曾松弛下来、从来不曾放下“我想要获得幸福、想要无忧无虑”的急切渴望的人,永远也无法获
得安宁与休憩;相反,他将无可避免地被拉下泥沼,时常感到痛苦。大自然总会有潮起潮落,
这不正是它的天然节律吗?一年有四季,女性每月有经期,我们每天也会感受到高低起伏的生
物节律,还要把一生中三分之一的时间都交给那个名为“睡眠”的黑暗世界,这不正是我们的亲身
体验吗?所谓的“被动的自然”与“能动的自然”(natura naturata, natura naturans),这种节律不正
是自然的天性吗?《传道书》(Ecclesiastes)中反复吟唱的讯息,不正是对这种节律的赞颂吗?
自我,即对“我是谁”在意识层面上的感知,是充满情绪的、不断重复的个人经历的累积。它是意
识的核心情结,而意识的边界是流动易变的,也很容易遭到侵犯。我们需要自我来主导意识层
面上的日常生活,调动心理的能量,并引导它们流向目标;我们需要自我来维持一定程度的自
洽和延续性,这样我们才能一天天地走下去,并适应各种各样的情境。可是,自我的核心目标
是安全感。不难理解,安全感就是要对抗从内在生发出的、无意识的潮涌,并与引起巨大冲击
的外来能量交锋。出于这个目标,也就是对安全感不可避免的、强迫性的渴望,自我变成了一
个神经质的小傻瓜,在人生的客厅里东跑西撞,捡拾杂物,弄得四处尘土飞扬,把那儿变成了
一个更加不舒适的地方。
从自我对待世界的狭隘视角来看,它的任务就是追求安全感、掌控感,以及平息冲突。然而,
从深度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自我的恰当角色应当是与自性和世界形成一种对话关系。自我应当
保持开放,尽力做到有意识,并且愿意交流协商。荣格将这种自我与自性之间的对话称作“交换
意见”(Auseinandersetzung),是对独立但相关的现实的辩证交流。“自性”这个概念超越于现实
之上,也高于自我,它不仅是对紧张的自我的局限性的认识,也是对自我在更大背景下的地位
的认识。荣格提出的个体化(individuation)概念——即人生的目的是借由成为个体来服务于生
命的神秘——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是极其深刻的贡献,或是像有人所说的,是一个为现代社
会提出的神话。
个体化迫使自我与自性之间展开持续不断的对话。在交流之下,割裂的心灵或许会愈合一部
分。因此,如果给自性下一个实用的定义,或许可以说,它是“我们内在秩序的原型”。这即是
说,自性是心灵的一种活动,它的功能就是促进个体的成长。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自性令我
们成为自己,或者说,通过在躯体层面、情感层面和想象层面上的体验,我们体验到它塑造我
们的过程。我们也可以把自性描述为一个“乐意当模具的模具”,也就是说,它既是目的论的,也
是情境性的;它既是目标,也是模具。那么,心灵或灵魂,就只是我们指代那个神秘过程的词
语而已——借由这个过程,我们得以体验到何为朝着意义前行。
就我们所知,人类是唯一总想去追寻意义的物种,就好像有某种力量在驱使我们似的。这种被
驱使的感觉往往令人痛苦,但身不由己,我们总忍不住要去追寻它。正如歌德在开头的引言中
所说的那样,我们永远也无法理解这种神秘,否则它也称不上神秘了,但是,在对关系的具体
化中,在对梦想生活的隐喻中,在对深度的猛然顿悟中,我们时常领略到它的暗示。无论我们
是从何处感受到深度的存在,是从宇宙中、自然中,还是从他人或自身,我们都置身于灵魂的
辖区了。
出于对安全感的渴望,自我会把这种深度简单地概括为不由分说的确定性,以及可量化的预
言。可是,“我们是不完整的碎片”,其中的神秘感不仅远远超出了我们能掌控的范围,它甚至超
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若想与灵魂搭通关系,大概只能借助于对心灵世界的想象——无论这想
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不管我们是否真的能理解它们。我们也有可能去往自我的地盘
寻找灵魂,比如神学、音乐或爱情,结果却是,我们被更加频繁地拽落到沼泽地中——那里是
我们最不想涉足的地方。这种“拽落”,就是灵魂的普遍性、自主性,以及不可或缺的神秘性的明
证。
对许多人来说,灵魂这个概念可能过于虚无缥缈,然而,正是为了尊崇它那含混不清、飘忽不
定的特质,我们必须保留它。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中,如今我们称之为“泛灵
论”。(下回有人打喷嚏,而你脱口说出“老天保佑你”的时候,想想看。)处于退行状态时,人
人都会把心灵投射到大自然与他人身上。灵魂是否真的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领域
里,人能够体验到神秘的深度,以及它给出的暗示——正是这些构成了灵魂。这种暗示有种奇
异的熟悉感,因为我们身上就有相似的东西——同频就会共振。波德莱尔(Baudelaire)在诗句
中追忆人与自然尚未如此割裂的年代:
自然是一座圣殿
那些有生命的柱子 时而吐露出含混的语音
人类在象征的森林中漫游
森林以亲切的目光将他打量
我家离大西洋的海边约有一英里。每年夏天,大批大批的游客像旅鼠一般蜂拥而至。他们并不
是为了避暑,因为到处都有空调,待在屋里可比挤车和驱赶沙蝇舒服多了。这必定是因为,我
们内在的某些东西与海洋的浩瀚幽深发生了共振。那引人敬畏的、无从触底的深度引发了我们
的共鸣,因为我们的内在中也蕴含着同样的深度。我家离大西洋城(Atlantic City)的赌场也只
有一两英里,每年造访的游客里绝大多数都是西方人,人数比去迪士尼乐园或纽约的还多。同
样,这必定是因为,在铺着绿绒毯的赌桌上,在叮当作响、彩灯闪烁的机器前,灵魂被投射了
出去。人们必定是在寻求片刻的超越,瞬间的赋权,还有与他者(the Other)稍纵即逝的相遇。
人们寻求的,其实早已存在于内心,然而我们轻易地将之投射到海浪与沙滩上,或是安乐无
忧、优渥富足的梦想中。
灵魂总是居于当下的,但人们会处于无意识的状态,因此才会向外寻求。诗人荷尔德林
(Hölderlin)深刻地洞察到了这种失落:“上帝就在近旁,却难以企及;不过,危险出现的地
方,救赎也在聚集。” 心灵将我们拉回来,拖向深处,拽回内在,只为把我们带回灵魂
面前,这难道不是奇迹吗?
个体化的目标并不是有些人以为的那样,它不是让人沉迷于自恋,一心只想着自己,而是要借
由个体,将天地的宏伟意图显化出来。每一个人,无论多么微不足道,身上都承载着一小块天
地赋予的终极目标,这个目标的起源笼罩在神秘之中,若要实现它,就需要我们扩展意识。如
果这是真的,而且我相信这是真的,那么,个体化的任务就是追求完整——不是美德,不是纯
洁,也不是幸福。而完整就包括了被拽落泥沼,也就是心灵经常迫使那个不情愿的自我所做的
事。
在我们人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个体化的进程并不取决于那帝王般的、狂妄自大的自我,而是
取决于内心中的那些“农夫”,它们会发牢骚,会有怨气,基本上毫不在乎那位帝王的意志。有多
少漠然的君主都被不起眼的小人物推翻了?我们那无法预测的人生旅程也是一样。尽管灵魂才
是最重要的,可是,受到惊吓、不知所措的自我拼命地忽视沼泽地的存在,压制它、否认它,
仓皇地逃离它。然而,在人生的很多时间里,我们都得待在这泥沼之中。之所以会有神经症这
个牢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拒绝承认沼泽地的存在。
荣格说,他不会在过去中寻找神经症的成因,而是在当下:“我会问,患者需要做,但又不愿做
的任务是什么?” 无一例外,这种任务包含更高级别的自我负责,更坦诚地面对暗影,
走得更深更远,进入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所有这些心灵状态都具备灵魂层面的意义。我们的
任务就是全然地经历它们,不压抑它们,也不把它们投射到他人身上,造成伤害。如果我们不
去面对内在的东西,就要一直背负着深层的隐患。为了疗愈自身,也为了向世界提供疗愈,我
们需要时不时地蹚过泥沼。虽然我们不愿意涉足那些地方,但或迟或早,我们总会被拖拽进
去。
在研习精神分析的那些年里,我的一个朋友总爱说一句话:“可它意味着什么?”无论是跟别人起
了冲突,还是做了噩梦,只要遇到不愉快的状况,她都会这样问。我觉得这很烦人,可她是对
的。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们拓宽了自己的地平线,也活得更有尊严。
灵魂层面的功课不仅是疗愈的先决条件,也是心智成熟所必需的。卡罗德努特再次精当地写
道:
心理治疗的终极目的不在于像考古一样,不断发掘儿时的伤痛,而是逐渐地学习,努力地接纳
我们自身的局限,并在此后的余生中努力自行承担起痛苦之重。心理医生的工作并不是提供解
脱,让患者摆脱那些造成严重不适的症结,而是要加重不适,教会患者成为成年人,此生第一
次去主动面对“独自面对痛苦、被世界抛弃”的感受。
在接下来的篇章中,我将会探索一些黑暗的领域。我们每个人都曾涉足其间,并渴望逃离它
们。我不会提供脱离困境的方案,因为它们并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说,它们是一种始终
会存在的、对旅程的体验——那是心灵分派给我们的旅程。
在一封1945年写给奥尔加·弗罗贝-卡普泰因(Olga Froebe-Kapteyn)的信中,荣格提出,史书
(opus),即灵魂的功课,由三部分组成——“洞察、忍耐和行动”。 他写道,心理学只
能对洞察的部分有帮助。在洞察之后,就需要道德上的勇气,去做必须做的事,还需要力量,
去承担相应的后果。在后文中,我会举出一些具体的案例,但它们体现出的范式却是真正通用
的。绝大多数案例是真人真事,但已做脱敏处理;有两三个是撰写的,但比起真人真事,它们
更加接近真实……
接下来的内容既是心理学上的观察,也是一系列深入的思考。我的目的是引发反思,同时也请
你给自己颁发一份批准:准许自己带着更清明的意识,去造访这些沼泽地。说到底,我们并无
多少选择,因为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此生都得在那儿花去不少时间。与这些黑暗的力量搏斗,
犹如雅各与天使角力 ,二者异曲同工。正如诗人沃伦·克利沃尔(Warren Kliewer)在
“摔跤天使挑战雅各”中所写的那样:
你当然乐意 不再追寻上帝
如果停止追寻是个选择……
所以来抓我啊,莽汉,让我们来斗一场
以搏斗那手忙脚乱的、绝望的美 致献我们的敬意
第一章
无处不在的内疚
在预约电话中,艾尔特别指出两点。第一,她有连续的两个小时,而且这是我们见面的唯一机
会。第二,她会寄给我一张翻拍的照片,让我提前好好看看。我同意了。三天后,照片寄到
了。
照片十分老旧,皱巴巴的,但挺清楚,上面是一个女人牵着两个孩子的手。显然这是从某个档
案里复制下来的,因为照片底下的说明文字是童年记忆中的那种老式打字机打出来的,字迹边
缘斑驳不清,偶尔还有字母缺了一块。“来自卢布林的佚名女子带着她的两个孩子,走进迈丹尼
克的焚尸间(Majdanek Krematorium)。约为1944年3月。”
照片上的女子大约二十八九岁,穿着一件薄薄的棉布外衣、羊毛袜、黑鞋子,面朝左方;她的
右臂拢着一个差不多六岁的孩子,左手拉着的那个大概有四岁,离她稍有点距离。我无法把眼
光从这张翻拍的照片上移开。女子的脸上写满了紧张和警觉,显然充满了焦虑,但永远定格在
朝前看的状态。两个孩子被她用手臂围拢住,跟她一起往前走,就像一个人似的。年幼的那个
孩子看上去吓坏了,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身躯显然在向后躲。或许她被噪声、人群,或照片
左方的什么东西吓到了。
时光中的那一刻永远冻结了。其中的讽刺令我感到难过,因为我知道照片上的这几个人当时不
知道的事情——这就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后一刻,他们将会被驱赶到淋浴室中,要不了多久就会
拼命抓挠彼此,抓取那并不存在的天堂,去争取未受污染的空气。他们知道吗?有些事孩子们
不知道,但那位女子知道吗?那连根拔起式的迁移,火车上的运送,心中的困惑,不知从何时
起就消失不见的父亲,还有空气中飘着的可怕气味,一旦闻过就会烙入神经,令逃脱的人永远
无法释怀……他们知道多少?这让我心神不宁。在拍下照片的这一刻,要是他们不知道该有多
好;要是这一刻依然留有希望——那长着明亮又脆弱的双翼的东西——该有多好。
约好与艾尔见面的那天,我很早就醒了。我知道自己梦见了那个地方:在铁道交汇之处,欧洲
永远终结了“道德进步”这个脆弱的概念。照片上有一处细节一直在我心头盘桓不去:那个年纪更
小的小姑娘,拖在后面的那一个,她的左腿离镜头更近,所以能看见那条腿上的羊毛袜破了。
她必定是摔了一跤,蹭破了袜子。我想知道她的膝盖有没有流血,那一刻她还疼不疼,妈妈有
没有安慰她。那可怕的大门在她面前张开血口,而我居然还在担忧她的膝盖,这简直毫无道
理。或许这属于某种道德上的转喻吧。当一个人无法承受整体的时候,就会转而关注一些细小
的、具体的、能够理解的部分。 我想搂住那个孩子,摸摸她的膝盖,对她撒个谎:这就
像个糟糕的梦,很快就会没事了。但我不能。我永远也没有机会触碰到她,她的恐惧将永远停
留在这个可怕的世纪——那些嶙峋的肋骨、空洞的眼神——并不断地萦绕、徘徊。
艾尔快八十岁了。她的英语完美无误,但我听得出,她的母语隐藏在那依稀可辨的口音背后。
我们见面时是夏天,但她穿着黑色的半裙,白衬衫和白毛衣。你会觉得,这身装束就像是她的
某种制服,或是她向来只穿这样的衣服。她说:“今天我跟你要了两个小时,给你讲个故事。如
果你想,可以打断我,也可以提问,但到最后我不会要求你做任何事,而且这是我最后一次来
这里。”
心理治疗可不是这种做法,但我感到,我必须答应她的条件,因为在那一刻,好像有些东西远
比游戏规则重要得多。
“我寄给你的照片,你认真看过没有?”她问。
“是的,我看了。我甚至梦见了它。”
“我也是。这正是我想谈的。照片上那个女人就是我。”
“可这……我以为她死了。说明文字上说,他们正在走向焚尸间……”正说着,我看出来了,面前
的女子正是照片上的那一位。五十年的时间相当漫长,但那双眼睛没有变;她也没有发福,颧
骨处的皮肤依然紧致。
“当年我家在卢布林,我是医生的女儿。刚开始运送犹太人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在意。我们不是
犹太人。我父亲年纪太大,没法参军,战争不会波及我们。而我还年轻,打仗对我来说是很遥
远的事。我希望能遇见个意中人,结婚,同时也找份工作。拍那张照片的时候,我二十六了,
这个岁数还没结婚,已经不小了。我担心遇不上合适的人了。”
“可你怎么去了迈丹尼克?你不是犹太人啊,你是安全的。”
“现在回头看看,我真觉得一切都再蠢不过了。那天是星期五,我去市场帮母亲买菜。就在那一
天,德国人的特遣队开始了抓捕行动。他们知道犹太人会在安息日开始之前去市场。他们包围
了市场,另一批人去了犹太区,同时把整个街区都封了。我被封在里面。”
“你没有告诉他们……”
“当然说了,一开始就说了,我说我是基督徒,不是犹太人 ,可其他人也都这么说。那
帮人哈哈大笑,把我们所有人都赶到了卡车上。”
在诉说中,她好似又回到了那个地方。我不能说她在害怕,但在脑海中,她确实身临其境。或
许她保持了某种解离状态,但她真的回到了当年。她告诉我,她如何跟大批人一起被车子拉到
了中央火车站,一路抗议也没有用,最后还是被轰到了火车上。几个小时后,吓呆的人们被带
到一个栈桥,旁边就是人称K-Z Lager Majdanek的迈丹尼克集中营。这是所谓的“最终解决方案”
(Endlösung)里的灭绝中心之一。随着人把自身不能容忍的部分疯狂地投射到“他们那批人”身
上,长达几个世纪的文明文化轰然坍塌。
我知道此时不该插话。她继续说下去。她告诉我,他们是如何被推搡到一个军官面前,而此人
要把他们分成左右两队。哪一队去往焚尸炉,哪一队去往营房里疫病丛生的日子——那里有伤
寒、严酷的劳役、每天仅八百卡热量的伙食,到最后,在早已被摧毁的肉体中,人的精神也终
将颓然倒下。
排在艾尔前面的是一位母亲,她带着两个孩子,一个被吓到不敢说话,另一个在哭。他们走过
军官面前,那军官冲母亲笑笑,指了指右边,但让孩子们去左边。女人尖叫起来,紧紧抱住孩
子们不放,可有人过来把她拉开,推搡到右边那一小群人里去。两个孩子站在那儿,吓得不敢
动,被妈妈的哭喊声弄得不知所措。紧接着,轮到艾尔走到了军官面前。讲述到那个关键的时
刻,那个“分拣”的当口,她再也抑制不住,在我办公室里尖声喊了出来:“我是基督徒,我不是
犹太人 !”那军官答说,现在说这个太晚了,而且好多人都说自己是基督徒。艾尔接着
告诉我,当时她是如何报出父亲的姓名、爷爷的姓名,还有一长串当地著名医师的名字,卢布
林的一所医院还是以其中一位命名的。
军官停下来,说:“行了,知道了,可你在这儿看见的已经太多了,不可能让你回去。把这两个
小孩领到浴室门口,让他们进去,然后你上那边一队去。不过你要跟他们一起干活,而且永远
也别想离开这儿。”
“我没法告诉你那一刻我有多么高兴,”艾尔说,“我不用进那里边。我会去干活。我会活得长一
点儿。我推着孩子们走。一个紧紧地抓住我,另一个我得拽着走。就在那个时候,有人拍下了
你看见的这张照片。我不记得当时有人拿着相机。能活着,我太高兴了。我一路拉着孩子们,
把他们带到浴室门口。囚犯里的头目把孩子们拽了进去。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们。”
那一刻,我再次察觉到,她又回到了当年,因为她叙述中那片刻的暂缓,多少带点如释重负的
意味。她重重地靠向椅背,沉默了约有两分钟,然后继续说了下去。她向我讲述起集中营里的
生活,她是如何在那段暂缓的死亡判决中生存下来的。她那坚韧的年轻躯体熬过了严酷的劳
役,忍受着被剃成光头的屈辱,还有日复一日的稀粥。等到苏联人解放集中营的时候,那里只
剩下一两百个尚能行走的骷髅,其中有不少没过多久就死于疾病,或饥饿的后遗症。
“战后我搬到了华沙(Warsaw)。我父亲那边的许多亲戚都去了美国,所以我拿到了签证,去了
底特律(Detroit)生活。多年来我都不愿想起那些日子。我没有结婚。我怕我会生孩子。我知道
我已经失去了爱的可能。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图书馆工作,直到四年前的一天,我偶然在一份二
战的历史资料里看到了这张照片。我没法跟你说清楚那种感觉,一切都回来了,那种噪声、气
味,那种恐惧……但最主要的是那种战栗的感觉——我可以多活一阵子。”
此时,我以为我明白她为何来见我了。以前我也和幸存者一道工作过。比今天我们称之为“创伤
后应激障碍”更糟糕的是幸存者的内疚,那份内疚感往往太过沉重,以至于他们决定——有意识
的或无意识的——像死了一样生活。于是,他们麻木地过日子,生活在沉默和怀疑之中,永远
不曾感受过活着的滋味。
可是她说:“我没想从你这儿获得任何东西。你什么也不用对我说。我只需要你听着就行。几年
前我信了犹太教,或者说试着去信吧,可我没成功。我没法去信仰他们的上帝,那个抛弃了他
们的上帝。但我听说了melamed vovnikim的传统,意思是,无论这个世界上发生了多么糟糕的
事,上帝都留下了二十四位公正的人,如果你向他们讲述你的故事,上天就会听见。”
“我不敢说我是其中之一,艾尔。”
“一有机会我就跟人讲这张照片上的故事,我会一直讲下去。你或许是,或许不是。这辈子我还
有点儿时间,也还有必须去找的人。”
她走的时候,我告诉她我不能收钱,因为我觉得没帮上忙。她说那你就把那张照片留下吧。我
照做了,直到今天我还留着它。她走出了我的办公室,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可我没有一天
不想起她。
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 观察到,奥斯威辛(Auschwitz)确实很恐怖,但它只
是日常生活的夸张版本。 弗兰克尔有资格这么说,我没有。但我认为我明白他的意思:
生活中始终不缺灵魂层面的重大议题,每天都能遇到;以及,那些最好的人,用他的话说就是
——与别人分享自己的食物、不肯将自己受到的残酷对待加诸他人的人,没能存活下来。因
此,艾尔的照片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虽然我们的人生是安全的。命运把她置于那样的境
地,没有一个人敢说,万一遇上同样的事自己会做出什么行为;人人都有道德上怯懦的时刻,
没人能因为她强烈的生存渴望而责怪她。然而,我们也都能理解,她为何要像个现代的水手一
般,带着那张照片四处漂泊——那是悬挂在她脖颈上的内疚——到处寻找公正之士,就算不能
被宣告无罪,至少可以寻求被人听见。
内疚就像一只硕大的黑鸟,栖落在我们绝大多数人肩头。荣格关于“阴影”的概念提醒我们所有
人,我们会踏足禁区,会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自恋且怯懦。有谁不记得拉丁诗人泰伦斯
(Terrence)的金句“我是人,凡属于人的于我都非异类”(Ego sum humanum.Nihil a me humanum
alienum.)呢?我是人,有关人性的一切对我来说都不陌生。可是,正当我们祈望欢庆,祈望自
由,不再受过往约束时,那只硕大的黑鸟依然落在那儿,刺耳地嘎嘎大叫。它粗嗄的叫声破坏
了那一刻的欢悦,一切又滑落回从前,还伴随着那个名叫“耻辱”的侍从。
我们应当在反思中深入辨析内疚这个概念,这是因为,就像许多概念一样,诸多不同类型的体
验会被统归到一个宽泛的名词之下。我们真的需要仔细地分辨以下三种内疚:
1.以责任的形式出现的真实的内疚
2.用于防御和对抗焦虑的非真实的内疚
3.存在性内疚
真实的内疚
尽管各个国家的司法系统都承认,低内疚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比如当事人低于特定年龄,或
是智力受损,但本书读者肯定都不属于这些情况。如果说,个体化这项任务要求我们尽力拓宽
意识,那么,没人当得起“从未做过亏心事”这几个字。没有一个意识清明的人敢说自己一件亏心
事都没做过,这既包括个人层面,也包括集体层面——正如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在《堕
落》( The Fall )中明确指出的那样。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而这个社会制造出了大屠
杀,还有绵延不断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恐同等问题,无论我们有没有主动共
谋,都脱不了干系。
因此,个体的健康发展包括在合理的程度上承认内疚,也就是说,担起责任,承担自己的选择
带来的后果——无论在做选择的时候是多么无意识。
古希腊悲剧的精髓就在于,它承认在文化或个人心中存在某种力量,导致一个人做出了可能会
令其他人痛苦的选择。在绝大多数悲剧中,合唱队——代表的不仅是剧作者的视角,还包括集
体智慧——见证着命运的运作。命运安排出各式各样的可能性,也给主角造成创伤。古希腊有
个词叫作hamartia,它往往被翻译成“悲剧性缺陷”,但我更喜欢“片面的视野”这个说法。由于
hamartia的存在,个体做出了无法预见后果的选择。借由承受痛苦,个体有可能通过承认、忏
悔、与神祇重新建立起恰当的关系而获得救赎。
在《中年之路》( The Middle Passage )中,我提出,这种片面的视野与童年时期的经历密不可
分,并且会让个体——往往是在人到中年的时候——体会到诸多错误选择造成的现实后果所带
来的冲击。以下两个简明的案例有助于理解这一点。
贫困的童年给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他用过度补偿的方式,即苦
苦追求认可与尊重,来回应曾经的贫困。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之后,那片面的视野继续停留在
无意识的状态,导致他做出了糟糕的选择,最终招致公众的唾弃。但从没人写过理查德·尼克松
的晚年生活。基本上,他从来不肯承认自己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还极力声明这就是政治的规
则。他从不曾看到,他自己才是那些糟糕选择的源头。由于如此“谦卑”,他不愿与道德结构重新
建立起正确的关系,也就拒绝了获得内心安宁的机会。
与此形成对比——正如1993年的影片《机智问答》( Quiz Show )中演的那样,查尔斯·范·多伦
(Charles Van Doren)出身美国著名的书香门第。他一心想获得大名鼎鼎的父亲的认可,却全是
徒劳;与父亲在智力方面比拼的时候,他只能拿到第二名。于是他没能忍住诱惑,在一个智力
问答节目中造了假,赢得了金钱、名声,以及大众的喝彩,这一切都是他父亲永远也不可能得
到的。但造假行为最终曝光,令他声名扫地。值得赞扬的是,他站到了调查委员会面前,为自
己的选择承担了全部责任,并承认自己丢失了道德的指南针。
在这两个案例中,人人都能找到熟悉的东西。敢于承认错误,承认自己做出了糟糕的选择,应
当为伤害性的后果负责,这不仅仅是获得智慧的开端,更是卸下心中重担的唯一途径。
在有信仰的社群中长大、知道忏悔之圣仪的人,有机会从过往中解脱。这是因为,名为内疚的
那只黑鸟不但能破坏当下的生活质量,还会把我们跟过去牢牢地绑缚在一起。肩负着往日的重
担会让人心神俱疲,还会削弱我们做出新选择的能力。
但绝大多数现代人都没有忏悔告解的可能,要么是因为他们属于另外一种文化传统,要么是因
为他们不再具备忏悔所要求的坚纯信仰。艾尔寻找公正之士的步伐不会止息,这是因为,一旦
她找到了,连信念带来的力量可能都会失去,而正是这种力量让领受恩典成为可能。不过,即
便是不知晓忏悔的神圣历史的人,也有可能从以下的“3R”中得到指引:承认(recognition)、补
偿(recompense)、解脱(release)。
对于愿意以成熟的方式来处理内疚的人来说, 承认 是不可或缺的。有意识,意味着一个人承认
对自身或对他人造成了伤害。很可能在最初的时候,人并不知道自己造成了伤害,但是,当承
认的时机到了的时候,他必须有意识地坦承:是的,我做了什么,导致了什么,我为那个结果
负责。反社会的人,以及有其他一些性格障碍的人,他们的自我容量被破坏得如此严重,以至
于无法承担责任。他们不但有可能对别人撒谎,也有可能同样地欺瞒自己,不断地把责任投射
到外界去。
人们对心理治疗有种普遍的误解,以为做治疗就是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责怪父母、社会和经济
状况上,而不去处理当下的问题。诚然,那些经历确实会对我们的性格塑造产生很大影响,但
心理治疗的精粹在于承认这一点——我应当为自己的选择、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其他一切都
是对真正意义上的“成年”的逃避。这种承认可能会令人感到惭愧,甚至很受打击,但进一步的否
认或无意识会把人与过去牢牢地绑在一起,毫无改变的希望。因此,在十二步戒瘾法(Twelve
Step program)中,大量工作都建立在以下基础上:停止否认,承担起自己人生的责任,并且在
有可能的时候,对自己造成的伤害做出补偿。
能做 补偿 的机会其实很少。许多做过的事情已经覆水难收。艾尔永远不可能把孩子们带回来
了。她试着追随他们的信仰,可到头来,如此真心实意的努力并没有成功——这个举动其实于
事无补。她没有要孩子,或许是因为害怕在自家孩子身上看见迈丹尼克那两个孩子的影子,或
许是因为她感到应当惩罚自己。但对她来说,直接补偿是没有可能的。如果有补偿的机会,至
关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唯有真诚悔过,补偿才有意义。但凡不够真心实意,就是对灵魂的物
化,到头来补偿也不会见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补偿都是象征性的,这不是说它不实在,而
是说,这种偿还显然是心理层面上的。
我们的刑罚体系为何效果如此之差,部分答案或许就在这里。英文中的penitentiary(监狱)和
reformatory(少年犯管教所)这两个词是这样来的:如果一个人被驱逐出去,得不到群体在心理
层面上的支持,他或她就会penitent(忏悔),于是道德层面上的reformation(革新)就会发生。
但现实中的刑罚体系实际上是惩罚性的,人们极少去思考这个问题:如何帮助一个合法地被证
明有罪的人意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并为之担责,而不是责怪社会,或单纯地归咎为自己运气不
好。
当一个人能够真诚悔过,当实际的或象征性的补偿已经做出,那么他会体验到解脱的恩典。对
那些依然能从忏悔的圣仪中获得帮助的人来说,牧师充当了人神之间的中介,为人提供宽恕,
帮人获得解脱。这种宽恕被视作上帝的行为,用力争取是得不到的,只能从悔过中寻得;这就
叫作恩典。对于那些不属于此类宗教社群的人来说,寻获恩典可不容易。不过,对于那些努力
拓宽意识疆域的人来说,承认、补偿、解脱的三部曲依然是可以实现的。在拓宽意识的过程
中,人必须接纳自己的阴影,承认它的存在,并为之负责,由此,他开始以全新的方式进入世
界。
荣格清晰有力地写出了何为健康地承认内疚。这不意味着否认或逃避,当然也不是继续卡在过
去。
这样的人知道,世上发生的无论何种错误,其实都在他自己身上,只要他能学着处理自己的阴
影,他就已经对世界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面对当今那些庞大的、尚未解决的社会问题,他已
经成功地肩负起了一部分,哪怕只是微末的一点点……当一个人连自己都看不见,也看不见自
己无意识地把黑暗带入了一切行为之中,他又怎么可能看清其他呢?
非真实的内疚
在很多时候,或许可以说是经常吧,我们所说的内疚并不是上文所说的“真实的内疚”。这种内疚
往往表现为微微的紧张或不安,或是感到四肢僵住了,甚至还会有一点头晕。这确实很奇怪。
这种独特的体验常常在身体上表现出来,而这向来预示着内心的某种情结被击中了。情结被激
活(我们会在第八章中更加深入地讨论这一点)的征兆是:涌起的能量超出了当下情境的合理
需要,人感受到躯体层面上的“入侵”,在身体上体验到了情绪状态。这些线索表明,此人体验到
的实际上是潜藏在意识层面之下的心灵活动。
而且,此处所说的这种内疚,大部分是对较为严重的焦虑的防御;这是人在感受焦虑时的附带
反应,当时很难分辨清楚。例如,我们常听到人说,当他们对别人说“不”的时候,发脾气的时
候,或是感到自己不是完美父母的时候,就会感到内疚。这种感受是从孩提时代就慢慢成形
的。孩子都有天然的自恋,他们的欲望会非常自然地表现出来,可是,这些欲望立即与成年人
的世界迎头相撞。大人拥有无边无际的力量,他们会惩罚你,不赞同你,不喜欢你。没有哪个
孩子能在这种荒野中坚持很久,他们很快就学会了抑制那些不被接受的冲动。
一个男子回忆起六岁时在自家门廊上唱歌的情景。他妈妈吼了他,不许他这么“吵”,他发誓以后
再也不唱歌了。长大后,在高中必修的音乐课上,他的舌头就像打结了一样,他完全唱不出
来。老师了解到他是真的不能唱歌之后,允许他整个学期都默默地站在合唱队后排,也给了他
及格的成绩。成年后,这名男子甚至在淋浴时都不会试着哼唱几句。与更严重的虐童案例相
比,这个问题看上去没什么大不了,但它清晰地反映出,与无所不能的父母之间的“碰撞”被孩子
内化后,具有多么强大的力量。在进入社会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无可避免地会遇到类似
的、与强势力量的碰撞,我们开始抑制自己的冲动,并将之渐渐内化。有时,一些人甚至会防
御一切包含情感的动机,最后与自己的真实情感彻底失去联系。
因此,我们称之为内疚的东西,往往是一种孩子式的、保护性的、被动反应的情绪状态。那种
微微的紧张和不安,突如其来的冰冷感,都是因为反射性地想起了当年踏入父母那名为“不赞同”
的荒野时的感受。好比说,我们感受到一种自然的冲动涌起,比如气愤吧,可有一只手忽然伸
了出来,就像坐在汽车里的大人物似的,把这种冲动一下子扼杀了。这种反射性的反应能把一
个人的人生约束得死死的,以至于他或她会产生相当严重的自我疏离感。例如,对别人说“不”时
感到内疚,实际上是在防御“他者会因此不高兴”的可能,并由此激活了人人都背负着的、浩瀚无
边的情绪库。
这类非真实的内疚还有可能被用来对抗对他人的憎恨、嫉妒、狂怒、色欲,以及其他一切阴影
因素。荣格指出,一个没有阴影的人——意思是一个人完全没有意识到阴影的存在,并且极力
防御阴影——是肤浅的人。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接受了这样的教育:要做个好说话的人,别表露
真性情;要随和宽容,而非耿直;要圆滑变通,而不是坚持己见。我们可以想象一个采用十二
步戒瘾法的、“不当老好人”的小组里的情形:一个成员讲述他或她上一周不由自主地又变成了老
好人,对此十分后悔;或者,当他或她决定不当老好人时,心里有多么内疚。
这种“防御深层焦虑”式的内疚,反映出的是一个人很少被允许做自己。它反映出生命早期受到的
规训所具有的难以估量的强大力量;同时,它也为人们提供了从早期经历中恢复和疗愈的机
会。当一个人感受到这种内疚的时候,可以这样自问:“我这是在防御什么?”通常,答案都会归
结到恐惧上——害怕别人会因为自己的某个决定而不悦。
在真实世界里,如果你想做一个有价值的人,而不是情绪变色龙,你势必要做出很多选择,而
取悦别人不该是你的首要目的。从心底涌出的焦虑之所以令人无法招架,完全是因为它来自最
脆弱的孩提时期。由于这份能量从未流走,而是滞留在潜意识中,所以它能够带着令人动弹不
得的强大力量喷涌而出。在那一刻,你没有活在当下,而是回到了儿时脆弱无力的状态。但你
忘记的是,你已经长大,是成年人了,当你有意识地采取行动时,完全有能力做出有价值的决
策,而且,实属必要的话,你肯定也能够承受他人的不悦。
既然这类内疚是非真实的,不属于“勇敢地承认自己对他人做过的错事”,那么去努力地理解它、
处理它,让自己真正进入成年状态,就是十分必需的了。被这类内疚束缚住,意味着你依然卡
在童年。当我们意识到这种紧张与不安的源头时,那种卡顿状态就不再是无意识的了,也不再
被我们接受。
存在性内疚
最后这种内疚是关于存在主义的;生而为人,这类内疚感是无可避免、与存在相伴相生的。举
个例子,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死是生的基础。这不仅是说,生与死就像宇宙之心的收缩与舒
张,它也意味着,一切生命都建筑在杀戮之上。我们杀掉动物来维生;如果我们选择当个素食
主义者,我们也收割了植物的生命;如果我们停止进食,就会杀掉自己。出于这个原因,我们
的祖先在进食时会敬谢上天的恩典,这不仅是表达感恩之心,也意味着人们明白这个道理:我
们准备吃下去的东西,来自杀戮的行为。出于同样的原因,古老文化中的人们在捕猎前、捕猎
后、进食过程中都会念诵祷词,这是为了承认,他们加入了大母神(the Great Mother)原型的死
亡——重生的循环。
就算无视我们对这种牺牲循环的参与,我们依然要参与市场竞争,为了自己的利益,从别人那
里拿取某些东西。世界某个部分的繁荣发展,或许是以牺牲另一部分的利益为代价的。比如,
经济指数上扬了,但环境可能受到了损害,等等。这个两难的困境是与人类相伴相生的。这一
点在许多宗教传统的神话原型中都有所体现。比如说,在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传统中,亚当
与夏娃的内疚就是无可避免的,也是系统性的。他们吃了智慧树的果子,一旦不再像婴儿般混
沌无知,他们就不得不看到了自己赤身裸体的真相,也知道他们的存活是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
价的,他们在感受能力上存在分歧,以及他们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无论他们多么努力地辩
称自己是无辜的。他们被逐出了伊甸园,这实际上是一种必要的离开:告别幼稚无知,告别婴
儿般的无意识,告别那些不必承担后果的选择。此后,他们被迫承受这个事实:他们的许多选
择将不再是非好即坏的,而是位于各种深深浅浅的道德灰度之中。他们需要承认自身在道德层
面上的模糊性,以及人格与文化方面的表里不一。
再一次,我们想到了阿尔贝·加缪的《堕落》。尽管加缪出生在阿尔及利亚(Algeria),但身为
法国作家,他浸润在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传统中,对于现代人,他想不出比“堕落”二字更强有
力的隐喻了。一方面,现代人见证了大屠杀从自己的文明中诞生出来,另一方面,他们又体验
到了自身的道德滑坡。出于这些必要的认知,一个人从自命不凡的尖塔顶端堕落下来,这一点
毫无疑问;但与此相随的是意识的萌生,而且,在堕入道德泥沼的过程中,人获得了必要的谦
卑之情,此外,心理的容量也增大了,变得更加丰富和广阔。
这样一个收获了谦卑的人,不仅会更加有趣,身上的人性也会更为充分。布莱克 在读
《失乐园》( Paradise Lost )的时候必定看到了这一点。“弥尔顿,”他这样写道,“乃是恶魔一
党,只是他并不晓得。” 就道德上的复杂度来说,撒旦远比没有个性的神主有趣得多。
撒旦是狂妄自大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他的心理实际上与我们的更为相似,他的困境和存在
性内疚因毁灭而变得更加丰富立体。
鲁格·肇嘉(Luigi Zoja)在他的著作《成长与内疚》( Growth and Guilt )中追寻了狂妄自大与
天谴之间的韵律——人类妄取了神的特权,将之据为己有,然后遭受了上天的报应,这报应带
来了谦卑、调整、重获平衡(希腊人将之称作sophrosyne)。肇嘉认为,历史即是人类个体的心
理被投射到更广阔的舞台上之后所呈现出来的东西。自我对安全的需求是至高无上的,比其他
任何东西都重要,但是自我会欺骗自己,会自命不凡,还有着扩张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打算——
无论是把大自然夷为平地,再建一座城市,还是去往其他星球;更有甚者,自我将死亡视作敌
人,还使出“英雄的手段”来对抗它。
自我的这种狂妄自大的天性或许可以叫作“浮士德情结”,这源自歌德笔下的主人公。一方面,由
于心怀无止境的雄心抱负,浮士德是高贵的,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可遏止地想要超越自身能力
的限制,去理解并控制结果。浮士德的后代们塑造出了现代世界——满是奇观,也满是恐怖。
肇嘉认为,对于偏离了自然状态的每一个行为,我们都会背负一份内疚,这种内疚令人不能安
眠,也让现代社会生了病。正如诗人里尔克(Rilke)在20世纪初观察到的那样:“在这个我们创
造出来的世界里,我们却并不自在。” 因此,这前进的步伐——这种说法如此频繁地被
人采用——属于狂妄自大的进步,其代价就是构成了存在性内疚的病态感受。
有时候,出于好意的选择也会造成罪恶的结果,这是避免不了的,因此内疚在现代生活中无处
不在。犹太教与基督教中都有的“罪”(sin)之概念(这个词来源于希伯来语,意思是“没有打
中”,就像箭术里说的一样),与狂妄自大——天谴中蕴含的辩证意味类似。由于缺陷无可避
免,个体不得不一直背负着内疚的重量。要想理解这种hamartia,这种狂妄自大,这种罪过,就
需要人们拓宽意识。知道自己的缺陷无可避免,无意识状态也实属必然,这就是迈向自我接纳
的第一步。
或许存在性内疚是最难承受的。知道自己应该肩负起责任——不仅为了自己做过的某些事,也
为了没做过的某些事——或许会拓宽人性,但也会加深痛苦。在《追踪神祇》一书中,我描述
了诸如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康拉德(Conrad)、加缪这些作家如何描绘现代人的
困境——意识的觉醒令现代人目瞪口呆,他们只能满面羞惭地站在自己选择的世界面前。与内
疚的这种相遇充满了讽刺意味。与人生中的悲剧感和滑稽感不同的是,对这种讽刺的知觉是无
法疗愈的。这种充满讽刺感的意识能够看到选择的缺陷,能理解这些选择的后果,可这种知晓
既没有救赎的力量,也没办法躲开。这样的人只能一直背负着惴惴不安的意识。但就像荣格指
出的那样,因为这个原因,他或她至少不大会继续给社会增加负担。
有多少次,我们不得不面对自己心中的糟糕信念。这倒不是因为,我们由于有神经症或只想着
自己而感到内疚,而是说,我们有神经症或心里只想着自己,并且对此心知肚明,因此我们缺
乏改变自己的勇气或决心。当生命中的创伤阻止或屏蔽了心灵的欲望,心灵是知道的;同样,
当我们心怀对自己的糟糕信念的时候,心灵也是知道的,并且会在某个地方将之记录下来。有
谁不是这样呢?又有谁,在某些深深的地方,不知晓这些呢?而有谁会不再抱持那些糟糕的信
念呢?这就是存在性的内疚,我们逃避不了它,唯有否认它,或是去深入地了解它。
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对于世上存在的那些罪恶,我们无异于同谋共犯,有时我们自己也确实
会做出罪恶的事,考虑到这些,或许自我原谅是最难做到的事。无可避免的是,在人生的前半
程,我们生活在年轻时代那严重的无意识状态中;而痛苦在中年时期到来,其核心是一种必要
的盘点:看清楚我们对别人、对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学着原谅自己,这是至关重要的,也是至
为艰难的。得到原谅的自己会变得轻松自由得多,可以向前走了,同时也拥有了更加清明的意
识,而这能让生命变得更加丰盈。但是,这种对自我的原宥——伴随着真诚的悔过、象征性的
补偿,以及随后而来的解脱——是极为珍稀的。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无法抵达原宥自我的境界,
于是,人生后半程的生命力就被前半程所黏附的结果严重侵蚀。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对
恩典做出了这样的定义:“接受你已被接受的事实,虽然事实上你是不可接受的。” 把这
个定义内化,是多么艰难,又是多么必要的事。这恩典是多么奇异,卸去重担后的灵魂又该是
多么轻松!如此一来,人便可以更加深入地体验这个世界了。
可是,折磨灵魂的存在性内疚还有一种形式。生而为人,为了发展自我,有时候我们必须越过
界限——虽然我们一度认为,那些界限令人望而生畏。每一个孩子,为了长大成年,在某些时
候都必须违逆父母的意愿。没有哪个父母能始终知道,哪些决定适合孩子,因此孩子必须离开
家——这既包括字面意义,也包括比喻意义。在并不那么遥远的过去,如果哪个孩子没跟父母
同住并照顾他们,就会遭到指责,这种情况相当常见。那些确实这样做了的孩子,由于牺牲了
个体化的机会,往往会变得愤懑且抑郁。可是,那些冲破了约束去寻求自由的孩子依然会感到
内疚,就好像自己亏欠了父母似的。他们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自己局限在父母的心理发展水
平上。
同样地,为了成长,有时候人必须打破承诺。很多人由于所谓的内疚感,继续留在极为恶劣的
虐待型关系中,可他们没想明白的是,他们自己也有权利展开独立的人生旅程。有时,一个人
甚至必须成为神话中所说的“神圣罪犯”(Holy Criminal),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违背社会规
范。这类人不得不活出自己的使命,即便要背负结果带来的沉重内疚感。认为战争罪恶而拒绝
服兵役的人就是例证。历史或许会原谅这样的违规者,但社会很少会,个人往往也不会。
由于内疚把我们与过去牢牢捆绑在一起,它也会污染当下和未来,甚至能达到毁灭的程度。若
想带着清醒的意识去处理内疚,我们必须有能力辨别自己承受的内疚是哪一种。真实的内疚是
承担责任的成熟行为。逃避责任不仅属于人格上的退行,它还意味着,一个人永远无法走出未
经整合的体验。我的一位朋友说过:“只会内疚,又有何用?”我猜她的意思是,生命的优质能量
被浪费在过去,而且让人无法对新方向做出切合实际的评估。唯有通过整合,个体才能拥有必
需的意识状态,让新模式得以渐渐铺展开来。
对内疚的成熟整合需要人承认自己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因为补偿往往是象征性而非实质性的,
同时,人也需要有放下的能力。非真实的内疚常常会重复出现,这是一种被高度合理化了的防
御手段,对抗的是某些严重得无法容忍的焦虑。绝大多数情况下,此类焦虑的数量与质量都标
志着它源自一个人童年早期的经历,在那个时候,孩子受到的冲击远远超出他能够理解、评估
和整合的程度。当一个人能驱除掉心底的焦虑,他往往就能重新找回意识状态,也能够看见当
下的自由选择了。
最难承受的,或许也是最无法解决的内疚就是存在性内疚。只要一个人拥有了一定的意识与道
德成熟度,就必然会看到我们徘徊其中的道德灌木丛。我们做出的选择——哪怕是完全不做选
择——难免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波及他人,并有可能造成伤害。这是一张由道德裂痕织成的
网,认识到这张网的存在,就会被模糊的、满是不确定性的人类处境所俘获。想要做到完全不
狂妄自大,彻底远离罪恶,或丝毫没有自欺,同样也是不可能的。当我们越过这些无形的界
限,反作用力也开始运行,终有一天会反噬回来。我们需要深入地思考生命的讽刺意味,像圣
保罗(St.Paul)一样认识到:虽然我们能做正确的事,但我们没做;我们就是自己最强大的敌
人;在我们的行为当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在逃离更为完整的自我,我们因此继续泥足深
陷。
认识到这些,未必能让人卸下重负,但这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由于分清了内疚的性质,人至
少有机会去解开一部分过往对自己的束缚。在这个过程中收回的能量就可以被重新投入更为广
阔的未来。
然而,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艾尔似乎象征着我们自身那坎坷的旅程。她在内疚的星球上徘
徊,希冀能从过往中解脱,也能过得了自己这一关。我衷心希望她终能寻获一位公正之士,卸
下重担。如今,我也背负着她的秘密了。有些时候,我也会感觉到,我的一只手臂拢着一个孩
子,一只手拽着另一个,这个孩子的膝盖磕出了淤青,小手紧紧地抓住我,而她充满恐惧的旅
程永无尽头。
第二章
哀悼、失去与背叛
找回领航的星星
戴文今年三十八岁。他父亲生前是建筑师,哥哥是建筑师,他学的也是建筑,也当过一阵子建
筑师。他从哀悼、失去与背叛中获得了如此丰厚的赐福,以至于寻获了自己的灵魂——他都不
知道自己丢失了它。
戴文的父亲是个好人,但控制欲很强。他是个酗酒的大家长,爱家人,也期待他们以忠诚回
报。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戴文就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以后当个建筑师,住在父母
家附近,对家人忠贞不贰,有求必应。他的哥哥分毫不差地遵从了这些指令,戴文自己也这样
踏上了“第一个成年期”——在这个时期,童年时的体验被内化为一系列对自我和他人的感知,孩
子发展出应对焦虑的反射性策略。
戴文不仅当上了建筑师,还结了婚,成了家,跟父母住在同一个社区,而且如父母所愿,他经
常回去报到。他的母亲是个典型的依赖者,并以这种方式成为系统的共谋。丈夫过世后,她立
即把戴文擢升为自己的情感守护人。
乍一看,戴文的妻子安妮似乎和他的家人很不一样。她是知识分子,是个作家,在政治观点和
生活方式上都是先锋派,但她也酗酒,而且情绪不稳定。三十多岁的时候,她罹患癌症,戴文
尽心尽力地照顾她,直到她过世。接下来的两年里,丧妻之痛让戴文在情感上大受打击。两人
共同生活的那段日子是混乱的、悲剧性的,令两人都伤痕累累,可戴文对妻子极为忠诚,并且
承担起了照顾这个受创家庭的任务——他从小就是这样被培养的。他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在
太多类似的家庭中,孩子中的某一个会被默默地指定为火焰的守护人、替罪羊,以及“伤员”的照
顾者,而这种指定是从父母双方无意识的共谋态度中透露出来的。戴文也默默地接受了提名,
并且很好地承担起了分派给他的任务。
由于心灵变得麻木无感,整个人茫然无措,戴文来做心理治疗。妻子去世后,他无法再像从前
那样到建筑事务所上班,为美好生活绘制蓝图。他不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想拿这辈
子做什么。妻子过世将近两年的时候,就在他开始做心理治疗的同一个时段,他开始约会。他
很多年前就认识丹妮斯,但为了追求安妮而离开了她。这些年里,丹妮斯没有结婚,而是追求
事业,如今在情感和经济上都实现了成熟与独立。当戴文谈起和丹妮斯的新关系时,言语中流
露出对她的爱意,可他深信两人不会有未来。他不知道自己为何这样想,他仰慕丹妮斯,甚至
爱上了她,可他觉得自己没办法再度进入亲密关系了。
很容易就能诊断出,戴文这是反应性抑郁(reactive depression)。可是,自从他妻子离世,这种
情况持续的时间已经超出了一年,并且如此广泛地渗入了他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我猜测抑郁
只是冰山的一角,底下隐藏着更深的、难以名状的不适和不满。戴文抵达了人生中的转折点,
他走上了“中年之路”:一头是虚假的自我,源自被内化了的、对原生家庭的认知;另一头是他本
该成为的那个人。
但凡一个人正在经历虚假自我的解构,一般都会遭受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茫然感,就像在荒野里
徘徊一样。就像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描述的:“在两个世界之间徘徊,一个已经死
亡,而另一个还无力诞生。”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职业生涯、情感关系、人生方向
或欲望可言,因为这个人已经失去了活力,变得随波逐流,也预见不到更新后的自我感是什么
样子。在这个时期,任何事情对戴文来说都毫无意义,因为一切事情的内核都被虚假的自我污
染了。唯有阅读,以及对音乐和大自然的热爱还能在他的灵魂中激起些许涟漪。
随着治疗工作逐渐展开,我们一点点地凿掉不再起作用的旧自我,但此时很容易陷入“试图设计
未来”的误区。这种“未来”都是自我的意识安排出来的,并不是源自人格深处。于是强烈的抵触
就会出现,人的行为会变得慢吞吞的,很像是懒散,甚至是怠惰。实际上,这是对虚假的人生
道路的抵触。或许治疗的关键性转折发生在戴文带丹妮斯一起来的那天。他想向她解释他对她
表面上的抗拒是怎么回事——这种抗拒只会让丹妮斯认为,他在拒绝她这个人。在我们共处的
时段里,丹妮斯无意中提到了自己和戴文母亲的关系。戴文的母亲对她非常和气,可同时又不
放过任何一个贬低儿子的机会。“他真正擅长的事情只有一件,”那位母亲说,“就是把家里收拾
得确实很干净。”
丹妮斯还指出,戴文的兄弟姐妹们是如何在事到临头的最后一刻才给他打电话的——找他帮忙
带孩子、去机场接他们、帮他们修房子等等,而像海军陆战队般永远忠诚的戴文,又是怎样一
次次答应他们的。一个画面浮现出来:一个天资聪颖、有才华的成年男人,依然在很大程度上
受困于原生家庭。他的母亲心里很清楚,知道应该安抚儿子的女朋友,可她也在想方设法地破
坏两人的感情,这样她就可以继续独占儿子了。戴文的手足们也认为他在家庭结构里的角色是
理所当然的,于是就想也不想地占他便宜。
若论是什么令戴文感到如此压抑——虽然压抑感出现在无意识的层面——失去妻子只是其中一
部分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在多年以来他人连续不断的要求与期望之下,他失去了自我。通
过与丹妮斯的交谈,戴文渐渐看到了他的家庭纠缠(enmeshment) 中的剥削本质。随
后,生活的热情开始萌动,他再次看见了欲望的天使。(从词源学上讲,欲望,即desire这个
词,源自拉丁语中的de与sidus,意思是“失去了领航的星星”)。正如塞西尔·戴-刘易斯(C.Day-
Lewis)所写的那样:
带着新的欲望前行吧
因为我们惯常去建造的 去爱的
是一片无人的荒野 唯有鬼魂才能
居住于两团火焰之间
两周后,戴文做了一个梦。
我去光谱中心(Spectrum)听猫王的演唱会。既然要去见猫王,我梳什么发型就特别重要。猫王
正在舞台上唱歌。他非常年轻,正在唱一首我最喜欢的歌。舞台左边有一块大屏幕,后面有个
裸身女人正在洗澡。她走出浴缸,此时猫王和我目光对视,给我使了个会意的眼色。他的眼神
中没有任何下流的意思,相反,她的出现好像给了猫王力量,让他变得完整。她是演出的一部
分,但只有我一个人能看见。
走出体育场的时候,我发现安妮站在那边。她递给我一本“圣经”,但那不是基督教的《圣经》。
安妮说:“她又干这事了。”此时我明白过来,这是她妹妹罗斯在精神分裂期间写画出来的。封皮
上画的是“启示录”。
我问安妮,我要拿这个怎么办,她说,“我希望你把它整理整理,弄得像样点”。我感到非常犹
豫。我爱她,可我不愿接过这本书,因为它代表着我们关系中一切糟糕的东西——来自我们双
方家庭的坏影响,我那“努力厘清每一个人的困惑”的角色,还有我“拯救安妮,让她免受世界和
她自己的伤害”的需要。
我意识到安妮又喝醉了。我意识到,她其实靠从生活中汲取悲伤维生。我告诉她我要和丹妮斯
结婚了,但这不是为了伤害她。然后她说:“人人都觉得咱俩在一起很蠢。”随后她又说:“费城
人队怎么样了?老鹰队呢?”此时我明白过来,我们的生活是愚蠢的、肤浅的。我们花了太多时
间生活在虚假的情感中,从来不曾认真思考过什么对于我们是重要的。我意识到我们永远不可
能再生活在一起了,这令我感到非常难过,可是我会娶丹妮斯,而安妮会继续留在悲伤和孤独
之中,因为对她来说,没有第二条路。
这个梦显示出戴文心灵中那股独立自主的惊人力量正在运作,这力量正在帮助一个活死人寻求
重生。表面上看,失去妻子令他陷入了停滞,实际上,他的心灵在进行深层次的反抗。失去成
为他重新检视生活的催化剂。要想理解这种体验的深度,戴文必须理解,他最大的失去其实是
失去了自己心灵的完整性,他的哀悼与其说是献给妻子,不如说是献给他失去的灵魂。
戴文若想建立起全新的自我感,方法之一就是充分认识到,这个梦就像一个礼物,是他自己的
心灵送来的精彩批注,为的就是帮助他理解过去,把他从中解放出来,让他得以继续前行。
在戴文的梦中,猫王象征着“神力人格”(mana personality)。在充斥着责任的生活中,戴文会唱
的歌没有几首,而这位猫王是一个魅力四射的灵魂歌手。舞台上那个只有戴文能看见的裸女,
象征着对阿尼玛(anima)的大胆认可。在他考虑进入一段新的情感关系之前,他必须把这两种
能量整合在一起:猫王所代表的现象层面的能量,以及阿尼玛的本体能量,即给生命带来活力
的“欲望天使”。
安妮把“圣经”递给戴文的时候,这不仅象征着他年轻时得到的、与责任捆绑在一起的训诫,也象
征着他在妻子家庭中发现的疯狂。安妮的妹妹罗斯曾患过精神分裂症,而戴文是照顾她的主
力。他的任务——在梦中和在现实生活中一样——是为那些不能或不愿自己做事的人把事情整
理清楚,弄得像样点。但在梦境中,戴文看见了之前在意识层面上没有看见的东西,即他不再
属于那个悲哀的世界了——保证其他人的生活正常运转,拯救他们,免于他们受到自己的伤
害。
如今在他看来,安妮不只是他从小就受到训练、要去保护的那种贪婪的人,同时也是肤浅的,
转移注意力的——她把两人深刻的交流带偏了方向,转而讨论起费城人队和老鹰队这些球队
来。带着古希腊悲剧般清晰的视角,戴文看到,他一直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中,那些失去、
束缚、对于被遗留在地下世界的那些东西的哀悼令他感到悲伤,但他也准备投身到一个新世界
去,进入一段崭新的情感关系,拥有崭新的自我感。做了这个梦的两周后,戴文和丹妮斯订婚
了。
唯有巨大的失去才能提供这样的催化剂,帮他看清另外一个埋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进入了无
意识状态的失去——他失去了自己的人生旅程。唯有哀悼,才能激励他终于面对与自我的疏
离。唯有对安妮的背叛,才能引领他看清他的原生家庭中的剥削本质。
戴文栖身在那些阴郁凄凉的沼泽地中,努力处理一个个极其痛苦的创伤,经由这些,他收回了
本该一直属于他的生活——他自己的,不是其他任何人的。走出失去、哀悼与背叛的深海,他
重新找回了他的欲望,他自己的星星。
失去与哀悼
在我们坎坷的人生旅程中,除却存在性焦虑,大概没有哪种体验重复出现的次数比“失去”更多。
我们的人生始于失去。我们与安全的子宫彻底分离,与宇宙的心跳断开联系,被扔进一个不确
定的,而且往往充满了凶险的世界。出生创伤标志着旅程的开始,而这段旅程终结于生命本身
的失去。一路上,我们还会遭逢各种接连不断的失去——失去安全感,失去联结感,失去无意
识状态,失去纯真,渐渐地,我们还会失去朋友,失去体能,失去自我认同的各个阶段。难怪
所有文化中都有与它相关的神话,将失去与断开联结的感受戏剧化地表达出来,比如关于秋天
的各种神话故事、告别想象中的伊甸园状态、黄金时代、与大自然和母亲融为一体的记忆等
等。同样,所有的民族都会表现出对联结感的浓重怀念。
“失去”的主题贯穿于我们的文化之中,从最为多愁善感的歌词(从中我们听到这样的哀叹:由于
爱人不在了,生活都失去了意义),到充满痛苦与渴望的祈祷,祈求与神相联结的神秘体验。
在但丁(Dante)看来,最深重的痛苦就是失去希望,失去救赎,失去天堂,以及被“联结之承
诺”的记忆困扰,无法摆脱,而那个承诺本身已经失落,无处可寻了。在我们的生存境况中,失
去也是一个核心。如果我们活得足够长,就会失去每一个我们关爱的人;如果我们活得没那么
长,他们就会失去我们。正如里尔克所写的那样:“于是我们活着,不断地说告别。” 这
告别的对象是人,也是人存在的状态,还有那不断消逝的时间。在另一段诗句中,里尔克把别
离拟人化了:“别离,把她的手指放在唇边。” 德语中的失去是Verlust,其含义是,经由
欲望去体验,随后,体验的对象消失不见。在欲望之外的,总是失去。
两千五百年前,乔达摩成为佛陀(意思是“觉者”)。他看到,人生是无休止的受苦。这种痛苦主
要是由自我的控制心导致的——想要控制环境,控制他人,甚至控制生死。既然我们无法成功
地控制人生,所以失去得越多,痛苦也就越多。在佛陀看来,穿越并超越痛苦的唯一道路,就
是放下想要控制的心,顺其自然。放手正是神经症的对症解药,因为这样一来,人就不再与自
然割裂开来,其中也包括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这种放弃不会令人沦为失去的奴隶,相反,它让人成为主动放手的参与者。唯有放手,才能带
来安宁与平静。可是,我们都知道,自我的得力干将就是那个名叫“安全感”的警长,还有精明强
干的名叫“控制”的副手。在我们之中,有谁能像佛陀一样成为觉者?有谁能彻底摒弃欲望、超越
自我,笃信“勿按我的意愿,而是你的意愿”(not my will but Thine)?丁尼生(Tennyson)告诉
我们,爱过又失去,胜过根本没有爱过。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遇刺后的第二天,他的
亲信肯尼·奥唐奈(Kenny O’Donnell)在广播节目中说:“如果你不晓得这世界迟早会令你心碎,
身为爱尔兰人又有何用?”
虽然有佛陀的智慧箴言在前,但渴盼依恋、向往家园仿佛是我们的天性。心向往的是永久与联
结,而头脑能接受分离和失去,在这两者的冲突之间,有个地方可供我们找到心理上的空间。
我们大概没人能达到佛陀的境界,可也用不着当个永远的受害者。
若要拓宽意识,其核心是要承认人生的常态就是无常。确实,变幻无常正是生命力量本身的一
种表达。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这样阐释这个矛盾:“那经由绿色茎秆催放花朵之力是毁
灭我的力量。” 那股能量引燃了大自然的能量,就像炸药的引信一样,它会燃烧自己,
终至耗尽。这般的幻灭即是生命本身。“不变”的别名是“死亡”。因此,要拥抱生命,就需要我们
拥抱那股燃烧自己、终至耗尽的能量。不肯改变,即是与生命力对立,也就意味着死亡。
这就是为什么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总结说,“死亡是美丽之母” ,出于同
样原因,死亡是大自然最伟大的发明。伴随着对那股会耗尽自身力量的体验,我们得到了意识
的能力、有意义的选择,以及对美的赞颂。其中蕴含着一种智慧,它超越了自我的界限与焦
虑,体现出生与死、依恋与失去的隐秘合一,它们都是同一个伟大循环的组成部分。 这
种智慧与自我的需求对峙,将之从琐屑中提升出来,带入超然之境。
依恋与失去隐秘地合二为一,这一点在里尔克的诗作中被精妙地呈现出来。这首诗的名字十分
恰当——“秋”。我们这些生活在北半球的人都明白,这个季节意味着夏日的消逝,凛冬的到来。
这首诗是这样结尾的:
我们所有人都在坠落 看这只手 也在坠落
再看看其他人 众人皆同
但有一位 用双手
无限温柔地 将这坠落捧住
里尔克将落叶的意象扩展出去,引申出地球在时空中坠落,进而带出普遍意义上的失去与坠落
的体验。他透露出,有一个隐秘的统一体在坠落底部托住了它。这是不是上帝,里尔克没有明
说;在依恋与失去的伟大循环中,他获得了满足。二者看似迥然相异,但不知何故,又是一体
的两面。
唯有当有价值的事物确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过,失去的体验才会真切。如果我们不曾感觉到
失去,那说明它对我们没多大价值。想要承受住失去,我们就必须承认失去之物的价值。弗洛
伊德写过一篇名为“哀伤与忧郁”(Mourning and Melancholy)的文章,他观察到,丧父或丧母的
孩子能够哀悼这份失去,并因此释放出部分能量,而有些孩子的父母明明在身边,在情感上却
是缺席的,这样的孩子没办法哀悼,因为父母并没有真正离去。这种受挫的哀悼随后会被内化
成为哀伤,即因为失去而感到的悲哀,以及对重新联结的渴望;联结感对孩子的价值越大,渴
望就越是强烈。因此,唯有当有价值的事物曾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才会体验到失去。
在这种痛苦的泥沼中,我们的任务是认清被赐予的价值,并且好好珍惜它——即便我们无法掌
握住那个将之赐予我们的力量。
当我们失去深爱的人,就需要哀悼这份失去,但也要有意识地珍惜我们从这个人身上内化而来
的东西。例如,受空巢综合征折磨的父母,他们痛苦的主因不是孩子不在身边了,而是失去了
为人父母的身份。曾经投注到那个角色里的能量,如今可以投注到另一个方向去,因此,对于
失去的人,尊重他们的最佳方式,就是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什么价值,然后
铭记这份价值,并将它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面对无可避免的失去,这就是恰当的转换方式。
这种转换不是否认,而是转化。被内化的东西永不会失去。即便在失去之后,也还有某种灵魂
层面的东西留下。
英文中的“哀悼”(grief)源自拉丁语的gravis,意思是“承受”,从这个词中还衍生出了“重力”
(gravity)。体验哀悼,不只是承受住当前境况的重负,同时也是再次见证灵魂的深度。我们只
会哀悼有价值的事物。当然,哀悼中最深重的痛苦之一,就是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那种感觉
提醒我们,在人生中我们能掌控的东西是多么微乎其微。就像古罗马的西塞罗(Cicero)观察到
的,“哀悼时撕扯头发真是蠢,就好像秃头能减轻悲伤似的” 。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会
同情希腊人左巴 ,失去儿子之后,他跳舞跳了一整夜——这行为让他的村庄蒙羞——因
为他只能通过肢体来表达失去的哀恸。就像人类其他的主要情感一样,哀悼拒绝言语,拒绝被
钉住和分析。
可以说,对哀悼描写得最深刻的诗句来自19世纪的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诗的名字叫作“大戟”(The Woodspurge) 。“哀悼”二字在全诗中仅出现过一
次,而且是在最后一节。但读者能充分感受到作者的迷茫无着,以及那痛彻心扉的、失去联结
的感觉。他所能做的,似乎只剩下详尽地描摹大戟花朵的复杂精妙。哀悼的重量实在太过沉
重,超出了他能理解的范围,因此他只能把心思放在大自然有限的细节上。
从至深至纯的哀悼中得到的
未必有智慧 甚至未必有记忆
我只知道
大戟开着花儿 三朵一簇 生在一起
罗塞蒂深知,巨大的失去是多么不可碰触,因此,就像里尔克运用了秋天落叶的比喻一样,他
借用可知的、有限的细节,去暗示无边无际的痛楚。再一次,从哀悼的诚挚情感中,人们了解
到曾拥有的事物是多么珍贵。在犹太人的信仰中,在人逝去满一周年的纪念日,要把墓石“揭
开”,这里面的涵义是双重的:既象征着失去之沉重,也提醒人们,哀悼期结束了,生活该更新
了。
无论多么强力的否认,也不能令我们免于失去。我们也不该犹豫,应该立即进入哀悼。在心所
承受的折磨和头脑的疯狂运转之间,我们有机会接受“万物转瞬即逝”的事实,也认识到我们挽留
的力量是多么微薄,然而,这也是我们确证“曾经拥有”的机会——即便时间短暂。在阿齐博尔德
·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根据约伯的故事创作的诗剧《J.B.》中,J.B.谈起上帝,“他不
必去爱,他就是爱”。“可我们要去爱啊。”妻子莎拉说。“这便是奇迹。” 在失去中确证
我们曾经拥有的价值,这种力量即是深刻意义的源头。持守这份意义,同时放下掌控,这就是
我们面对失去和哀悼时要完成的双重任务。
荣格在妻子艾玛过世后,患上了反应性抑郁症。一连数月,他陷入了凄凉和迷茫。有天晚上,
他梦见自己孤身走进一座剧院。他下到第一排,等待着。乐池如同一片深渊,横亘在他眼前。
大幕拉开,他看见艾玛站在那儿,穿着白裙子,冲他微笑。他明白,死寂被打破了。他俩是在
一起的,无论是厮守还是分开。
在美国执业三年后,我打算回一趟苏黎世(Zürich)的荣格研究所。那是我离开后第一次回去,
我盼望能见到一大批老朋友。我最想见的人是我的督导分析师阿道夫·安曼(Adolph Ammann)
博士。可就在回去之前,我得知了他过世的噩耗。我为失去与断联而哀悼。随后,在1985年11月
4日凌晨3点,我“醒来”,看见安曼博士就在我的卧室里。他用惯常的、温文尔雅的气度向我欠身
致意,微笑着对我说:“再次见到你真好。”当时我有三个念头:“这不是梦——千真万确,他就
在那儿”;然后是,“这肯定是个梦,毫无疑问”;紧接着又是,“这就像是荣格梦见了艾玛。我并
没有失去他,因为他依然在这里,跟我在一起”。于是,这次体验结束在一种深深的宁静与接纳
中。我没有失去亦师亦友的安曼博士,因为他依然在我心里,即便是我写下这些字句的此时此
刻,他也在。
或许,真正真实的、重要的、有分量的人和事,永远不会真的失去。唯有放下控制的妄念,一
个人才能真正地哀悼失去,真正地赞颂价值。
背叛
背叛也是某种形式的失去——失去的是纯真、信任和简单明了的关系。我们每个人都遭遇过背
叛,甚至是在宇宙的层面:自我做出的假设,即暗地里认为自己无所不能的幻想,遭到了沉重
的打击。(尼采指出,当我们发觉自己不是上帝的时候,是多么失望啊。)
在自我的幻想与我们脆弱生命的局限之间存在着落差,这种差距总像是宇宙对我们的某种背
叛,仿佛某种宇宙级别的父母令我们失望了。就像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慧黠诗句
里写的那样:“主啊,请原谅我对你开的小玩笑;而我也会原谅你对我开的巨大玩笑。”
还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悲泣:“我的主啊,我的主啊……你为何离弃我?”
十分自然地,我们渴望得到保护,好躲开这个令人担忧的世界,远离矛盾和不确定。我们将孩
子式的需求——想要能保护自己的父母——投射于漠然的宇宙。孩子对于得到保护和爱的期待
往往会落空。即便是在最有爱的家庭中,那一对孪生式的创伤,即“难以负荷的重压”与“被忽视
或遗弃”,也在所难免。或许最令父母们心寒的莫过于这个认识——我们只是做自己而已,但这
已经伤害了孩子。父母只是凡人,都有局限。于是,每个孩子都会感到自己遭到了父母的背
叛,而有些孩子的感受会更强烈。奥尔多·卡罗德努特这样写道:
我们只会被信任的人欺骗。然而我们还是需要相信。一个因为害怕遭到背叛而不愿心怀信念、
拒绝去爱的人,确实不会受到这些伤害,但谁知道他或她会因此错过什么呢?
孩子感受到的对纯真、信任和信念的“背叛”越强烈,长大后就越有可能不信任这个世界。极为强
烈的背叛体验会导致偏执的妄想,也就是把“失去”的感受广泛地转移到别人身上。我有一位来访
者简要地回忆起母亲离开他的那一天——她此后再也没有回来。虽然他的婚姻很有爱、很忠
诚,可他从来不肯信任妻子,她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还坚持要她做测谎来确证清白。他
在蛛丝马迹中寻找妻子背叛他的证据,因为他认为遭到背叛就是自己的宿命。尽管妻子一再保
证自己的忠诚,最后他还是把她赶走了,并且认为她的离去就是明证:他一直深信不疑的东西
确实是对的,他遭受过一次背叛,而这种事会一次次地重演。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偏执的想法潜伏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因为每个人都受过创伤:被宇宙、
被生存境况、被我们信任的人伤害。
信任与背叛是相互依存的对立面。如果一个人遭遇了背叛——有谁不曾遭遇过呢——要再度信
任别人该有多么困难。情况往往是,如果孩子因父母的忽视或虐待而感受到深重的背叛,日后
他或她会与一个将此背叛重演的人建立关系,这种模式叫作反向形成(reaction formation),或
是“自我实现的预言”;或者,他或她会出于避免再次受伤而完全避开亲密关系。无论采用哪一种
策略,当下的选择都被过往的创伤统治着。就像内疚那一章里的案例一样,主人公依旧被过往
所定义。然而在亲密关系中,深深地投注了信任,亦是埋下了背叛的可能。如果我们不去信任
对方,那就说明我们投入得还不够深,还未到产生亲密感的程度。可是,如果我们不投入到这
种潜伏着风险的程度,那么真挚的亲密感就永无可能出现。可见,信任与背叛这一对矛盾是互
为前提的。没有信任,就没有深度;没有深度,就无所谓真正的背叛。
正如我们在内疚那一章中提到的,背叛是最难原谅的,尤其是有意的背叛。可是,对背叛的原
谅,不仅是对我们自身的背叛能力的含蓄承认,也是将我们从过往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的唯一方
法。有许多人在离婚之后依然心怀怨怼,不能原谅背叛自己的前任,这样的例子我们见得还少
吗?他们成为往事的奴隶,相当于依然留在那段婚姻关系中,并未与背叛自己的人分开。他们
依然被憎恨的酸液侵蚀,任由它定义自己。我也见过另一种已经离婚的人,他们之所以憎恨前
任,不是因为前任做了什么,而是因为该做的没做。
朱莉安是个乖乖女。她找了一个愿意照顾她的男人。尽管她因他的指手画脚而恼火,他也因为
她的需索过度而感到不耐烦,但两人都被这个无意识的合同约束着:他是她的丈夫,也是父
亲,而她则是他满怀挚爱的女儿。这个盟约是在两人二十岁出头时缔结的,当她丈夫日渐成
熟、不愿再遵循它的时候,她勃然大怒。她停留在少女时期,依然任性,没有意识到丈夫的离
去其实是提醒她迈入成年的警钟。他对她的背叛看起来是全方位的、不可原谅的,但实际上背
叛她的是她从未脱离的亲子关系。不用说,她飞快地又找了一个可以让她依赖的男人,旧情节
再度上演,长大成人的邀请函被拒之门外。
背叛往往令人产生一种孤绝的感受。曾经依赖的那个人,寄予期望的那个人,或是曾经心有灵
犀的人,如今变成了嫌疑犯,一个人最底层的假设动摇了。然而,在这个充满了变数的状态
中,人有可能获得成长。我们可以从创伤中学习,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就会在另一个
情境中重复它,或者是与它产生身份认同——有许多陷在过去里的人会认为创伤就等同于自
己。上帝看似“背叛”了约伯,但到最后,约伯对宇宙那散漫随意的前提假设动摇了;他进入到一
个崭新的意识层次,将受到的磨难转化成神的祝福。耶稣感到自己不仅遭到了犹大的背叛,也
遭到了天父的背叛,然而,在各各他(Golgotha),在最后的接纳中,他实现了顿悟的圆满。
当我们遭逢背叛,感到极为愤怒并想要复仇是很自然的。但复仇无法助人拓宽意识,反而会限
制意识,而且不仅如此,它还会把人牢牢束缚在过去。那些被复仇之心裹挟的人,无论他们的
哀恸有多么合情合理,他们依然永远是受害者。他们依然活在当初的背叛中,此后原本属于他
们的光阴都被虚掷了。同样,一个人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否认手段,选择继续留在无意识状
态。这种策略相当于不肯去感受已经在承受的痛苦,这意味着拒绝接受失落的伊甸园所提供的
成长机会,拒绝拓宽意识。
背叛的第三个诱惑是把背叛体验“推而广之”,就像那个被母亲抛弃的男子产生的偏执妄想一样。
母亲离开了他,因此毫无疑问地他重视的所有女性都会这样做。如果放在当时的场景看,这种
妄想也可以理解,但它会渐渐发展成一种愤世嫉俗的念头,把一切人际关系都“污染”掉。把一次
痛苦的背叛体验推而广之,这种思维方式会把人困住,轻则满腹狐疑,不愿投入亲密关系,重
则产生偏执妄想,归罪他人。
背叛能促使我们实现个体化。如果遭到背叛的是我们关于存在主义的天真念头,那么我们将被
迫接纳宇宙那更为深广的智慧,去体会依恋与失去的对立统一;如果遭到背叛的是依赖,那么
我们将被迫看清,在哪些方面我们不愿长大;如果背叛发生在关系中,一个人有意识地背叛了
另一个人,那么我们将被迫忍受痛苦,并接纳对立性的存在:它不仅存在于背叛者身上,也存
在于我们身上。无论是哪种情况,如果我们不躲在后面,不陷在对他人的指责中,我们就会成
长,变得更加复杂、更有意识。卡罗德努特很好地总结了这个两难的困境:
若是把背叛的体验翻译成心理学的术语,那就是,它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人得以经历一种非常
基本的心理过程,即整合矛盾,其中包括在关系中普遍存在的爱恨交织的情感。必须再强调一
遍的是,这种体验不只涉及那个通常来说应该承担罪责的人,也包括那个被背叛的人,后者无
意识地启动了那些导致背叛的事件。
背叛中最难以下咽的苦涩药丸,或许是我们极不情愿地承认(往往是在多年以后),我们自己
亦是导致背叛发生的同谋。如果能够咽下这粒苦药,我们就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阴影。
我们受到召唤,需要认识到一些东西,可我们未必次次都喜欢它们。再一次,如荣格所说:“对
自性的体验总是意味着自我的落败。” 在20世纪的第二个10年,荣格深入探索了自己的
潜意识,在对这段经历的追忆中,他记述道,他不得不反复地对自己说:“这又是一件你不知道
的、关于你自己的事啊。” 但是,借助如此苦涩的药丸,意识得以大幅度地进化。
借由失去、哀悼与背叛的痛苦,我们被拽入泥沼之中,但我们可能由此获得更为广阔的世界
观。比如戴文,他似乎陷在丧妻之痛中,可那段时间的荒废与迷茫已经与他的失去不成比例。
通过修习这段人生功课,他渐渐看到,他失去的还有自己,他也在哀悼自己那未曾真正活过的
人生,因为自从儿时起他就遭逢背叛,生活在其他人的计划里。唯有经历了那两年的痛苦,他
才终能开启自己的旅程。
失去、哀悼与背叛告诉我们的是,不能执着于任何事物,不要认为任何一件事、任何一个人是
理所当然的,以及我们不可能免除痛苦。但与之相伴的是通往意识的邀请函。在无常中保持恒
常的,是个体化的召唤。我们既不是这段旅程的起点,也不是目标;前者早已成为过去,后者
会随着我们的前行而不断后退。我们就是旅程本身。失去、哀悼与背叛不只是我们不情愿涉足
的阴郁之地,若想让意识臻于成熟,它们是不可或缺之物。和那些我们愿意逗留、暂缓歇脚的
地方一样,它们亦是旅程的组成部分。得到与失去的伟大韵律不在我们的掌控范围之内;我们
能够掌控的是自己的态度:哪怕是在最苦涩的失去中,我们也愿意去寻找留存下来的、值得为
之好好活着的东西。
第三章
怀疑与孤独
l(a
le
af
fa
ll
s)
one
l
iness
——爱德华·埃斯特林·卡明斯
无垠空间的寂静
在《思想录》中,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布莱兹·帕斯卡(Blaise Pascal)这样写道:“这无垠空
间的寂静令我心惊。” 有谁不曾在凌晨四点时醒来,感到极度孤独、脆弱与恐惧?有谁
不曾体会过外部与内在那些无垠空间的寂静?有谁不曾在落叶的飘零中感受到时光之易逝,以
及人在世间的孤独,就像爱德华·卡明斯在诗作中如此犀利地指出的那样?或者,像罗伯特·弗罗
斯特所写:
星辰间的空寂 不会令我惊惧
因为那些星辰之上 并无人栖居
在这离家如此近的地方 我却感到孤独
令我惊惧的 是我心中的那片荒芜
面对生活,有谁不曾感到力不从心,期待某种拯救?有谁不曾眼睁睁看着熟悉的东西逐渐消
逝,剩下自己孤身一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匮乏资源?
……就连令人安心的谷仓也渐渐消隐远去
我不禁心生怀疑
内里的勇气是否能随着天明升起
拯救我们于这无助的境地
在每一片灵魂的沼泽地里,都有一项成长任务。正如荣格建议的那样,在每一次治疗中都应该
问,借由神经症,这位来访者在逃避什么任务,因此我们也应该自问,在每一片阴郁的泥沼
中,暗含着什么任务。每种情况都会有所得:获得允许,告别依赖,或是找到勇气,让人即便
脆弱也能敢于站到天地之间,并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都会遇到挑战,促
使我们成长,并带着更强大的意识踏上人生旅程。虽然这样的发展与成长往往会令人心生畏
惧,但它也能让我们自由,为我们的人生带来尊严和意义。
三十岁时,诺曼已经有过两段婚姻了。每一次,他都先用甜言蜜语、翩翩风度、装出来的世故
老练来攻陷对方的心,婚后没多久,当妻子不配合他的需求时,他就会勃然大怒;他控制妻子
的行为和选择,还辱骂对方,渐渐地发展成拳打脚踢。当妻子变得很难“对付”时,诺曼就会离
婚,然后寻找下一个。
第二任妻子想办法把诺曼拉去做了个简短的婚姻治疗。治疗期间,诺曼轮番使出了发火、威胁
和霸凌的招数。他拒绝讨论自己的成长背景,也不肯承认在目前的婚姻不幸中他有可能扮演了
重要的角色。治疗师不得不很快叫停,这是因为,如果有任何一方不愿意“认领”自己的模式和责
任,治疗是走不下去的。
检视诺曼的人生,能看到一个清晰的模式。他渴望与女性建立联结,可一旦对方靠近,他就开
始虐待她。这代表着他既需要对方,同时又害怕对方。心理上这种深深的分裂只可能源自生命
早期的经验,比如与母亲的关系。
诺曼不能忍受的是怀疑,他一定要得到保证才能安心。就像原教旨主义者一样——这样的人如
此害怕模糊不清,以至于必须严格遵循基本原理,他们甚至会打压看法与自己不同的邻居——
诺曼不能冒险向内看,他“临时的”自我感建筑在一个弥天大谎之上,他不敢冒险去怀疑那个谎
言。被母亲虐待的孩子依然需要母亲;与此同时,他也对她又怕又恨。在成长过程中,这个创
伤出现得越早,他的防御手段就越是系统化,把这些感受移情到他人身上的范围就越大,那未
曾痊愈的伤口也越发不可碰触。因此,就像所有有性格障碍的人一样,他会用一辈子的时间来
伤害别人,把这当作一种偿还,却没有能力反思和在心理上负起责任。
可以说,神经症患者(这包括我们绝大多数人)最糟糕的敌人就是自己——遭受内疚和失败感
的折磨,被匮乏感纠缠。造成性格障碍的创伤发生得太早,伤口也太深,以至于个体没有足够
的自我力量与个人素材对话。这些问题引起的情感反应过于强烈,令人无法面对,于是就被推
入了无意识的领域,而且往往会被投射到他人身上。虽然这样的人成年后可能会在社会里位高
权重,但他或她其实永远被困在了童年时期。幼时的创伤定义并指引着每一个决定,并且会继
续精准地破坏人际关系,因为此人过于羸弱,无法容忍怀疑的存在,而怀疑是成长和超越早年
创伤的必要条件。
诺曼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地下泉眼,里面涌动着的创伤与渴望灌溉了他的整个人生。像所有孩子
一样,他向往母亲的关爱,但他母亲辜负了自己的角色,并将这样的女性形象永远注入了诺曼
心中,而且,其中附带的恐惧非常强烈,足以与渴望比肩。因此,他绝望地寻求与“她”的联结,
与此同时又害怕她。人只会攻击自己害怕的东西,而他的恐惧确实相当深重。但这也是他的秘
密,一个必须瞒住自己的秘密。这样的秘密是有毒的,它必然会侵染人际关系,给他人造成伤
害。除非诺曼能够有意识地去承受自我怀疑的痛楚,否则他将会继续被无意识地封印在自己的
历史中。
自我的首要任务是安全感,因此,怀疑是个不受欢迎的访客。幸运的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受到
的创伤不像诺曼那般严重,所以还能够承认怀疑的存在。有时候,我们甚至会被怀疑压倒,被
它弄得不知所措。在德语中,怀疑写作Zweifeln,即“二重性”,这显示出当我们体验到怀疑时感
受到的那种分裂感。如何承认怀疑——这是一切成长的必要条件——同时还能不被它压倒、弄
得手足无措,这绝非一个简单的任务。
自我就像一个心胸狭隘的暴君,执意要声色俱厉地强调自己地位的正当性,这是因为它的城堡
建筑在怀疑的沼泽之上,而强调是一种补偿。丁尼生说过:“相信我,比起对教义的半信半疑,
诚实的怀疑中蕴藏着更坚定的信念。” 威尔逊·米兹纳(Wilson Mizner)也有类似的看
法,“我尊重信念。但令人受教的是怀疑” 。固执的、没能力自省的、无法做自我批评的
立场,是法西斯式的、铁板一块的、停滞不前的。“如果对僵化的看法忠心耿耿,”歌德观察到,
“就永不可能打破锁链,也不会解放人的灵魂。” 僵化的看法有可能是政治或宗教方面的
教条,或者是离日常生活更近的东西,比如我们心中被具体化了的自我感。当然,伴随怀疑而
来的是强烈的焦虑,于是许多防御就会升起,想要对抗这些焦虑。冒险去承受怀疑与不确定,
意味着冒险承受更强烈的焦虑。但是,冒险承受更强烈的焦虑,即是向着更广阔的人格敞开大
门——我们那些僵化死板的观点防御的正是这个。
怀疑有没有好处呢,让即便是神经质的自我也有可能接受?事实上,它的好处很多。
怀疑是改变的必备燃料,让成长得以发生。 没有哪个科学或神学的教条,不蕴含具体化与专
横的种子。同样,心灵号召我们放弃那些看似清晰准确的、能保护我们的东西——这与自我的
渴望相距甚远——正是这些东西令我们陷入昨日的泥潭。问题不在于怀疑,问题在于对改变的
恐惧。任何组织或个人想要成长,就必须面对怀疑的风险。
怀疑是民主不可或缺的要素。 请注意世上的某些力量是多么强大,它们想为“作为本国公民意
味着什么”的问题制定出标准答案,比如作为一个美国人/加拿大人/德国人等等。请注意某些焦
灼的少数派是如何向立法机关、法院和社会部门施压的,他们要求这些机构严格遵守约束性的
价值观,遏制多元化的力量。指出皇帝其实什么都没穿的孩子永不会受到大众喜爱。在私人生
活中也是一样,我们有类型学,有神经质的模式、重复出现的冲动,以及僵化的观点,我们排
除不同的声音,摈弃辩证的思维,拒绝心怀不满的人。
荣格曾经指出,个体化并非来自“高处”,即治理各项事务的、帝王般的自我,而是来自“小人
物”,也就是各种分离出去的能量,它们是内在王国里的农夫。 自我希望把灵魂的宇宙
变成一神论的、独裁式的,但心灵实际上是多神论的、非常民主的,容纳了各种各样分离出去
的能量,也就是情结。想要拓宽自我感,就需要让这些能量与自我展开对话,双方都要开放、
谦卑。唯有当傲慢自我的王位被推翻时,绝大多数人才会真正长大。当围墙碎裂坍塌,新的视
角就有可能产生。因此,怀疑不仅能让辩证思维保持鲜活,并因此保护文化免于陷入具体化与
僵化,还能让人的个性变得更有活力,激励它不断进化、成长。
怀疑是一种激进的信念。 我们对神秘的神秘之处保持信念的唯一方式,就是把“模糊性”悉心保
存好。确定性是真理的敌人。真正有信念的人都是能打破旧习的人,时不时地,他们必须破除
陈规,好把能量释放出来,让它再次流动起来。一切概念,无论是教条还是尚在起作用的信
条,都是外壳——它承载着能量,但也是牢狱。威廉·布莱克在审视伦敦的沉寂时曾这样哀叹:
“头脑锻造出来的、人类的镣铐。” 他指的应该就是这个意思。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个人
而言,禁锢的害处都无处不在。
对于怀疑的价值,现代社会中没人比神学家保罗·蒂利希说得更清楚了。他认为,与其说我们的
信念存在于有意识的信仰中,不如说存在于我们的“终极关怀”中。 因此,他指出,我们
实际上笃信的,可能并不是卫理公会,而是利益至上;不是基督教义,而是神经症;不是英国
国教,而是沉溺与上瘾。但是,只要你心怀敬意地追寻终极真理,怀疑就是不可或缺的必备要
素。由于我们不可能知道终极是什么,所以,在召唤之下,我们需要保持一部分开放的视野,
好让神性的能量重新进入。能被命名的神祇不是真正的神。正是那些从破碎信念的废墟上升起
的、饱含情感的图景,构成了新的神性。这种怀疑是一种谦卑,是人在面对神秘的浩瀚广阔时
体会到的感受。它是一种诚实。它也显示出一个人对待人生旅程的认真程度和重视程度。
为了成长,我们必须承受住怀疑带来的不确定性,或者说,我们关于自身的确定性必须被打
碎。无论是哪种情况,怀疑都是改变与更新的代理人。怀疑将暴虐又狭隘的自我推下王座。诺
曼无法成长为真正的自己,无法停止伤害别人,除非他能够承认他那个有意识的自我所代表的
谎言。他卡在原地,是因为他不能怀疑自己。总之,怀疑会带来模糊性,而这会令人感到焦
虑。但是,为了不断成长,我们必须冒险去承受这种逐渐增强的焦虑感。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
要面对的任务。
孤独地漂流在灵魂的公海上
生命、意识,还有令人生畏的灵魂旅程都始于创伤性的分离。我们原本与宇宙的心跳紧密相
连,在子宫这个温暖湿润的世界中,一切需求都能得到满足,可突然之间,我们被扔到一个在
时空中不停旋转和坠落的冰冷星球上。从此,我们始终未能复原,再也不能充分地重新体验到
神秘参与(participation mystique),即与宇宙融为一体的感觉。如果说,我们将把整个人生都用
来处理这个问题——要么通过某种形式的退行冲动重新找回失去的联结感,要么就是把这个深
层需求升华,去寻找与大自然、他人或神的联结——这说法恐怕也并不夸张。
但这种联结感不可能持续太久,也不可能完整。因此,人感受到了失去联结、在宇宙中孤单无
依的焦虑与痛楚。即便是联结真的发生了,人也会很快再度真切地、痛苦地感受到孤绝。里尔
克在他的诗作《孤独》中做出了形象的描写:尽管“(我们)同眠于一张床上/孤独感随着河水流
淌”。
在童年时代,我们的孤独感多多少少被父母或养育者安抚了。在第一个成年期,父母情结会主
导我们,或是会被我们移情到其他人身上,这些因素也多少缓解了我们的孤独感。可是,即便
是最和谐顺畅的关系,也只能是“接近”最原初的联结而已。因此,到了中年之后,每个人都不得
不面对关系的局限,在一个保护性的社会中社会角色的局限,以及自身否认与移情的力量的局
限。我们无可避免地领悟到,没有人能拯救我们,没有人能保护我们远离死亡,甚至都没有人
能有效地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在人生的后半程,我们不得不放弃的两个最大的幻想是:我们能
够永生不朽,以及在某处有一位“神奇他者”,能够把我们从存在性的孤绝中拯救出来。
身为心理分析师,我发现,一个人能否在治疗中取得进展,也就是说变得成熟起来,直接取决
于以下能力:能否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停止责怪他人或期待他人的拯救,以及能否承认孤
独的痛苦——无论自己在社会角色和人际关系方面做了多少投入。
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这样描述孤独感的普遍性与重要性:
如今,我对人生的坚定看法建筑在这个信念之上:孤独感远非罕见之物……它是人类存在的一
个核心的、无可避免的事实……那些骇人的怀疑、绝望、灵魂中暗黑的困惑,孤独的人对这一
切必定都十分熟悉,因为除了这个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形象之外,他再无其他形象可言……没有
人会支持他、鼓励他、帮助他,没有哪种信仰能抚慰他,而且,除了他自己,没人对他有信
心。而这份信心往往也会离他而去,只留下他颤抖着,满心都是无能的感觉。
比起我们绝大多数人,沃尔夫的观点要阴郁荒凉得多,因为时不时地,我们还能从他人身上得
到一些安慰和归属感。但这种浓烈的孤绝感也化作泉眼,他从中获得了惊人的力量,去和宇宙
再度建立联结。虽然他的创作主题基本上都是流放和孤独,但这么多年来,作品把他和诸多读
者联结在一起。我们确实无法再度回到家园,这是真的,但是,在这个流放的宇宙中,当人们
的道路发生交会,在他者出现的那段时间里,旅程本身就会有家的感觉,这也是真的。这绝非
小事。
克拉克·莫斯塔卡斯(Clark Moustakas)观察到:
孤独是人生的一种状态,是生而为人的一种体验,它令个体得以维持、扩展,并深化人性。
……为了克服或逃避孤独感所做的努力,只会导致自我疏离。当一个人远离了生活的基本真
相,当他成功地躲开并否认了可怕的孤独感,他也就自行封闭了那条意义重大的、自我成长的
道路。
莫斯塔卡斯末尾那句话里的观点非常关键,这是因为,恰恰就是在我们孤身一人、只能靠自己
的时候,我们才不得不去思考这些问题:我们是谁?我们由什么构成?在那个转瞬即逝的时
刻,在对灵魂问题的思索中,我们创造出了最丰富、最深刻的自己。恰恰就是孤独,令我们的
独特光彩得以绽放。
与他人的羁绊越多,我们与他人的差异就越小,个体化程度也就越低;个体化程度越低,我们
就越是无法实现宇宙的宏伟目的——我们被如此神秘地创造出来,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啊!
荣格提出的个体化概念远非自恋之意,事实上,它是对那股伟大力量的谦卑服从——那力量推
动了日月星辰,也推动我们采取行动。每个人都以独特的方式承载着宇宙,借由个体最充分的
发展,宇宙亦取得进步。从定义上看,这就是个体化的意义所在。想要退却,想要寻求他人的
陪伴,想要避开那条通向圆满自我的旅程,不仅是对灵魂犯下罪行,也是对宇宙本身的拒绝。
深度心理学的客体关系学派认为,婴儿对“原始客体”(primal objects)——也就是父母——的体
验,会对日后形成的“自我”与“他者”的概念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此后余生都不可能彻底摆脱。
这种依恋体验,无论是令人窒息的,还是疏离抛弃的,或是居于两者之间,构成了人际关系上
一再重复出现的讯息。这个讯息——孩子极为脆弱、需要依赖他人——被过度地接受、吸收,
对人的行为产生极大影响。因此,在长大后,人很难认为孤独是有价值的,而是把它视作生死
威胁。孤独令人感到忧惧,有时人会借助投射性的愤怒,来激烈地对抗和防御这种感受。正如
莫斯塔卡斯所说:“人对孤独感到焦虑,攻击性往往是这种焦虑感的伪装,并且可能表现为愤世
嫉俗,以及对爱与文化利益的蔑视。”
这么说来,或许理想的父母是这样的:能够为孩子提供支持和保护,同时也能真诚地一再肯定
孩子自身的内在资源。这样一来,在分离的各个阶段,孩子就能感受到内心这些资源所提供的
支持。大自然并没有让我们赤手空拳地踏上这段旅程。里尔克曾写信给一位焦虑的、没有安全
感的青年:
我们被置于生活之中,其中的元素都是与我们最为匹配的……我们没有理由不信任这个世界,
因为它并非与我们对立。如果说世上有恐惧,那也是我们的恐惧;如果说有深渊,那些深渊也
属于我们;如果有危险,我们也必须尽力去爱那些危险。面对困难,我们永远要坚持住,如果
我们能遵循这个指导原则来度过人生,那么,现在看来最为陌生的事物,日后将会变成我们最
亲切、最可靠的体验。
鉴于童年时期的脆弱,以及塑造环境的能力有限,我们无可避免地会高估关系的价值,低估独
处的价值。契诃夫(Chekhov)曾这样挖苦道:“要是你害怕孤独,就别结婚。” 当我们
能独自待着,却不感到孤独的时候,我们就抵达了独处的境界。能够独处的人,在对人生的独
特体验中确实是孤独的,然而这样的人清醒地意识到某种内在的存在,并且可以与之对话。基
于这种对话,个体化的进程得以向前推进。若是拒绝这样的成长机会,那就太不幸了。唯有欣
然赞成这种对话,有意识且持续不断地重视灵魂的自主性和目的性的价值,一个人才能成为个
体。
历史中充满了对孤独的价值的暗示。有两个关于“伟大合一”的神话原型,其中之一就是英雄探险
的神话(另一个是“永恒的回归”,即死亡——重生的循环)。此类探险是社会成长的文化范式。
探险一般分成三个部分:(1)离家,这意味着离开原有的自我概念;(2)通过受苦受难,经
历意识的拓宽;(3)抵达一个新地方,一个新家园,但是到了某个时机,英雄同样也要离开此
地。这个神话范式不仅仅是个人成长的模式,它也是一个文化的视野逐渐拓宽的过程。例如,
在中世纪的圣杯传奇中,人会得到这样的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走进没有道路的森林,因
为走别人走过的路是可耻的。但是,走自己的路,需要的是何等的勇气和智谋,又要承担多大
的风险啊!
诺玛三十九岁,在学校里当老师。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她嫁给了一个不成熟的男人,婚姻很快
就结束了。离婚这么久以来,她每天都陷在深深的痛苦之中,悲悼自己的孤独——虽然她有好
几十段短暂的情缘,还跟另一个不成熟的男人谈过几个月的恋爱。诺玛在以下几种状态中来回
切换:憎恨男人、憎恨自己、狂热投入恋爱,或是因为没在恋爱而想要自杀,在手腕上划出不
少浅浅的伤口。在诺玛看来,她的人生就像是一个铁轮,她被邪恶的命运绑缚在上面,无可避
免地在孤单和沮丧中反复轮转。
有一天来做治疗时她迟到了。她看上去生机勃勃,精力充沛,脸颊上还染着红晕,好像那个束
缚着她的铁轮子终于松脱了。她急切地汇报说,她刚跟一个最不可能在一起的男人共度了一
天,简直“爽翻天”。当天晚上或次日早上,她会感到更加空虚,但此刻还没到时候。诺玛的爱情
生活——纠正一下,应该说是性生活——是一种无法遏止的上瘾行为。我们都知道,所有的上
瘾行为都是人对焦虑的管理方式,无论当事人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焦虑。无论他想要的是一支
香烟、一杯酒,还是白粉、食物,抑或是另外一个人,联结感暂时抚慰了人人都有的原始创
伤。与他者的融合短暂地取代了孤独感。在那个瞬间,人回到了子宫里,通过脐带与宇宙相
连,但这只是短短一瞬,然后,就像里尔克所说,孤独感又回来了,像大河一样向前奔流。
诺玛的母亲是个极度自恋的人,那个女人会掌掴诺玛,说她拖累了自己。诺玛的父亲软弱又被
动,把一辈子都花在挣钱上——挣到足够的钱,靠买东西来填补生活中的空虚。诺玛唯一体会
到的联结和滋养的感受来自她的保姆。诺玛上大学时,保姆去世了,这给她造成了摧毁性的打
击。她经常去给保姆扫墓,这位故去的守护人时常出现在她的梦里,尤其是在她感到被人抛
弃、最为孤苦无依的时候。
原始创伤最糟糕的后果并不是创伤本身,而是它会扭曲人的自我感,并且造成一种无意识的冲
动,让人在日后的生活中一次次地重演那种关系。诺玛的母亲极度自恋,她犹如一个情感黑
洞,把能量都吸收进去,却不返还一点点光。诺玛的父亲又如此软弱,既不能呵护孩子,也不
能保护她免受妻子的毒害。于是,诺玛对父母的体验塑造了她的孤独,并且在此后每一段恋情
中,她都会再次创造那种孤独。
这些扭曲的关系铸就了诺玛的行为模式。创伤令她的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无意识的、凄凉的宿
命感,影响着她长大成人后的决定。成年人或许能勉强承受住孤独的感觉,可对于孩子来说,
这是摧毁性的。而且,诺玛遭受的创伤是双重的。一方面,她在孩童时期缺乏肯定与支持,这
被她直观地理解为“我没有价值”,并且被当作一个客观陈述而内化了。缺乏价值感导致她日后只
选择两种男人,一种是不能支持她的,比如已经结了婚的,或是自身创伤已经很严重的人,另
一种就是她父亲那个类型,太过软弱,没办法满足她“经常需要得到抚慰和情感支持”的需求。
另一方面,孩童时期在情感上的被遗弃感,导致她在恋爱空窗期时体验到难以负荷的、可怕的
孤独。在这种时期,她要么痛苦地沉溺在暴饮暴食、催吐、吃安非他命之中,要么就像诊疗迟
到的那天,纵情于狂热刺激的性爱冒险。这些上瘾行为就是她对可怕的孤独感做出的反应,童
年时她就非常熟悉那种可怕的感觉了——即便她的父母就在隔壁的房间。
对于诺玛来说,分离体验的痛苦程度甚至超出了出生创伤,也超出了我们这些普通人时常遇到
的、日常生活造成的无数创伤。她的孤独体验既不能支持健康自我的成长,也无法让她承受住
恋爱的分分合合带来的正常变化与不确定性。在她的治疗中,分析师需要为她提供一个保护性
的、滋养的环境,也要让她觉察到自己的投射、移情,以及强迫性的重复。但在表面之下,孤
独的深渊始终潜伏在那里。
正如我们在前文中看到的,诸多人格失调都源自童年时期遭受的严重创伤,这些创伤摧毁了自
我,令人无法拥有温暖的、带有一定风险的、能够彼此敞开的关系。这样的人或许会结婚,或
拥有不少恋爱经历,但在他们内心深处,某些东西被关闭了,导致要么亲密关系被破坏掉,要
么就不可能与他人建立起真正的联结。带有这类创伤的人,获得疗愈(如果可能的话)需要很
多年时间,他们需要不断地重新学习,感受与他人的相处中天然附带的那些可能性。
有人曾问弗洛伊德,在心理治疗中起到疗愈作用的是什么,他给出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答
案:是爱。弗洛伊德所说的爱,需要一个持续不断的、关爱的情境,这是每个孩子都应该得到
的,但极少有人能真正得到,因为父母自身也创伤累累,心中带着恐惧。再强调一遍,正如接
纳孤独是个人成长与创造力产生的先决条件,一个人也必须先建立起对孤独的情绪容纳能力,
然后,亲子关系造成的创伤才有可能得到疗愈。
上天要求我们承担的东西,往往令人感到沉重得无法承担。这就是在这片名为“孤独”的灵魂沼泽
中等待着我们的任务:把不可能承担起来的东西承担起来。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借由穿越沼
泽,我们打破了原始恐惧对我们持续了半生的钳制。如果我们带着成年人的洞察与勇气去穿越
它,跟它交朋友,奇异的是,那暴虐的钳制就会被打破。一个不能承受原始创伤带来的情绪的
人,就只能继续当个受害者。
诺玛的故事很常见,但她的痛苦程度并不会因此减轻。她想知道,为何自己总是没法拥有幸福
的亲密关系,可她没有意识到,正是她自己选错了人,或是亲手破坏掉了每一段感情——她不
切实际的期望和要求把对方赶走了,这恰恰导致了她最害怕的孤独。要意识到在每一段短暂的
恋情中,她都是在重演童年时期与父母的关系,这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非凡的想象力。说到
底,没有任何疗法能帮助她避开那令她害怕、让她逃避的孤独感。一些出于好意的朋友或咨询
师或许会鼓励她寻找“更好的”情感关系,可是,只要她自己依然维持原样,结果就不会有多大区
别。对付恐惧的唯一解药就是去经历它,穿越它。唯有去拥抱孤独,才能推翻它的暴虐统治。
在《抛物线》( Parabola )杂志的一次采访中,萨提殊·库玛(Satish Kumar)讲到他如何学会
在世间独自行走,并因此收获了宁静、友谊和自己的旅程:
当你接纳了身为陌生人的状态,你就不再是个陌生人了……我指的是那种流放者的感觉——感
到身边的一切事物都很奇怪、每一个人都很陌生的那种感觉。一旦我接受这个想法,也就是我
不一定非得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我就感到了一种自由,反而可以去成为它的一部分了。这种
灵魂的释放是个悖论。当我不再抓住这个世界,世界反而成了我的。
“害怕失去世界”的解药,就是放开手。孤独的解药就是去拥抱孤独。就像顺势疗法那样,疗毒的
办法就是吞下一点点毒素。
关系的悖论——我们这些西方人似乎认为关系是一切病症的解药——就是,一个人越是能接纳
分离的感受,越是能与自己相处,就会拥有越好的关系。关系之所以失败,不仅是因为我们将
个人情结代入其中,也是因为我们向关系提出了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向它索取它无法给予的东
西)。在结婚誓言的背后,往往就隐藏着这种无意识的幻想:他者能够解决孤独这个问题。
绝大多数亲密关系都会先顺畅运转一阵子,形成了某种融合的感觉,但也因此限制了双方的成
长,要么就是在不合理的期望之下,关系逐渐凋萎。唯有当一个人能够作为独立的个体进入关
系时,健康的关系才有可能建立起来。里尔克认为,真挚关系的核心是与另一个人分享自己的
独处时光:
我认为,在两个人的情感纽带中,最高级别的任务就是:守护彼此的独处时光。
这是我们所能给予对方的最丰厚的礼物——即便我们认识到,对方也是孤独的。
在恐惧之外,在无垠空间的寂静之外,丰盈的生命旅程正在静静等候。当我试图通过把自己的
生命旅程转嫁给另一个人,从而避开它的时候,当我由于害怕孤独而向孤独屈服的时候,我不
仅违背了我人生的独特意义——实现它正是我此生的召唤,给那个我宣称要去爱的人身上增添
了一副重担,我也因此放弃了自己应当体验到的宇宙的丰盈,也就是生命要求我去显化、去表
达的那份丰盈。唯有在对“我自己”的激进体验中——不是我的父母,不是你,甚至也不是曾经的
我——我才得以体验到生命的富足,这富足往往令人害怕,但它一向使人变得更加充实、丰
盛。
在怀疑与孤独的沼泽地中,蕴含着这样的任务:寻找到健康的怀疑精神——甚至能把伊克西翁
从往事的铁轮上撬下来;活出那既有助于个人成长,又有益于提升一切关系质量的孤
独。荣格清晰地描述了这个神秘的平衡:
孤独对陪伴关系未必是有害的,因为没人能比孤独的人对陪伴更敏感;而唯有当每一个个体都
牢记自己的个体性,不去与别人认同的时候,陪伴关系才会蓬勃绽放。
第四章
抑郁、消沉与绝望
三只乌鸦
苏格兰有一支古老的民谣,叫作“三只乌鸦”。它们饥肠辘辘,知道过不了多久就能找到一个刚刚
倒下的骑士,饱餐一顿。骑士的猎犬已经不再追逐野兔,鹰隼也不再寻找猎物,他的心上人也
已经另觅良人。所以它们很快就可以拿骑士的骨头筑巢,用他的头发垫窝,再拿他的血肉填饱
肚子。
抑郁、消沉、绝望这可怕的“三人组”,好似时常栖落在我们窗外的树上,就像那三只乌鸦一样,
等着我们颓然倒下,成为它们的猎物。这不就是《乌鸦》( The Raven )中纠缠爱伦·坡的那只
灵魂黑鸟吗?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不是把他心中的抑郁称作黑色的野兽吗?性格
阴郁的卡夫卡(Kafka)将抑郁形容为一只“隐秘的乌鸦”的时候,不是还拿自己的名字用作双关
吗? 当这三个家伙潜伏在窗外——不仅是在忧伤黑暗的日子,有时甚至在我们最辉煌、
最光鲜的时刻——有谁不感到瑟瑟发抖呢?
这个“三人组”,这群乌鸦,是十分熟悉的存在。在我们就要入睡之际,它们嘎嘎大叫;它们拍打
着翅膀,掠过我们的视线,提醒我们,在道路尽头的地面上,一个坑洞等在那里。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荷尔蒙会出现波动,白昼时有生物节律,到了晚上,还有被我们称作“睡
眠”的能量的显著退行,这些都是正常的。所以不难预料,我们的情绪也会出现周期性的波动。
若是世上只有欢乐,却没有对立面与之映衬,我们还能想象得出它的滋味吗?然而在现代文化
中,我们就像上了瘾一样,拼命追寻不掺一丝杂质的幸福,从而扭曲了现实。这样的追寻有可
能会沦为邪恶。
当任何一件事——哪怕是好事——摒除了对立面的存在,变成了单方面的,邪恶就会插手。当
我们被美德裹挟,即便是美德,也会沦为邪恶。想想荣格提出的“阴影”概念,即每一处光明都有
与之相对的黑暗面;实际上,荣格还指出,“更多光明意味着更多暗夜”。 想想清教主义
那席卷了其他教堂的道德狂热,还有费城的历史,老话说,贵格会(Quaker)到此地是来做好事
的——看看他们干的好事。
与阴影的相遇会让现实变得更丰富、更有深度,否则它会继续停留在肤浅的状态;在这样的相
遇中,也隐藏着一张通往更广阔的意识的邀请函。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一个抱有孩子气
的幻想、把纯然的幸福当作目标的文化中,抑郁本身就是阴影的显化。
对于阴影,或许最为实用的定义就是:我身上(或我所属的文化中)令我感到不舒服的东西。
因此,抑郁的体验就有如某种道德的失败、宇宙的缺陷,或是一位受到鄙视的、不受欢迎的访
客。情绪的波动是正常的、难免的,它是我们人生旅程之意义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不想与自
己和世界疏离,就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抑郁:无底的深井
“抑郁”二字的含义是需要区分清楚的。正如癌症有许多种,精神分裂有许多种一样,抑郁也有好
几种。它可以细分为“反应性或外源性(reactive or environmental)抑郁”、“内源性
(endogenous)抑郁”、“心因性(intrapsychic)抑郁”。它们经常被混为一谈,一个人也有可能
同时遭受三种抑郁的侵袭。帮助患者厘清目前的抑郁是哪一种(或哪几种),正是治疗师的任
务之一。
当人遭逢失去或感到失望时,反应性抑郁是极为正常的反应。面对婚姻失败、朋友逝去,或是
另外一些重大的失去,如果一个人不曾感受到力比多(libido)的消退,那就很难说他曾经真的
投入外部现实。唯有当反应性抑郁严重干扰了一个人的正常生活,或是它的持续时间已经长得
超出了合理范围,才能称得上是病理性的。
内源性抑郁的根源尚不清楚,但经推测,有可能是生物学层面的原因。典型情况是,此类抑郁
是遗传的,往往能在患者的家族成员中找到先例。不过,早先几代人很难得到准确的诊断。这
类人非常容易自责,认为心头一直压着的重负都是自己的错。旁人也很容易认为他们不正常。
这就好比,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绝大多数人是在平地上走路,而他们每一天都在翻山越岭。
我的一位分析对象认为,只要有正确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她的身体状况和情绪状态必定就会好
起来。为了在上帝和宇宙面前赎罪、重归正途,她努力遵循各式各样的灵性律条,可她依旧抑
郁。最糟的是,她为此怪罪自己,认为这都是因为自己没能达到足够高尚的灵性境界。服用了
新型抗抑郁药物之后,她的状态好多了,她感到自己重新有了精神,也变得乐观了。诸如百忧
解(Prozac)、帕罗西汀(Paxil)、左洛复(Zoloft)、萘法唑酮(Serzone)这样的新型血清素
再摄取抑制剂(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已经显著提升了数百万人的生活质量,否则他们的
身体和心灵还会继续背负极其沉重的负担。
即便识别出了生物学层面的原因,人可能依然得面对生活中那些“正常的”不幸。在我经手的案例
中,最难辨析的就是一位二十八岁、患有癌症的男士。显然,癌症的影响,还有漫长的治疗过
程足以让他产生反应性抑郁,但他在童年时遭受过虐待,无论是否罹患癌症,都有可能产生心
因性抑郁。得知他在患癌前就出现过抑郁症状,而且家族中也有确凿无疑的抑郁遗传模式的时
候,我劝他试试抗抑郁药物。药物疗程的第23天,他醒来后感到轻松多了,他知道自己已经做
好了再次投入生活的准备——与所有正常的不幸共存。
抑郁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口无底的深井,但在荣格看来,心因性抑郁是一口有底的井,只是我
们需要下潜得很深很深才能发现井底。想想“抑郁”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抑——郁,哪些东西被压
抑下去了?是生命的能量、意图和目的。它们被压抑,被阻挠,被否认,被侵犯。虽然压抑的
原因有可能辨析得出,也有可能辨析不出,但我们内心中的某些东西是抑郁的同谋。甚至可以
说,抑郁的数量和质量与被压抑下去的生命力的数量和质量是直接相关的。生命在和生命对
战,而我们就是那不情不愿的宿主。
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成为自身抑郁的中介。试想,我们如何无可避免地将生活的状况内
化于心,尤其是原生家庭的状况。我们条件反射般地编出一套互相交织的,关于我们自己、他
人和人际关系的假设。例如,一个孩子对于爱、安全感和情感支持的早期需求没有被充分满
足,那么他会无可避免地形成一个错误的假设。孩子会感到自己不值得被悉心照料,因为那些
照顾他的人显然认为他不值得。再者,由于早期的照顾者是把孩子与更广阔的世界连接起来的
中间人,那么,早期的关系就会成为日后一切关系的样板。
我们许多人都背负着抑郁的重担,但很多时候从外表上很难看得出来,甚至还有“微笑型抑郁”这
种说法。我们想方设法把日子过好,同时却承担着灵魂中的重负,从不曾感受过轻松的滋味
——轻松也是人生旅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啊。这类抑郁很普遍,往往未经诊断。它会逐渐侵蚀一
个人的生活质量。可是,通过感到自己没有价值,应对不了生活的挑战,我们成了它的同谋。
在这片沼泽中隐含的任务是,我们需要拥有足够强大的意识,能够辨别出“过去我们身上发生了
什么”和“我们现在是谁”之间的区别。“我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是我选择成为的那个人”,
如果一个人说不出这句话,那么在心理层面上,他便无法前进。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他就会明
白,生命早期的匮乏感并不代表孩子内在有问题,而是孩子无法掌控的外在环境导致的。这样
一来,他就能够渐渐运用那些原先被屏蔽在外的生命能量了。
雅各的父母都是专业人士,对他抱有很高的期待,希望他能沿着他们的道路往前走。雅各小的
时候,父母对他非常严格,如果他不是样样第一,就会遭到羞辱和训斥。长大后雅各当了医
生,不过这不是因为他热爱医药专业或治病救人,而是因为这个职业能为他赢得父母的嘉许。
很自然的是,父母的自恋需求依然未经检视,无论雅各做什么,在他们看来都还不够。虽然雅
各是个很能干的医生,也从工作中获得了一定的满足感,但他还是在将近四十岁时陷入了抑
郁。
中年的抑郁相当常见。虚假的自我与天然的自我之间似乎要发生一场必需的、无可避免的冲
撞。虚假的自我源于童年时期,孩子对生活中不可预测的变化做出条件反射式的反应,然后把
它们拼凑在一起;而天然的自我渴望表达自己。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角色冲撞的结果就是神经
症。那些选择继续停留在无意识的状态、察觉不到痛苦中蕴含的任务的人,会继续卡在痛苦
中,或是继续伤害身边的人。
中年时爆发的抑郁暗示着生命力被压抑了。实际上,它有可能发生在任何时候,只要是心灵渴
望被拓宽,或期待发生转变,抑郁就会出现。当“天然的、直觉的自我”与“习得的、反应性的自
我感”之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我们就变成了自己最糟的敌人。这种对天然冲动的破坏会导致抑
郁,无论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出于这个原因,除却情绪的自然波动之外,每个人都会时不时地
体验到抑郁。每次感受到抑郁的时候,人都应该提出那个最根本的问题: 我的抑郁意味着什
么? 无底之井其实是有底的,但我们必须潜到最深处才能看见。就像吉尔伽美什 一
样,我们也需要面对“潜入水底,寻找生命仙草”的挑战。
为了得到温暖和光,植物会弯弯曲曲地生长,孩子也是一样,有时甚至会严重地扭曲自己。从
小到大,雅各一直在扭曲自己,为的是从父母那里得到关爱的能量,但他永远得不到,因为他
们的自恋把能量吞没了,却没有返还任何东西。若是按照天性,或许雅各——还有我们——理
当成为长途车司机、乡村歌手,或者就是闲适度日,可是为了寻找那必需的光线,只能扭曲地
生长。通过梦境与治疗,雅各发现,他当医生并不是为了响应内心的召唤,而主要是为了赢得
父母的嘉许。他在这个选中的领域干得很不错,这证明了他的能力,但同时也证明他灵魂的意
向变形得多么严重。这怎么可能不抑郁呢?幸运的是,雅各拥有潜入抑郁、触探井底的人格力
量。从那里起步,他逐渐开始疗愈自己的灵魂。
另一位男士名叫爱德华,他继承了家族的生意。很多人会认为,这相当于轻松迈入了有权力又
富足的人生,但在他看来,这犹如一个陷阱。他自己的梦想与此大相径庭,但他觉得自己理当
对配偶、家族、员工们负责,命中注定他应该服务于大家的共同利益。他的灵魂渴望去创作音
乐,进入艺术家的世界,但他的职责也很明确。每当他想朝着自己的梦想迈步时,他就会被内
疚压得喘不过气来。在我写作这本书时,爱德华依然承受着内疚与抑郁的重压。他能将职责与
渴望之间的紧张状态维持多久?我相信还会很久,直到“超越功能” 出现,到了那时,他
就会明白自己的路,他的抑郁也会成为历史。
雅各与爱德华的困境让我们深受触动,他们的境遇中存在一个悖论。如果雅各想成为自己,那
就必须放弃当年那个孩子的合理期待——希望父母接受他本来的样子。如果不放下这个期待,
并转而学着爱自己、给自己提供情感支持,那就意味着他还会继续抑郁下去。要走出抑郁,我
们往往需要冒风险——鼓起勇气面对我们最害怕的东西,挪走那些阻碍我们自然生长的东西。
如果爱德华决定追随灵魂的召唤,他很可能会一头扎进焦虑之中,因为这正是他的内疚试图防
御和对抗的,即对孤立感的焦虑——辜负群体的期望会令他孤立。
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艰难的抉择:焦虑还是抑郁。如果我们向前走,就像灵魂坚持想做
的那样,焦虑感可能会席卷我们。如果我们不向前走,就要继续忍受抑郁,也就是继续把灵魂
的使命压抑下去。在这个艰难的抉择面前,我们必须选择焦虑,因为焦虑起码是一条通向潜在
成长的道路,而抑郁是停滞,是被生命打败。
我们也有可能经历普遍性的抑郁。就像许许多多的人曾经遇到、如今也依然在面对的一样,我
们会受困于性别限制、阶层与经济条件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抑郁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人们
会看到整个国家层面上的抑郁(就像我在爱尔兰看到的那样)。如果时代的神话与我们的灵魂
不相符,我们可能会遭受文化层面上的抑郁。如果我们被要求扮演的角色与自己的内在形象不
符,差异往往就会以抑郁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我们却浑然不觉。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身在井
中,就很难去潜入井底了。
荣格学派认为,神经性抑郁症(neurotic depression)是有疗愈意义的。心灵的这种表现代表着服
务于自性的能量出现了退行。这就像我们在夜间的退行,即睡眠,是为了让身体和心灵恢复平
衡,获得疗愈。打个比方,如果我们身上有某个重要的部分失落了,那我们肯定要回去(或潜
入深处)把它找到,带回表面上来,去整合它,把它“活”出来。就像萨满巫师会进入灵性世界,
把分裂的灵魂修复好再带回来,以便重新整合,我们也需要找回落下的东西,把它带回表面。
深度分析师们会密切关注梦境,因为梦不仅来自井底,更来自井底之下那口更深的井。因此,
我们会提倡使用积极想象的技巧,来激活那些被压抑下去的心灵内容。当我们能够把这些素材
表现出来,带入意识中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发现抑郁减轻了。心灵运用抑郁来唤起我们的注
意,告诉我们,有些事情已经很不对头了。一旦我们理解了抑郁的疗愈意义,循着阿里阿德涅
的线团 ,走出自己的迷宫,抑郁甚至可以被我们视作朋友。毕竟,如果我们不曾感觉到
这般刺痛,说明心灵可能早就死掉了。刺痛与痛苦都是讯号,说明那些至关重要的东西还在,
正等待着我们邀请它回到世界中来。
每一片沼泽中都隐藏着任务。我们需要拿出莫大的勇气,去承认抑郁的价值,去尊重它,而不
是试图吃点药把它赶紧治好,或是用其他事物将我们的注意力从痛楚中转移开。在心底深处沉
潜着的,是有待揭示的意义,它们脱离了意识,但依然是鲜活的。尽管抑郁把能量从意识层面
的生活中抢走了,但那些能量并未消失。它们沉在底层世界,就像俄耳甫斯 需要深入地
府,去面对那些黑暗的力量一样(或许还要用魅力打动它们),我们也必须深深潜入抑郁中
去,找到灵魂最珍贵的宝藏。
消沉:无精打采的国度
精神(spirit)与灵魂(soul)的区别是什么?如果说灵魂是生命的目的性,是大自然给予个体的
投资,那么精神就是能量,是力比多,是人生旅程中的厄洛斯 。当我们感到抑郁的时
候,会说自己“无精打采”,也就是失去了继续走下去的能量。正如前文所说,那些能量依然还
在,但已经沉入了井底。消沉就是精力被抽走的感受,我们的能量不足了,没办法继续穿越荒
原。有谁不曾周期性地在倦怠、郁郁寡欢和迷茫这样的干涸地带停留?有时候,我们甚至一待
就是好几年。
从词源上看,desuetude(消沉)这个词的意思是“废弃、不再使用”。把生活必需的心灵能量抽走
的因素可能有无数种:身体上的疾病,即肉身注定要承受的各种自然冲击;疲惫;当然还有情
结的影响——它们把能量从意识层面上吸走。我们观察梦境与症状,为的是找到能量目前停留
在哪儿,它想去哪儿,追随它的流动,这样就可以追踪到丢失的能量。
在中世纪的语言中,每个人都会时不时地陷入怠惰,即精神上的萎靡不振,这也被称作“修道士
的疾病”。从中世纪的生理学视角来看,灵魂是湿润的,如果它变干了,人就会遭受精神干涸的
痛苦,心灵变成一片荒原。大概是修道士们简朴的生活方式,强制性的虔诚,保持清贫、贞洁
和服从的誓言,更不用说还有单调乏味的环境,这些因素导致精神日渐凋萎。这就跟被关进监
狱差不多。正如马克斯·派珀(Max Piper)所言:“怠惰的本质就是一个人拒绝准许自身的存
在。” 无论超我与外界环境的要求是多么合乎规范,放弃自身的独特性,把自我的旅程
牺牲掉,即是在伤害灵魂。附带的结果就是精神凋萎了。
与怠惰类似的体验是倦怠。从长远来看,只要心灵被引导的方向与它的自主渴望相反,或是它
不得不服务于某些与自身渴望相悖的价值观,倦怠就会出现。现代社会的许多工作都是重复性
的,而且被限制在人造的环境中。即便是专业人士,也会被局限在狭窄的职业训练领域,而这
些领域往往很少在乎个人灵魂的价值与多样性。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一个人的外在成就越
大,从社会中得到的回报越多,就越有可能被这种成功钳制,成为日益增多的期望与义务的囚
徒。这样的成功会将灵魂紧紧束缚住。倦怠是个最不受欢迎的访客,当我们对工作的热情逐渐
消退,欲望开始消沉的时候,它就会频繁造访。查尔斯·凯莱布·科尔顿(Charles Caleb Colton)
观察到:“倦怠造就的赌徒多过贪婪造就的,造就的酒鬼多过干渴造就的,而它造成的自杀可能
跟绝望造成的不相上下。”
我们这个时代仿佛有种神话:我们的“产出”应当越来越多,还要越来越快,而我们是什么样的
人,主要取决于那些可见的产出。当今时代,没有一种羞耻感——无论是性丑闻、财务危机,
还是在品位上闹了笑话——能比得过“感到自己不够高产”。我们不得不重复自己,就像戏路被定
了型的著名演员一样,迫于公众的期望,只能反复扮演同一类角色。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可
是,正如作家让·保罗·里克特(Jean Paul Richter)说的,“一心求快,反倒愈慢”。
在我们的先祖看来,时间就像一条宽阔的柱廊,人们可以从容地探索各个角落,而在我们看
来,时间总是不够用,该做的事情总是做不完。出于对成功的狂热追捧,对满足期待的强迫性
渴望,我们遭遇了倦怠的折磨,以及名为“消沉”的灵魂的衰弱无力。
就像其他沼泽地一样,这里也有一个心理层面的任务出现。生命赐予我们的能量足够走完这趟
旅程。应该承认的是,其中有不少确实需要用于维持生存,但是,遭受消沉的折磨时,我们必
须明白,这说明我们违逆了自己的心愿。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工业化国家里的人来说,生活或
许比我们设想得简单。心灵有两种自主行为:情绪功能,能量之流。这一对孪生的资源是永不
会出错的生活指南。任何一个孩子、任何一个农人都自然地知道这一点,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
忘记了。
情绪功能告诉我们一件事是否“对劲”。不幸的是,我们太多人早已与这项资源失去了联结,有时
甚至会为了高产而故意不听它的指引。我们无法选择情绪,情绪犹如自主生成的、对生活的定
性分析。我们能做的选择只有一个:把情绪带入意识中来,然后决定要不要依据它们采取行
动。同样,能量的潮起潮落虽然是人体的自然功能,却也是至关重要的指引,告诉我们某个选
择对不对、是否适合我们。如果我们在做的事是对的,能量就会有。但我们经常不得不把情绪
和能量引流到毫无灵魂可言的任务上去。我们学会了这样做,是因为从中能得到报偿,而且如
果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会感到耻辱。
然而,在消沉中,在了无生气的状态中(我们自己正是造成这种状态的同谋),一项名叫“意识”
的任务正在轻轻振动。荣格的提问一直在我们耳边回响——这个人在回避什么?在绝大多数情
况下,我们在回避“为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在童年时期,我们发觉自己没有力量,我们记住了
这一点——往往记得过于牢固;我们把权威人物和社会规范内化到心里,长大后,身为一只成
年的工蚁,我们就像奴隶一样为它们服务。若要违逆它们,我们会感到“非真实的内疚”与焦虑。
可是,消沉这种体验,也就是不再运用能量为灵魂服务,让我们与真实的自我渐行渐远。
唯有诚实地观察能量是如何失去的,我们才能追踪到断裂发生的位置。失去的能量是可以找回
来的。如果我们选择为灵魂服务,能量就会回来,并服务于我们。听从内心的召唤,活出真正
想要的生活——做出这个选择,同时应对生活中所有的迫切要求、实现对他人的承诺,这些责
任始终都是我们自己的。消沉是灵魂提出的抗议,它把能量从我们这里撤走,因为它不赞成自
我运用这些能量的方式。我们可以无视无意识发出的如此强有力的宣言,但接下来就等着看症
状加剧吧。灵魂是蒙骗不住的。那不满的隆隆声虽然令人不快,实际上却是一种友好的警告,
提醒我们需要做出改变。当我们作出响应,能量就会回来了。
绝望:最黑的乌鸦
绝望就是没有希望,没有可能性,没有选择。在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传统中,绝望是一种罪,因
为它是对上帝旨意的违逆,它为无限加上了限制,制约了造物主的神力。从许多方面来看,绝
望都可以说是忧郁状态中最糟的,因为它似乎毫无出路。绝望甚至阻碍了雪莱(Shelley)那充
满英雄气概的反抗,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中,他曾发出这样的指令:我们应“始
终心怀希望/直至希望从绝望中/创造出它心之向往”。同样,曾任英国首相的本杰明·迪斯雷利
(Benjamin Disraeli)显然深知失败、偏见与失去的滋味,他曾说过:“绝望是蠢材得出的结
论。”
可是,我们有谁不曾品尝过绝望的滋味?外在与内在的力量携起手来对付我们,它们比我们那
微末的力量强大太多,别说打败它们,即便是与之对抗都很艰难。有谁不曾动过认输的念头,
甚至恨不得一死了之,好终结那痛苦难耐的紧张,那因混沌带来的折磨?有谁不曾像旅鼠一
样,盲目地奔逃进“绝望”的血盆大口中,因为已知的恐惧总好过想象出来的恐惧?加缪在《西西
弗斯神话》( The Myth of Sisyphus) 中指出,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生存还
是毁灭——那才是问题。如果我们拥抱了绝望,决定自杀,也算是做出了选择,可是,我们选
择的这条路通向的不是生机。努力活着,拥抱绝望,接受对立两极的痛苦撕扯,这至少保留下
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向前走的可能性。
在《自杀与灵魂》( Suicide and Soul )一书中,詹姆斯·希尔曼(James Hillman)提出,即便在
绝望的时刻,当一个人想去死的时候,他真正想要的并不是死,而是立即发生彻底转变。最黑
的乌鸦在我们耳边低声提议,说这个决定性的行为会解决问题,但实际上它带来的只有永远的
止息。希尔曼说,如果一个人能够接纳“彻底转变”的含蓄愿望,就有可能催动改变发生,否则,
人不会从那个决定性行为所带来的有益想法中获得好处。
然而说说是容易的,在绝望所代表的修辞怪圈中,任何争辩都会被“毫无希望”给快速驳回。任何
解决办法都像是稻草人,被“不可解决”的逻辑轻松掀翻。绝望背后的逻辑是来回重复的,它把尚
未被证实的事当作论证的前提,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在这个毫无希望的循环中,几乎看不到
出口。
在我能想到的关于绝望的深思中,无人能与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在
1885年写下的《腐朽的慰藉》(Carrion Comfort)比肩。霍普金斯是一位耶稣会士,他个人的痛
苦与他每日履行的神职息息相关。他写作,是因为必须写,是因为他需要向自己忏悔,因为他
需要一个空间,来做他的灵魂沼泽地的功课。他在美学上的敏锐细腻,对语言和概念的娴熟运
用,以及独特的写作风格,都令他成为现代文学真正的先驱,可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只有寥
寥几人读到他的诗作,感受到他的挣扎。他的几篇诗作,包括这首《腐朽的慰藉》,如今被人
们称作“阴郁十四行”(the terrible sonnets),因为这些诗句描摹出一个处于危难中的灵魂感受到
的恐惧。
不,我不要,绝望啊,你这腐朽的慰藉,我不要享用你的盛筵
我不要解开心中最后这几根维系的绳索 就算它们已经快要松脱
疲惫至极的我 不再哀叹“我再也不能”我能
能做点什么 我能期待 盼望白日到来 不选择死去
可是啊 你这可怕的力量啊 你为何待我如此粗暴
用撼世的右足将我践踏?用狮子般的利爪将我扫划?
用吞噬一切的黑眼睛 扫描我伤痕累累的筋骨
你掀起暴风骤雨 我已匍匐在地 惶然 狂乱 避之不及
为什么啊?是要让我的稻壳纷飞飘散 好露出莹润剔透的谷粒
在那番挣扎之中 纠结之中 自从(似乎是)我亲吻了权杖
应该说是执杖之手 看啊 我的心 积攒起力量 也将欢欣品尝 我想大笑 想欢呼
可为谁欢呼呢?为那位将我猛推重踏的英雄?
还是为了与他对战的我自己?哦,为了哪一个?还是说,我们两个都值得?
那一夜 那一年
那如今已经止息的黑暗 可怜的我 与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苦苦对战
在霍普金斯运用跳韵 表现出的力度与炽热情感中,读者能够感受到他内心争斗的力量与
诚挚,而且,胜利的战果来得实在艰难,这样的争斗若是多来几次,人很难经受得住。
请注意看,绝望那迂回式的逻辑甚至把说明性的句子都变成了一连串的否定:“不,我不要……
不要……不要……”读者能感受到,他差一点就要彻底放弃信念,差一点就失去了人性,然而他
还是找到了力量,加入最后的战斗。我们能看出,他要对抗的东西远比“令人畏惧”更强大。那个
与他的灵魂对战的“存在”,被直观地称为“你这可怕的力量啊”,它具备能将世界撼动的力量,它
震慑他,重重地压住他,那犀利的眼光就像在扫描他一样,看穿他灵魂的最深处。谁能在这种
遭遇战中幸存下来?谁不想逃入绝望的甜蜜之中,尽情享用那腐朽的盛筵,那灵魂战死后的残
躯?
霍普金斯感到,即便在他宣誓服从、亲吻过圣物之后,绝望还是有增无减。然而,他内在的某
个地方凭直觉知道,他的灵魂正在摸索出路,正在痛苦中穿越某个辽阔的平原,某个如灵魂般
浩瀚无垠的风景。凭着直觉,霍普金斯知道,在自己的内心中,是神的反对者与拥护者在对
战。他的冲突,他的争斗,发生在一个超越凡俗的平原上。他与上帝,即那位掌管天国的英雄
对战,然而,在这场令人生畏的与神的遭遇战中,他承受住了绝望的冲突,没有屈服,而且他
似乎和约伯一样,得到了祝福。那是“我的上帝!”,即他的上帝,赐予他丰厚的祝福——那广阔
得令人生畏的人生旅程。
用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的话说,世上没有“轻易得来的恩典”。 如
果幸存下来,你会得到祝福,可有谁愿意赶赴这种战场?正如霍普金斯在另一首“阴郁十四行”中
提醒的那样:
念头啊,念头中有高山峻岭 悬崖绝壁
骇人 陡峭 崖底有多深 无人知晓
从不曾临渊而立的人 会将这危崖小觑
从灵魂的骚动中,从发自肺腑的绝望中,霍普金斯绞尽脑汁,追寻意义。他领悟到了,进而确
认了,这一切痛苦,是因为他被选中,去面对生命“存在”的深度。在他的冲突中,在几近溃败的
危险时刻,我们发觉他勉力留住了尊严,而这尊严拯救了他。给他带来胜利的,是这场争斗的
性质,远非其结果。我们能联想到凯尔特神话中的库丘林(Cuchulain) 那充满英雄气
概的绝望,他远涉重洋,在侵染了绝望的希望中挥舞着长剑。我们能感受到,他们渴望倒在绝
望的沙场之上,在这样的战役中,英雄们配享“英烈”的荣耀。对于丁尼生对那位暮年的远游者的
描写,就算头脑不认同,心灵也会:
死亡终结一切 但在这之前
还有一番高贵的事业可干
这方才配得上是 与神争斗的人
在这充满英雄气概的冲动中,人走出了受害者心态。且不论结果如何,不论解决办法与成败,
人感知到了争斗本身包含的救赎价值。埃斯库罗斯与雪莱笔下的普罗米修斯,遭到心怀报复的
宙斯的绑缚,但他是自由的,在这伟大的自由面前,神力无边的宙斯颤抖了。加缪笔下的西西
弗斯,同样受到神之惩罚的绑缚:他一次次地将巨石推到山上,然后只能看着它一次次地滚
落,永无休止。但西西弗斯比欺压他的诸神更自由。他选择了推动巨石,而不是屈服于推石头
的命运,由此,他将力量从诸神手中夺过,并留住了自己的尊严。在灵魂的这种行为中,人得
到的是悲壮(tragic)。与生命的悲壮感对立的是感伤(pathos),从中衍生出pathetic这个词,
意思是“可怜、弱小、无助”。悲剧,以及那无可避免的战败结尾,是带着英雄气概去主动拥抱生
命中的冲突。被动的受苦受难则是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上,是可怜的、羸弱的。
在与绝望的遭遇战中隐含着这样的任务:尽力斗争下去,不当受害者,而是选择成为英雄;拒
绝可怜,选择悲壮。当然,人生都会以死亡而告终,这可以视作一种战败,但也可以视作是天
地或神祇的智慧,它将自我那微薄的力量升华为理解与领悟。而绝望中蕴含的任务不是去否认
那些可怕的感受,也不是被迫放弃身为人类的那为数不多的尊严,而是努力承受住痛苦,朝着
绝望那冗赘的逻辑怪圈之外走去——无论在圈外等待我们的是什么。
这些可怕的乌鸦——抑郁、消沉与绝望——会一直栖息在我们的窗外。无论我们如何有意识地
努力赶走它们,它们总会回来,一次又一次,那粗嗄的叫声扰乱了名为“否认”的清梦。就把它们
看作某种提醒吧,不断提醒我们记得自己的任务。即便是在嘎嘎的叫声中,在那些讨厌的身影
中,我们依然可以做出选择。
第五章
强迫与上瘾
地狱一季
是什么让地狱成为阴森恐怖的象征,或者说,为何会有地狱这个概念?它是怎么出现的?我们
何曾停止过对这些问题的思索!但丁所写的“深入幽冥之国”指的是什么?《失乐园》呢?诗人兰
波(Rimbaud)的《地狱一季》( Une Saison d’Enfer )呢?等我们到了中年,如果我们还算有
点自省能力的话,有个想法必定出现过:“人生中唯一的常量就是我们自己。”无论我们多么希望
把遇到的问题归咎于父母、社会或伴侣,我们总会不停地和自己相遇。
我在苏黎世荣格研究所(Jung Institute)的中年体验就十分典型。我很自然地以为,这个课程肯
定和其他研究生项目差不多,对我来说不在话下。可是,这段经历更像是一桩禅宗公案。我就
是问题,我就是根源,此前形成的自我如今变成了障碍。“非我”或许才是唯一的答案。自我希望
保住自己的地位,捍卫自己的假设,这很自然。可是,必须拆掉的恰恰是自我。就像俗话说
的,无论去哪里,我就在那里。或者,像弥尔顿观察到的:
我真可悲!我该飞往哪里,才能躲过
这无尽的愤怒,无尽的绝望?
无论我飞向哪里,都身在地狱;我自己就是地狱。
或者是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在《浮士德博士的悲剧》( The Tragical History
of Dr.Faustus )中写到的:“什么话!这里就是地狱,我并没有离开。” 以及:
地狱没有边界,也并非处于一个固定的地方
我们所在之处即是地狱
哪里是地狱,我们就会永远待在哪里
地狱最恐怖的一点就是没有尽头。无论是什么样的苦难,只要有尽头,我们就能够忍受。如地
狱般恐怖,即是毫无希望,永无休止,也无从解脱。卡在原地,即是身在地狱。在但丁的想象
中,地狱是如同螺旋下降般不断加深的道德堕落。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的道德堕落的后
果就是,一个人卡在自己的选择所延伸出的象征中,不得解脱。
比如,阿谀者们谄媚了一辈子,因此整个人都被浸在粪溺坑中,污秽一直淹至下巴。不由自主
地,他们会永远保持这种个性,因此今后他们还是会满口粪汤。享乐主义者呢?命中注定他们
要一遍遍地推动巨石,永无休止。贪食者的命运也是注定了的,因为他们误解了何为真正的饱
足,不知道真正的灵魂食物是什么。在地狱最深处的那一圈,叛徒们被冻结在冰里,心中的冰
冷是对他们永久的惩罚。
总之,但丁的观点是,我们会继续保持从前的样子,更有甚者,我们会一直卡在这种状态中。
这话听上去有点熟悉了吧,因为有谁不是越来越像“自己已有的模样”,觉得自己就像命中注定一
般,永远无法摆脱那些重复出现的强迫行为?这里就是地狱,我们自己即是地狱。
强迫思维:不请自来的念头
强迫思维,指的就是一个想法侵入了意识,而它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取代意志。这种对意识的篡
夺自然会令我们感到焦虑,因此我们会立即做出某些条件反射式的行为,想去安抚这个不请自
来的念头引发的紧张感。我们每个人都会产生强迫想法,也都会随之做出强迫行为。
有时候,我们对这些强迫思维——强迫行为的戏码是有意识的,有时候则没有。有时,我们会
发展出一些以魔法思维为基础的个人仪式,为的是降低自己的焦虑程度;我们经常做出眨眼、
绞扭手指之类的动作,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一般来说,这些行为对意识的干扰不
大,我们也就容忍了。但有时候它们会控制我们,严重妨碍我们的生活。
罗杰是个三十五岁的男人,从事电台广告销售工作。他婚姻幸福,有两个女儿。由于他的工作
性质,他需要天天在路上奔波。只要看到一个漂亮女人,或是想到一个,甚至是听到相关的歌
曲,他就非得找个付费电话打给太太不可,好把这些颇为寻常的念头告诉她。起初,他太太感
到很好笑,随后她开始觉得不对劲,直到她被这频繁的打扰惹急了。她坚持要他去做心理治
疗,把问题解决掉。
这种不请自来的念头影响的范围越广,其根源出现的时期必定就越早,处理起来也越是棘手。
罗杰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了,是母亲把他带大的。她是个虔诚的清教徒,把他的童年管束得死死
的。在强悍母亲的训导之下,在罗杰看来,任何关于身体、性欲,甚至只是关于女人的想法,
都是污秽的。他的天性与后天得到的教化之间出现了深深的裂痕,但凡想到与性有关的事,他
就会感到内疚,这种内疚一层层地累积起来,加之他念的又是教会学校,导致裂痕变得越来越
大。多年后,只要罗杰看到有魅力的女人,或是有了性幻想,这道裂痕就会被激活。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看到,内疚往往是对抗焦虑的防御手段。那些想法都再正常不过,但罗杰被
内疚压得喘不过气来,为了减轻压力,他会立即做出这样的强迫行为:向妻子坦白,就好像她
是个严厉的修女,或是满腹狐疑的母亲。他这是在重演童年时期的恐惧,把妻子当成了母亲
——对罗杰来说,仅仅是承认这一点都颇为困难。这个裂痕如此之深,以至于强迫性的想法和
随之而来的内疚都根植在心里,很难撼动。虽然他没办法单凭意识的力量把旧想法连根拔除,
但他确实想办法改变了自己的行为,他把忏悔都写下来交给了分析师,不再烦扰太太。
乔治心中的创伤也很严重。他记得九岁那年,他亲眼看着母亲走出家门,上了陌生人的车子,
面无表情地回望了他一眼,然后再也没有回来。多年后,他结了婚,却坚持认为妻子也会离开
他。他跟着她,想控制她的生活,在脑海中幻想她与其他男人在一起。周年纪念日的时候,两
人去一个很远的城市旅行。洗澡的时候,酒店的客房服务到了。就在那短短的一瞬,乔治认定
妻子与她的神秘情人有个联络人。当妻子建议他去做心理治疗的时候,他坚持要她去做催眠,
把实话说出来,而且还要做各式各样的测谎——她真的做了,而且也通过了测试。
和罗杰一样,乔治也忍受着原始创伤的折磨,也把妻子当成了母亲,就像俄狄浦斯(Oedipus)
把母亲变成了妻子一样。悲哀的是,这两人的创伤都形成得太早,以至无法碰触,也没法解
决。认知疗法、行为矫正、积极想象——这些方法都无法动摇他们强迫性的错觉。
强迫性的想法会给人造成伤害,但在有些案例中,它化作欲罢不能的“迷恋”,确实点燃了人的创
造性,或是让人找到了存在的理由。有人问雕塑家亨利·摩尔(Henry Moore),如何做到在数十
年间始终保持旺盛的创造力,他答说,他的激情太多太浓,没法雕凿得完。
荣膺诺贝尔奖的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同样也遭受了迷恋带给他的长达
五十年的折磨。1889年,他遇见了美丽的爱尔兰革命家茉德·冈(Maud Gonne),当时她伫立在
门口,盛放的苹果花像画框一般镶在门边。叶芝后来说,自从那一眼起,他一生的烦恼开始
了。五十年后,在临终的床上,他依然在写她。她去哪儿,他就追随到哪儿。他向她求婚了许
多次,次次都遭到拒绝。他提出放弃创作,投身到她的世界中,但她继续沿着自己的政治道路
向前走去——这条路通向了北爱尔兰冲突,构成了爱尔兰的悲惨历史。他知道,她走在一条命
定的旅程上,而他无力拯救。于是他开始为她写作。
一个女孩的身影浮现 红唇凄然
宏伟的世界仿佛浸没在泪水中
像奥德修斯与多舛的船队般命中注定
也如普里阿摩率众 傲然殉城
此后的数十年里,他对茉德·冈的浓烈迷恋始终持续着。有时候他陷入绝望和感伤,甚至想要自
杀。
可是我啊 穷困潦倒 有的只是梦
我已将梦铺在你脚下
轻一点踩吧 因为你踩的是我的梦
茉德嫁给雇佣兵约翰·麦克布赖德(John McBride)的时候,叶芝感受到的是双重的拒绝:她不
仅选中了别人,而且那个人简直处处是他的反面。后来,因1916年复活节起义(Easter Rising)
失败,麦克布赖德被英国人处决,叶芝赶到茉德身边,再次求婚,结果再次遭拒。爱迷心窍的
叶芝气得发疯,竟向茉德年轻的女儿伊索尔达求婚,明智的伊索尔达一听就知道这是个坏主
意。后来,心灰意冷的叶芝娶了一位英国女子,拥有了幸福的婚姻,还生了两个孩子,可即便
在临终前,他还在牵挂着茉德。
文学系的学生或许要感谢茉德的铁石心肠,这是因为——借用奥登(W.H.Auden)在悼念叶芝的
诗中形容爱尔兰的措辞——她“将他刺伤成诗”。叶芝承认,他是多么愿意交出自己的文采,换得
与她携手:
若她真的理解了 谁又能说
筛子里会有什么摇落?
我或许就将抛却这些贫乏的字句
心满意足地投入生活
浓烈的迷恋点燃了叶芝的诗情。不过,和罗杰和乔治不一样的是,他至少还可以把痛苦升华成
艺术。没人能说清,为何偏偏是这位女郎如此强烈地激活了他无意识中的阿尼玛,以至于在他
心中占据了这么重要的位置。
从痴缠之人的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心灵中某些至关重要的因素被投射到另一个人身上
时,会出现另一种结果。切勿把那种强迫性的想法与爱混为一谈;那纯粹是投射,绝大多数情
况下,它反映出生命早期亲子关系的某些状况。孩子都需要依赖父母,因此父母对孩子的心灵
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于是,创伤、融合的身份、最深层的关系互动状况,都深深镌刻在心灵之
中。被激活之前,无意识的念头一直保持在被压抑的状态;激活之后,它会被投射到另一个人
身上。如果那个人身上具备我们缺失的碎片,并因此承载着我们的全部幸福(或是恰恰相反,
成为我们最大的恐惧),强迫性的投射性认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就发生了。
“坠入爱河”就是投射性认同的结果。恋爱之所以让人感觉那么美好,就是因为在那个短暂的瞬
间,对方能将我们缺失的碎片“反映”回来。从自身那片刻的完整感中,狂喜的感觉油然而生。显
然,对方身上也会有与我们自身的无意识不同的品质,因此这种投射不会持续很久;当现实取
代了幻想,我们会感到冷淡和漠然,甚至会厌憎对方显露出来的“弱点”,于是,“爱”往往就被这
些感受取代了。我们都知道痴迷的爱是什么样子,这是因为它承载着我们最原初的投射——不
仅仅是童年时期遗留下的那些,还有源于生存困境的投射,即孤独地存在于一个在浩瀚虚空中
不停旋转的星球之上。
正如罗杰与乔治被困在孩子对父母的需要中,叶芝被困在他对一个女人的投射中。诸多证据表
明,她完全不适合当他的伴侣。无法拥有的人或事进入了意识,因此变成了强迫性的想法,或
欲罢不能的迷恋。不请自来的念头携带着大量情感,威胁到了心灵的稳定状态。由于失去了平
衡,我们于是做出了看似不理性的、有破坏性的举动,但它们都是无意识念头的合理结果。
显然,在这个阴郁之地,我们需要面对的任务是把无意识的心理活动带入意识。这个任务最为
艰难,有时候会由于我们承受不了而不可能做到,于是,强迫思维与行为就继续存在下去,我
们也继续滞留在地狱之中。我们已经看到,由于那些不请自来的念头通常都深深根植于早期经
历中,而且往往是童年时期,对当年的那个孩子来说,我们如今受到召唤、需要面对的那些事
情实在过于沉重,根本无法承受和消化。正是对那些多到无法承受的情感的反射性记忆,令强
迫思维和行为得以运作。
成年人有能力承受那些“无法承受”的东西。比如:“我很孤单,真的很孤单。没人会陪伴我、支
持我。”“我会受到伤害,重重的伤害。”“他们不会照顾我的,也不会满足我的需求。”“我怕疼,
我害怕那种害怕的感觉。”“我没能力承担起自己的人生旅程。如果没人来拯救我,我会过得很
惨。”
看,就是这些。这些秘密埋藏得如此之深,无可避免地对我们的灵魂产生影响,以至于我们既
不能面对它们,也无法战胜它们。可它们不会消失不见,在我们最想全面掌控人生的时候,它
们不请自来。它们令我们想起自身的脆弱,令我们感到失败,它们羞辱我们、贬低我们。可
是,我们的任务依然是去面对,面对这些无法承受的想法,令它们最终失去暴戾的力量。荣格
指出:“我的绝大多数患者都明白深层次的真理是什么,却没有把它活出来。” 也就是
说,除非我们把深层的真理活出来,否则我们还将会在地狱里度过许多个季节。
上瘾:伊克西翁之轮
厚颜无耻的伊克西翁引诱了赫拉,宙斯勃然大怒,罚他被绑缚在一个轮子上,在冥府中永无休
止地旋转。(有趣的是,唯有俄耳甫斯的优美音乐能让轮子停转,但这也只是暂时的。叶芝也
是,唯有从他的灵魂痛楚中提炼出的优美音韵,才能抚慰那痴狂的迷恋。)
我们对伊克西翁的困境都不陌生。一个强迫性的想法,加上紧随的强迫行为,将我们牢牢绑缚
在“始终如故”的轮转之中。有哪个老烟枪不曾因为总是戒不了烟而厌恶自己?有哪个酒徒不是借
着眼前这一杯来安抚上一杯引发的内疚?有哪个贪食的人不曾看着日渐增多的脂肪而胆战心
惊?有谁不曾感到自己就像被绑在了自我挫败的想法与行为的铁轮之上?即便是那些最擅长自
控或取得了很高社会成就的人也不例外。
有不少人已经不再把酗酒的人看成失败者或缺乏意志力,而是最需要修正自我感的人。例如,
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认为,那些难以自制的酒徒认为自己能够掌控住酒精。
就这样,战书已下,角斗开始,但胜出的往往是酒精。随后,酒徒再次遇到新一轮的挑
战,往小里说,是认为自己能严格做到滴酒不沾——这愿望迟早要屈服于日常生活的压力;往
大里说,就是幻想自己能够掌控无法掌控的东西。因此,酒徒想去安抚的情绪痛苦反倒变成第
二位的,位居第一的,是他或她被征召参与的“力量的较量”。这个循环只会愈变愈糟,除非能像
匿名戒酒互助会(Alcoholic Anonymous)坚持的那样:酒徒需要承认,自己在这场较量面前其
实并无力量可言。
荣格曾对匿名戒酒互助会的创始人提出,“从较低层面上来讲,对酒精的热望,等同于我们灵魂
中对完整的渴望”,这是一种想与更高力量建立联结的含蓄尝试。 酒精,或其他任何情
绪调节药物确实能对人的生理机能产生影响,能够让人短暂地体验到联结的感觉,但随即它们
又会把这种感觉一把撤回。为了安抚新的痛苦,人只能继续依赖它们,如此循环往复,永无尽
头。
唯有通过臣服,放下“我能掌控”的幻想,并承受住因此产生的两种痛苦——自我失去掌控感的痛
苦,以及原本想要安抚的痛苦,人才有可能从伊克西翁之轮中解脱。这与臣服神的旨意有些类
似——“勿按我的意愿,而是你的意愿”。
荣格分析师玛丽昂·伍德曼(Marion Woodman)用相当感性的笔触阐释了伊克西翁之轮那地狱般
的恐怖:
在这些成功人生的面具背后,潜藏着幻灭与恐怖。有一个共同元素会反复出现。在意识层面,
个体如同受到驱使一般,在自行设置的严苛框架内,期待自己能拿出越来越好的表现;在无意
识的层面,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一旦每日的例行事务完成,有无数个人层面与集体层面
的原因会导致混乱爆发。意志力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如果人一直维持着意志力,代价是牺牲
掉人格中的其他一切,那么虚无感就会油然而生。到了夜晚,到了转回来面对自己的时段,外
在的面具与内在的存在并不交流……强迫行为令人生变得狭隘逼仄,直到毫无活着的感觉——
生存着?或许是。但根本没有活着。
伍德曼指出,那个框架,即伊克西翁之轮,是被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虽然我们并没意识
到。为了巩固我们摇摇欲坠的自我感,无论我们搭建出来的结构是什么样子,我们的上瘾模式
都是对抗焦虑的防御手段,不管我们知不知道这一点。一切上瘾其实都是管理焦虑的手段。每
当焦虑所依附的心理素材被激活,我们的心灵就开始防御。
随着焦虑感愈发严重,我们沉溺在某些重复性的、让我们能够体验到“联结感”的行为中。在那样
的联结感之下,焦虑感暂时消退了。此类行为有可能完全是下意识做出的。一个人有可能会点
上一支烟,抽完,摁灭,然后继续和别人谈话,在整个过程中,意识根本就没有进来打断。不
幸的是,短暂联结带来的愉快感觉不会持续太久,于是,待到饱含焦虑的心理素材被再次激活
的时候,这种行为必须被重复一遍。伊克西翁的轮子不停旋转,将人一次次地带回初始的地
方。
正如伍德曼指出的,把混乱永远关在港湾里是不可能的,不去感受脚下大地的凶险摇晃也是不
可能的,于是,充当缓和剂的那些行为推动了轮子。再一次,内疚、羞耻感、挫败感立即随之
而来。我们希望那一次次的重复能让我们自由,但它们只会让我们陷得更深。不过,受到伤
害、感到脆弱、感到恐惧,这些肯定都不是我们的错。在名为“上瘾”的阴郁沼泽里隐含的任务,
就是冒险去承担那些无法承担的东西。在意识层面无法被承担起来的东西,会被投射到其他
人、其他事、某种行为上,轮子会再度运转起来。
没有哪种地狱比上瘾更恐怖,因为所有一切看起来都是我们自己的错。“无论我向哪个方向飞,
都是地狱;我就是地狱。”但奴役我们的是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常常是从性格中衍生出来的,它
扎根于过去,在生命的初期阶段成型,且未被我们同化吸收。我们必须记住,当这种想法把我
们困在过去的时候,它也把我们继续限制在童年时期的局限中。这种想法令我们的人生变得狭
窄;它们过于简单地看待事物的起源与结果,它们想要防御存在性焦虑,可那些焦虑是我们成
长过程中必要的伴从。罗杰与乔治似乎命中注定要将母子关系一再重演,因此破坏了成年生活
那潜在的辽阔。叶芝至少还能把自己的痛苦转化为艺术作品,短暂地从伊克西翁的轮子上解
脱。
我们的任务——这任务的确非常骇人——就是挖掘到强迫性想法与行为的根源深处,拆毁上瘾
行为,找到那个被深深掩埋的、原初的、未被理解的想法。然后,身为成年人,为了终获自
由,我们或许能够承担起那些无法承担的,想象那些无法想象的,忍受那些无法忍受的。
伊克西翁的轮子悄然无声地、不可阻挡地旋转着,就在我写下这些、你读到这些的时候,依然
如是。没有人时时刻刻都处于意识状态,与我们的诸多缺点相伴相随的内疚和羞耻感会精准地
侵蚀我们的力量——要面对无法想象的事所必需的力量。深深地潜入焦虑状态中,去感受我们
真正感受到的,即是我所说的“穿越”,它必将推翻那一直困扰我们的情绪的暴政。我们就是地
狱,我们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建造了它,又条件反射地屈从于它。想要找到但丁在那个可怕旅
程的末尾突然发现的“圆形洞口”,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地狱全然地、彻底地经历一遍。唯有深入冥
府,才能将我们从冥府中解救出来。
第六章
愤怒
喂饱三头恶犬
在希腊神话中,看守地狱之门的是一只长着三个脑袋的恶犬,名叫刻耳柏洛斯(Cerberus)。但
丁和向导维吉尔(Virgil)把泥土塞进它的三个喉咙,从而避开了它的血盆大口,安然通过。但
我们很少能如此顺利地避开它狂暴的噬咬。
在中世纪的生理学中,人体完美的健康状态是四种基本液体相互平衡的结果。它们被称作
humours,也就是体液。那个时代的人还认为,人的性格特征也是由体液的量决定的,如果几种
体液的比例非常不均衡,就会导致病态的性格。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本·琼森(Ben Jonson)在他
的剧作《个性互异》( Every Man in His Humour )中讽刺了这种类型学的论调。
以下就是这几种体液以及它们的病态形式。黑胆汁过多会导致忧郁症,或称抑郁。莎士比亚把
他笔下阴郁的丹麦王子打扮成一身黑,这并非偶然,因为观众们会自动把这个颜色与角色的心
理状态挂上钩。过多绿胆汁(黏液质)令人的性格也变得黏糊糊的,人会比较懒,或是整天无
精打采。太多黄胆汁令人暴躁易怒,脾气恶劣。过多红胆汁会造成“胆汁质”的性格,让人充满愤
怒,火气冲天——犹如那只疯狗刻耳柏洛斯。
为什么刻耳柏洛斯长了三个脑袋?或许可以这样推测:愤怒有三种,要么就是它的源头有三
个。anger(愤怒)、angst(忧虑)、anxiety(焦虑)、angina(心绞痛)这四个词的词源都来自
印度日耳曼语系中的angh,意思是“约束、限制”。如果一个生物体受到约束和限制,不能处于自
然的舒展状态,就有可能感受到愤怒、焦虑或身体上的压力。然而,对很多人来说,愤怒不会
被家庭圈子所容忍,因此,当孩子感受到心理层面上的“限制”的时候,这种不被接纳的情绪反应
会被引导到三个方向:要么发泄出去,要么被压抑下去,成为抑郁,要么就是令内心中的阴影
愈发分裂。
在与阴影相遇的体验中,性欲与愤怒是最成问题的,这并非偶然。因为它们都是被自我世界体
验到的,也是人人都有的,它们都不遵从规则,会扰乱社会秩序,也不受人控制。可是,只要
人存在,总免不了受到约束和限制,所以愤怒总是在所难免。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都漂浮
着一团团的愤怒,就像那一团团的悲哀和恐惧一样。由于大多数人接受的训导都是不可以诚实
地表达情绪,尤其是愤怒与性欲,所以我们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背负着这些分裂的情感。有时候
它们一直被压抑着,成为长期的、低程度的抑郁;有时候它们离表面非常近,终于带着强大的
破坏力喷发出来,伤害自己,也殃及他人。有时候,一个人背负的愤怒过于沉重,以至于始终
受到它的支配。
数年前,瑞士出现了一本名为《玛尔斯》( Mars )的自传——玛尔斯是罗马神话中的战争与愤
怒之神。作者的笔名叫作弗里茨·佐恩(Fritz Zorn)。在德语中,Zorn的意思是“愤怒”;而他的
真实姓氏是Angst,即“忧虑”。在这本充满激情、犀利刻薄的精彩作品中,佐恩猛烈地抨击了他
的原生家庭,还有他所属的瑞士中产阶级文化。他出生在钟鸣鼎食之家,既富有又有特权,但
他也是严苛又沉重的期望的囚徒——瑞士社会的共同心理曾经是极为严格、规矩、苛刻的,现
在也依旧如此。在将近三十岁的时候,佐恩得了癌症,时日无多。他意识到自己从未真正活
过,这不仅让他感到极度愤怒,而且,他认为自己的癌症正是严苛的环境导致的——他的精神
状态在躯体上表现了出来。他心中无人看见也未能表达的愤怒渐渐演变成了恶性的狂怒。(有
零星的证据表明,特别难以表达愤怒的人的免疫系统更容易受到抑制,也就更容易患上癌
症。)
在《玛尔斯》一书中,佐恩控诉了他那个富有名望的家族对人的“标准”要求,控诉了瑞士的文
化,也控诉了命运——命运给了他一段这样的人生,又猛地一把夺走。借由写作《玛尔斯》
——它后来成了瑞士的畅销书,一部相当受争议的名作——佐恩希望能冲刷掉自己心中恶性的
狂怒,将自己从正在转移的、缓慢吞噬他的癌症中拯救出来。他与癌症赛跑,想要完成这本
书,也给自己赢得自由。就在去世前一天,他得知有出版商接受了这本书。一直未曾被人看见
的愤怒深深地进入了细胞层面,现在终于可以被表达出来了。这部作品成了畅销书,因为它表
达出了太多人无法表达的东西。
在《中年之路》中我指出,我们每个人都忍受着名为“难以负荷的重压”的创伤,即孩子的脆弱边
界无力抵抗外部世界;要么就是名为“匮乏”的创伤,即对于孩子的需求,外部给出的回应并不足
够,甚至干脆彻底忽视或遗弃。这些创伤的结果就是,人误读了世界的天性,也作为共谋,扭
曲了自己的天性,并且发展出一套条件反射式的回应——这就是虚假的自我,其目的是管理焦
虑。例如,一个孩子生活在“难以负荷”的环境中,比如说有个酗酒的父亲或抑郁的母亲,这个孩
子为了生存下去,容易发展出一种被动的、依赖的人格。而一个忍受“匮乏”的孩子,容易形成较
低的自我价值感,并且会像上瘾一样,不断寻求他人的情感支持与慰藉。在这两种情况下,孩
子都不知不觉地成为共谋,令自我疏离的感觉变得愈加深重。在这两种情况下,由于自然天性
遭到了限制和约束,人背负着大量的愤怒——虽然自己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
此外,还有第三种能够引发愤怒的创伤——我们意识到,或是勉强算是意识到,我们多多少少
自愿地参与了对自己的伤害。我们都知道——虽然我们可能不愿意承认——我们就是自己最大
的敌人,而且,在生活中我们秉持着一些糟糕的信念,并以这些信念来对待自己和他人。用萨
特的话说,这些糟糕的信念叫作“自欺”(mauvaise foi)。这第三种愤怒最终指向我们自己。而
刻耳柏洛斯有三个脑袋。
杰拉尔德的父亲比母亲年长二十岁。等到杰拉尔德长成男孩,需要父亲的教导时,父亲已经年
事颇高、体弱多病了。杰拉尔德进入青春期时,父亲过世了。由于身边没有智慧长者帮助他摆
脱母亲情结那令人退行的力量,杰拉尔德漫无方向地生活着。母亲继续养着他,而且也很高兴
这么做,因为她已经把他擢升为伴侣的替代人。杰拉尔德背负着对“缺失的父亲”的需要,这种深
埋在内心的忧郁与悲哀难以名状,却统治着他的心灵。在将近四十岁的时候,由于感到消沉,
他来寻求心理治疗,唯有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没有父亲”的创伤对他影响有多深。
杰拉尔德厌憎母亲,因为他知道她严重干预了他的成年生活——虽然其中不乏他的配合。因
此,他对女性怀着一种埋藏得很深的矛盾心态。出于这种心态,他从没在爱情关系中做过承
诺。无意识地,他把心目中母亲具备的那种力量转移到了女友身上。由于害怕那种力量,他总
是停留在亲密关系的边缘,而且,他发觉自己总是对女性憋着一肚子火。他从来不会辱骂女性
或拳脚相加,但对于那些他认为想控制他的女性,他确实会暴跳如雷。与此同时,在事业方面
他也没有认真投入过。他惊讶地意识到,他对那位他几乎不了解的“老家伙”也很愤怒,因为父亲
既没有当过他的人生导师,也不曾给他阳刚的爱,去平衡母亲的阴柔之爱。
1992年4月,在费城荣格研究所的一场演讲中,《缺位的父亲,失落的儿子》( Absent Fathers,
Lost Sons )一书的作者、来自蒙特利尔(Montreal)的荣格分析师盖伊·科诺(Guy Corneau)援
引了一个案例:一个孩子在上学之后忽然变得暴力起来。这个孩子被充满爱心的母亲抚养长
大,可他没有父亲。孩子一直不知道世上还有“父亲”这个概念,直到他上了学,看见别的小朋友
在放学后有爸爸来接。他攻击的正是这些孩子。他的发展需求遭遇了限制,这让他充满愤怒,
也就是说,他对缺失感到愤怒。
杰拉尔德也是这样。他知道自己厌憎女性,因为他害怕她们的力量,但他发现,原来他对缺失
的父亲也抱有强烈的愤怒,这个认识成了他治疗过程的转折点。他把“匮乏”的创伤,以及对获得
教导的渴望带入了意识,这帮助他把负面能量从女性身上移开,转到“缺失的教导”这个方向。随
后,他得以把诊疗视作帮他走出母亲情结的仪式,也看作一种教导——这部分地填补了父亲的
空缺,同时,也是一座引导他走入成年的桥梁。
杰拉尔德的愤怒实际上是对早期创伤的合理反应,但他先感受到的是消沉,随后又将它错误地
指向了女性,然后,他开始攻击那个总是徘徊不散的父亲的身影。一旦愤怒的原因——藏在背
后的健康动机——被看见了,他的能量就获得了自由,可以用在正确的任务上了:在这个不够
完美的世界里长大。待到疗程结束时,杰拉尔德已经可以进入稳定的亲密关系,他结了婚,同
时也找到了一生的事业。
杰恩是个热心肠,身边的人遇到了问题都喜欢找她求助。青少年的时候她就想当护士,但后来
做了社工。她的父母都是酒鬼。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杰恩就被指定为调停人、问题解决专家、
弟弟妹妹们的代理母亲。家里的其他孩子长大后,都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要么嗑药,要么
酗酒,但杰恩没有。“有自己的感受”是一种奢侈,而她从来没享受过。她冲每一个人微笑,扛起
他们的重担,人人都喜欢她。乍一看,杰恩的人生相当完美——她是个非常能干的“治疗师”,也
知道自己是谁。
然而,严重的偏头痛常常向她袭来。一切办法她都试过了——吃药、催眠、生物反馈——但每
种都见效甚微。绝望之下,她来做心理分析。杰恩和杰拉尔德不同,杰拉尔德知道自己很愤
怒,只是他的愤怒指向了错误的方向,而乐呵呵的杰恩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有愤怒。她认为自
己是个开开心心的、阳光型的人,她确实也是,可她正坐在一座由愤怒垒成的大山上——这不
仅是由于童年时期那些堪称虐待的重压,从更深的层次上看,是由于她的灵魂被扭曲得变了
形。
杰恩常年生活在抑郁的山谷中,这抑郁来自向内攻击的愤怒——她只有权利攻击一个人,也就
是她自己。在她的阳光性格之下,潜藏着极大的愤怒。那种强烈又巨大的能量得有个去处。孩
童时期,她不被允许表达自己真实的需求,不能表达愤怒,于是她把这一切压抑下去,藏在“不
冒犯任何人”的人格面具背后,最终,她是如此认同这个名为“照顾者”的虚假自我,以至于无意
识地选择了这种性质的职业,这样她就可以继续去疗愈一个又一个受创的家庭。无论工作中她
有多么能干,得到了多少嘉许,她依然是那个受伤的孩子,只能用一个存在性的谎言来维持脆
弱的自我。
杰恩疗程的转折点发生在这个时候:她的父母原本住在外地,如今要搬到她所在的城市来。头
痛排山倒海地袭来,她意识到,这不仅是因为父母希望她继续承担起照顾者的角色,也因为她
害怕自己不愿承担。她感受到的恐惧正是当年那个孩子的恐惧。那个孩子没有其他选择,只得
听从家庭的强行安排。对于这份恐惧,她最先采用的防御手段就是内疚。
开始直面自己的内疚、恐惧与头痛时,杰恩渐渐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她的防御,对抗的正是她
身下的那座愤怒的大山。当她终于能把说不出口的说了出来,当她终于可以对父母表达强烈的
愤怒,并对他们说不的时候,她的头痛停止了。直面父母,是她这辈子做过的最困难的事。尽
管那些孩童时期无法承担的恐惧依然留在心中,但现在的她是个成年人了,可以划出那条之前
从不曾存在的界线。
与杰恩的童年如影随形的虐待经历被她内化,变成了毒素。“懂事的乖女孩”只能把强烈的愤怒发
泄到自己身上,不然她还能怎么做?她这种自我惩罚的行为令人想起威廉·布莱克在1794年写下
的诗——《毒树》。
我对我的朋友很生气:
我说出了我的愤怒,我的愤怒终结了。
我对我的敌人很生气:
我没法说出来,我的愤怒日渐增长。
接下来,诗里的叙述者用恐惧,用眼泪,用微笑,用花言巧语来浇灌这棵毒苗,就跟杰恩后天
习得的做法一样。最终,这棵毒树结出了有毒的果实,不仅伤害了他人,也伤害了它的宿主
——它就生长在他的灵魂之中。就像伊甸园里的树一样,这棵毒树结出了苦涩的果子,比如偏
头痛,要想把它连根拔除,唯有通过有净化作用的精神宣泄,而这是当年的孩子做不到的。此
前,杰恩一直在防御那些强烈情绪的冲击,这确实有必要,但现在她冒险承受住了,这不仅是
因为偏头痛愈演愈烈,也是因为她终于变得足够强悍,可以面对一直背负着的愤怒了。这愤怒
不仅是她对创伤的合理反应,也是令她做出改变、承担起自我疗愈责任的能量之源。
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就是问题,我们一直秉持着糟糕的信念生活,这种愤怒是最难承受的。
对于那些努力变得更有意识、学着为自己负责的人来说,最令人震惊的发现无疑就是——认识
到自己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成了伤害自己的同谋。我们的虚假自我,以及潜藏在防御手段背后的
恐惧,已经够难承担的了,就像杰恩的故事呈现的那样。收回我们的投射,以及我们对他人的
责怪,这也同样不容易,就像杰拉尔德的故事告诉我们的那样。但最为困难的是面对这个事
实:让我们的创伤久久不愈的,正是我们自己。圣保罗说过,虽然我们知道何为正确的事,但
我们没做。芝加哥美术馆(Art Institute of Chicago)里有一幅伊万·奥尔布赖特(Ivan Albright)
的画作,名字就叫“那些我该做却没做的事”。
有谁不曾尝过这句话背后的苦涩滋味?有谁不曾在凌晨四点醒来,惊觉这个可怕的事实:过往
发生的事情暂且抛开不提,我们的人生变成了什么样,我们成了怎样的人,我们对别人做过了
哪些事,这一切其实都应该怪我们自己。面对这个觉察,我们可能会感到羞耻、悲伤或抑郁,
但里面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指向自身的愤怒。
有时候,这种愤怒找到了出口,它化作怒火,甚至是伤害性的行为,朝着别人发泄出去。但更
多时候,这种深层的愤怒——它源自分裂的灵魂在与自身对抗——朝向了我们自己,变成无穷
尽的自我诋毁、自我虐待,让我们做出自我破坏的行为,削弱自身的潜力。
说到底,我们必须认识到,正如人人心中都有一泓名为“悲伤”的湖水,每个人心里也都有一座名
叫“愤怒”的大山。愤怒是灵魂对它遭受的创伤做出的合理反应。我们之所以将愤怒一直压抑在无
意识中,很可能正是因为,如果现在把它表达出来,就会重新激活当年表达它时所引发的巨大
危险。我们也有可能把它转向自身,化作身体上的症状表达出来:要么陷入抑郁,要么做出糟
糕的决定来自我破坏。或者,我们也有可能把愤怒转嫁到别人头上,去伤害那些沉默的替身
——他们替代的正是当初我们不敢面对的人。总之,愤怒是对灵魂所受到的限制的反射性反
应。因此,它不仅是心灵的防御系统的一部分,也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暗示——当我们对它追根
溯源,或许就能疗愈灵魂。
愤怒被意识转化之后,会变成至关重要的能量,它不仅可以用来疗愈创伤,还能拓展灵魂的渴
望。只要我们与创伤认同,就会继续卡在受害者的心态中,沉溺在盛怒的苦水中。当我们能够
认识到,面前的道路可能被那头名叫刻耳柏洛斯的三头怪兽阻挡了——那只代表着“难以负荷的
重压”“匮乏”和“自我憎恨”的疯犬——我们就有可能绕开那个凶神恶煞。
虽然原始创伤极难治愈,但它们对于我们的象征意义是可以被改写的。当我们卡在愤怒当中,
不管它有多么合理,我们都如同深陷地狱,留在过往的阴暗中无法自拔。我们当前的人生依然
被过往的创伤所定义。当我们能够承认愤怒的存在,追溯它的源头,看清它对我们的自我形象
的影响,那么,最终我们就有可能突破过往对我们的限制。那只名叫刻耳柏洛斯的三头恶犬看
似卧在我们前方,挡住了道路,但实际上它就在我们心里,我们随身携带着它。当我们像浮士
德博士一样,认识到我们所在之处即是地狱,那么我们就已经踏上了那条走出地下王国的漫漫
长路。
第七章
恐惧与焦虑
焦虑如冰山,我们是泰坦尼克
正当我开写这一章的时候,我女儿塔琳开始了每五分钟一次的宫缩。希望等到这章写完,我就
能见到女儿,还有我的第一个外孙女瑞秋。我期待着这双重的欢乐,但我也要坦白一个神经质
的想法。
得知瑞秋就要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焦虑,而非快乐。我的第一个念头是——
对此我一点都不感到自豪——“又多了一个要操心的”。我的第二个念头是关于塔琳的,身为职业
女性,她很快就要背上一副沉重的担子了。第三个念头才是“正确的”那一个——我对自然的伟大
运转产生了深深的敬畏,我们是其中多么微不足道又多么重要的部分啊。我回想起当年塔琳出
生的那一刻,我不敢相信那个奇迹,也不敢相信自己何其有幸,竟能拥有这么好的女儿。她弟
弟蒂莫西出生时也是一样,这小家伙是我这辈子遇见的最有趣的人。既然我有这么大的福气,
拥有这么好的一对儿女,而且他们如今都已经长大成人,和我像朋友般相处,那我的第一个念
头为何还会那么神经质,饱含着焦虑?
到目前为止,我们这本书里谈到的所有内容背后都隐藏着一条暗线。也就是说,在各式各样的
灵魂沼泽中蕴含着一个共同因素。这条共同的暗线就是焦虑。我给自己得知女儿怀孕后的第一
反应贴上了“神经质”的标签,这份焦虑我会自行解决。但我的反应显然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条件反
射,不受清醒意愿的控制。那么,面对如此奇妙又美好的事情,为何人会感受到一股暗流,好
像被一下子拽到了阴郁的沼泽地?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称我们这个种族是“向死而在”(Being-toward-Death)。索伦·
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雄辩地阐释了“恐惧与颤栗”,还直接用它做了书名。奥登则称
我们的时代为“焦虑年代”。
在《追踪神祇》一书中,我提出,如果把神话的地毯从人们脚下抽走,那么这整整一代人都会
感到焦虑。起到稳定作用的神话正在稳步销蚀,令人们内在的经纬线变得黯淡无光,而数个世
纪以来,人类正是依靠它们来绘制自己的方位的。从但丁那阴沉的确定性,到塞缪尔·贝克特
(Samuel Beckett)笔下的凶险景象,是什么在引导着我们的世界?无需细数证据,我们也都会
同意,文化价值正变得越来越不清晰,传统习俗的抚慰作用也在日渐减弱。伴随着这些失去,
创新与创意的自由度确实增加了,可是,“在两个世界之间徘徊,一个已经死亡,而另一个还无
力诞生” ,极少有人会感恩自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吧。
当我写下这些字句的时候,塔琳的宫缩还在持续。瑞秋不愿来到这个世界上,这很容易理解。
怎么会有人愿意离开那般闲适又安全的家园,来到这个危机四伏的地方?那个小丫头或许比我
们所有人都聪明,可到最后,她还是躲不过做人的命运。这令她成为我们的一员。她将从永恒
堕入历史,从纯真坠入罪疚,从神秘参与的融合感跌入疏离。她将成为我们中的一员,然后,
等到她长大成人,读到这一段,或许她会原谅那位早已不在人世的外公——在她经历了充满惊
惧的旅程,降生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夜,他曾经有过这些“神经质”的念头。
可是,那条线索为何能贯穿人类的一切行为?我们曾经连接着宇宙的心跳,一切要求都能被满
足,却骤然跌落到这个危机四伏的地方。我们的降生就是创伤性的,它是心理上的创口,一个
我们从未彻底从中恢复过来的灾难性事件。人生中的绝大多数主题都是对这场灾难性的分离的
回应。我们要么是想努力地回到与母亲脐带相连的状态,要么就是不得不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
里寻找联结。既然不可能真的回到子宫,我们就会借助以下这些方式,与母亲建立退行性的认
同:要么依然保有婴儿式的心态,要么借助药物和酒精来麻痹痛苦的意识,要么就是放弃自己
的成长任务,把主权移交给某位上师或某种狂热的崇拜。
人人都有这种退行的趋势。在过去,成人礼会支持人们面对这个问题,这种仪式能够提供动力
和更为宽广的价值观,借助这些,力比多得以从“退行”转变为“前进”。如今,没有了有意义的成
人礼,没有了富含文化意义的神话,我们基本上只能靠自己去尽力完成突破。然而,在我们向
前发展的每一步中,日益增长的焦虑都如影相随。事实上,每一天我们都得在焦虑与抑郁之间
做出选择。如果被退行的行为俘获,并因此破坏了个体化的进程,我们就要忍受抑郁之苦;如
果战胜了心理上的怠惰,迈入外部世界,我们就要体验日益增长的焦虑感。这真可谓是左右为
难。但是,无论有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确实每时每刻都要做出选择。
把恐惧、狭义的焦虑、广义的焦虑三者间的区别辨析清楚是很有用的。恐惧是具体的。我们怕
狗是因为之前被咬过。狭义的焦虑是一种无来由的不适感,几乎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引发它,某
些具体事物甚至会让它持续一阵子,但它通常是源自一个人对人生总体上的不安全感。不安全
感的程度、引发的焦虑的量级,部分地取决于一个人的独特历史。人所处的环境、原生家庭、
文化背景里的问题越多,无来由的焦虑就会越多。同样,创伤的性质也是因人而异的。而广义
的焦虑则是人人都有的,它反映出人类脆弱的生存处境。我们也可以把它定义成“存在性焦虑”;
也就是说,它源自一个有意识的动物,认识到了“命悬一线”的那根线有多么细弱。
玛莎·杜鲁门·库珀(M.Truman Cooper)在一首诗中描写了恐惧、狭义的焦虑与广义的焦虑是如
何通过各种方式混合交织在一起的,渐渐地,它们好像融合成了同一种感受:
假如说 你害怕的东西可以被抓起来 关在巴黎
那么 你就有勇气去往世上任何一地
罗盘上一切方位都向你开放 除了指着巴黎的方向
你依然不敢涉足那座城市的边界线
你也不太愿意站在数英里外的山边
远远望着巴黎城的灯火 在夜色里渐次点燃
为确保安全起见 你决定
干脆远远躲开法国吧
可随即危险似乎逼近了国境线 你感觉到
心中那畏怯的部分 再次将整个世界铺满
你需要这样一位朋友 他知悉你的秘密 然后告诉你
先去巴黎
想想巴黎的样子,就会觉得,对这座城市怕成这样简直是荒谬可笑。可是,如果一个人曾经在
巴黎遭遇过创伤体验,那么单是提到这个名字就足以唤起强烈的情绪。当然我们知道,诗人是
在借用巴黎来比喻我们害怕的东西。城市的名字可以随便改,换成苏黎世或多伦多,或是我们
的故乡,效果都一样。对巴黎的恐惧渐渐泛滥、扩大,演变成了我们时时刻刻都背负着的焦
虑,或者说,一种非具体的恐惧。我们走到哪儿,巴黎就跟到哪儿;我们不敢确定,是不是在
某个地方就无意中踩上了它的边界线。条条大路通向的不是罗马,而是巴黎;那座城市也不再
是光之城,而是“存在性焦虑”之城。
即便避开了令我们恐惧的东西,巴黎也跟着我们;巴黎城无处不在。“无论我逃向哪里,都身在
巴黎;我就是巴黎”,弥尔顿大概会这样写吧。既然巴黎是躲不开的,要想削弱它对我们的暴虐
统治,唯一有建设性的办法就是勇敢地面对它,去全然地感受它、穿越它。那位说出“先去巴黎”
的“朋友”正是自性,我们内在的那个寻求疗愈的调节中心。库珀马上就知道,这是一片灵魂的沼
泽地;他也知道,穿越这个阴郁之地的唯一路径是什么。
我们应当将深度心理学的发展归功于无处不在的焦虑,以及它的无数化身——各种各样的神经
症。当沙可(Charcot)和让内(Janet)、弗洛伊德、布洛伊尔和荣格遇到了医学手段的局限
时,他们转而去寻找那些不肯对药水、偏方或手术产生响应的无形之力。
起初,他们被许多当时被称作“歇斯底里症”(hysteria)的案例引领到了心灵的深处。后来,那
些症状被称为“转化性神经症”(conversion neurosis),如今又叫作“躯体形式障碍”(somatoform
disorder)。这些身体上的病症似乎找不出任何生理层面的原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似乎也不
是装出来的,但它们对个体的损害却显然是实实在在的。
尽管弗洛伊德从不少地方得到了启发,但他天才地发现,那些症状是两种价值——有时候是完
全对立的两种价值——妥协折中的结果。如果我是一个为即将到来的数学考试而忧心忡忡的小
孩,我会感受到如假包换的头痛——压力导致我的毛细血管收缩了。我确实头痛,但我也可以
请病假,不必参加考试了。利用头痛这个小小的代价,我避开了巴黎。
我第一次遇上躯体化的神经症,是在精神分析研修期间。母亲情结把莉莉压得喘不过气。她母
亲非常自恋,严重地入侵她的边界,好像要吞噬她的生活似的。母亲成功地破坏掉了莉莉的每
一段恋爱关系。在这种无意识的奴役状态下,莉莉一直非常抑郁和愤怒,却无法逃脱母亲那强
有力的魔咒。她的左前臂会出现周期性的麻木,去神经科也没有查出个所以然来。反正这种麻
木感也只是偶尔来袭,而且持续差不多半小时就消失了,她也就没有重视。
来做分析三个月后(她瞒着母亲来的),有一次在诊疗现场,莉莉感受到了那种麻木。我们探
讨了这个现象,却毫无结果。诊疗结束的时候,我把一支笔轻抛给她,好让她填写下次的预约
时间。她用左手敏捷地接住了笔,那时我才头一次意识到,她是个左撇子。在她敞开内心的那
个短暂刹那,我问她:“你会拿那只手臂做什么?”“我会杀了她。”她一边说,一边拿着笔做了一
个朝前刺的动作。
后一次诊疗中,我们谈到了她心中携带的杀意的强烈程度,以及这种能量——无论有没有表达
出来——对她和她身边的人造成了多大的毒害。莉莉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抑郁之下潜藏着狂
怒;然而,两周后莉莉攻击了母亲,差一点就要把她掐死了,还把她的头发揪下来了一把。
莉莉被自己的行为震惊了,于是搬离了母亲的房子。即便是早期的警示信号也没能阻止她的狂
怒浮出水面。莉莉心中被压抑的愤怒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令她感到极为焦虑。但就像弗里茨·佐
恩一样,她也没有意识到这股能量的强烈程度,直到为时已晚。每当杀意在心中涌动,手臂的
麻木就会发作。那些念头引发出的焦虑感实在太强大了,她无法消化,于是能量流入了身体。
事实上,被暴力念头引发的深重焦虑把莉莉吓坏了,以至于她中止了分析治疗。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狭义的焦虑与广义的焦虑之间的那条细线。狭义的焦虑源自一
个极其有害的情结,而广义的焦虑则是每一个必须与父母分离的人都会体验到的矛盾情感。想
要长大成熟,人就无可避免地要经历分离,这是有助于前进的;当人离开熟悉的环境走向未
知,任何一种分离都会引发焦虑。但在莉莉的案例中,合情合理的广义焦虑遇到了被母亲情结
引发出来的具体焦虑,两者的力量相乘,就加倍放大了。
恐惧症(phobias)这个词来自希腊语中的phobos,意思是恐惧。它可能是被某种特定的创伤引
发的。如果一个人曾经目睹过飞机失事,那他患上飞行恐惧症是很好理解的。但实际上,我们
往往找不到与恐惧症直接相关的创伤体验。
在许多情况下,令我们恐惧的事物其实是一种象征性的代表,背后是漂浮在无意识中的、难以
名状的焦虑。比如说广场恐惧症吧,希腊语中的意思是“害怕去市场”,从字面上看,这真是一种
令人困惑的病症。然而,“市场”的特质就是开放,在那里有可能会与他人发生接触,它是不可预
测的,换句话说,就是当一个人离开安全的家外出探索时,必须冒的“失去控制”的风险。
有一位女士,她的职业是银行职员,却有着艺术家的天赋。她对高度有种特殊的恐惧。一连几
个月,她勇敢地面对自己的恐高症:她会坐上电梯,逐步提高楼层,并走到观景窗前俯瞰城
市。这种脱敏疗法确实有帮助,而与此同时,分析诊疗中的深入探索帮助她看清了,她的恐惧
源自人人都有的焦虑——当我们面对脚下那辽远的旅程时产生的感受。她的恐惧症象征的是,
如果自由地、肆意地去探索自己的天赋,她就会失去脚下的坚实大地;她害怕的是自己的高度
与深度,那风险蕴含在“斗胆相信自己”之中。要响应事业的召唤,她就得走出去,在没有支持的
情况下迈向心灵的空间。因此,我们恐惧的东西或许是源于创伤,但它也常常象征着某种我们
尚未意识到的深层焦虑,或是某些我们尚且不具备力量去承担的任务。讽刺的是,此类“恐惧”其
实是对抗焦虑的防御手段,进一步深究起来,它或许是在对抗那种广义的、存在性的焦虑。
未被意识到的焦虑是最有害的,因为我们永远也不知道它会去哪儿,而它肯定要去往某个地方
——要么投射出去,要么进入身体。在名为“压抑”的腐臭屋檐下,有邪恶的怪兽在孵化繁育,它
们必定会扯断镣铐,侵入其他地方,这是无可避免的。焦虑常常被张冠李戴,比如我们在前几
段里提到的那些恐惧症的案例。如今饮食失调很常见,特别是在年轻女性和中年女性的群体
中。正如我们在“强迫与上瘾”那一章里看到的,强迫思维不仅会令意识变得狭窄,还会迫使人采
取行动去管理焦虑。因此,厌食症或暴食症把关注的焦点放到了身体形象与(或)食物上,这
是因为,这些东西貌似是能够掌控的。显然,一个人可以选择把哪些东西塞入喉咙,借此来掌
控某些事情——当生活中的其他一切都不受控制的时候。因此,饮食失调不仅是意识范围变窄
的问题,也是对焦虑的过度补偿。
辛西娅在孩提时代就失去了双亲。一个不情愿的亲戚把她养大,管束她,训诫她,却没有给她
多少爱。青少年时期,辛西娅染上了盗窃癖,用偷来的东西替代不曾得到的爱。她也开始狂吃
巧克力,然后再催吐。来做诊疗时她已经成年,总是做掉牙齿的噩梦。牙齿象征着她的第一道
防线。她还会梦见有敌人偷偷摸摸地潜入边境,可卫兵们在岗位上睡着了。一方面,人生给她
的只有酸涩,而通过暴食巧克力,她让自己品尝到甜蜜的滋味;另一方面,借助催吐,把那甜
蜜的罪孽清理掉,她好似再度掌控住了那不胜负荷的焦虑感。
辛西娅遭遇的创伤是遗弃。没有一个人真正地爱她、支持她,这种体验引发了海量的焦虑。与
此同时,缺乏父母的爱与支持会全面影响孩子的感知,造成原型创伤(archetypal wounding)。
由于父母是孩子探索世界、身体、人际关系的中介,决定着情结的牢固程度与力量大小,所
以,父母的缺位会导致孩子将原型外推,并因此引发存在性焦虑。
对辛西娅来说,缺失了慈爱的父母,导致的不只是顽固难解的情结,这让她对整个世界的初步
认知都因此受损。相应地,她“选择”了饮食失调,这既是个人情结的体现——她用这种手段防御
狭义的焦虑,同时,这也是防御广义的存在性焦虑的典型策略。失去了能呵护她的母亲,这激
活了负面的母亲情结,于是,对相伴而来的广义焦虑的控制,就集中在了母亲——物质——食
物——身体这个链条上。被遗弃在一个没有母亲的世界,这是无法承受的恐惧,所以她转而去
担忧饮食问题,因为这还能让人好受一点。我能担忧的事情、占据我全部心思的事情,都是我
的防御手段,用来对抗那些令我感到恐惧的、能摧毁我的东西。我的神经症是最基本、最原始
的防御手段,对抗的是我无法承受的焦虑。神经症固然令我痛苦,但与根本无法承受的焦虑相
比,还是能够接受的。
当真正的恐惧就快浮出表面的时候,它很容易被激活,人会感受到恐慌的侵袭。这几乎是最令
人心惊胆战的感受,其他状态很难与之比肩,因为在恐慌发作的那段时间里——漫长得好像永
无止境——人会觉得自己真的要死了。人会感受到窒息、气短或心悸,这些都是彻底被压垮的
感觉。在名叫“无意识”的没有路的密林中,我们不知所措。这里是那个长着山羊蹄子的家伙的地
盘,是潘神 的领地,而我们感受到的,正是以他为名的“恐慌”。
有零星的证据显示,容易恐慌可能是有生物学基础的。也有可能是我们见过父母或其他权威人
物被压力打垮,从而习得了这种行为。但是,被恐慌侵袭也有可能源于“代替”,也就是用一些能
够接受的恐惧来代替无法接受的恐惧。如果我一门心思想着我的大脚趾,时间足够长的话,我
就会感到它在痛,要不了多久,我会认为这疼痛预示着某种绝症。疑病指的就是对健康的正常
关注轻而易举地升了级。你不敢一口咬定说,自己肯定不会得癌症或心脏病,肯定不会死。然
而,与更浓重的恐惧相比,即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一心担忧自己的健康问题好像还能接
受。疑病至少让人得到一点点掌控感,因为病是有可能治好的。去追寻某种缥缈不定的原因,
总比面对真相容易一点——那真相就是,人是会死的,人完全没办法掌控宇宙。当我们把事情
往最坏的地方想的时候,我们不是在有意识地面对坏事、承担坏事,而是在无意识地小题大
做,然后忍受着泛滥情绪的攻击。
恐慌症发作的时候,去全然地、彻底地经历它(实际上,对待一切焦虑状态都应该这么做),
这会迫使我们有意识地面对“灾难”,也就是说,正视那可怕的现实。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发
现,身为成年人,我们可以承受得住,甚至还能想办法去接纳它,有时还会有能力把它放下。
“不放下”,意味着当我们下次再度偏离了狭窄小径的时候——不经意地,但也不可避免地——我
们会再次发现,我们又来到了潘神的密林。就像小时候,我们总觉得有大鳄鱼藏在床底下,或
是有怪物藏在衣柜里,我们知道它就在那儿,那个长着蹄子的、半人半羊的家伙,就要来抓住
我们了。
正如在“强迫与上瘾”那一章里提到的,在焦虑状态下,我们每个人都容易做出一些重复性的动
作。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面临压力的时候,我们会有某些特定的、坐立不安的表现,比如会
嘟哝口头禅、无意识地祈祷等等。形容一个人心情烦躁的时候,我们会说,“早上起床的时候起
错边儿了”,这句俗话反映出生活的程式化,这不仅是因为日常习惯会自行重复,也是因为我们
经常会无意识地运用魔法思维来安排生活。
魔法思维是孩童的以及所谓的原始文化的思维方式的典型特征,当我们处于退行和脆弱状态
时,也会用这种方式想事情。借由魔法思维,我们让自己相信,我们的想法和行为会对世界造
成特定的因果效应,正如世界也对我们有着秘密的因果效应一样。我们用半信半疑的态度对待
迷信。一个连赢几场的运动员可能会继续穿着那双脏袜子去打后续的比赛,直到连胜中断为
止。预祝演员登台演出顺利时,我们会说“摔断腿”(break a leg),这是因为我们唯恐美好的愿
望会招致神祇发怒。我就发现我自己走路时会小心地避开地上的裂缝,因为我不希望母亲摔伤
了腰背。
我们人人都会无意识地借助仪式化的行为来避开模糊朦胧的黑暗力量。如果仪式没能顺利进
行,我们就会感受到更加强烈的焦虑。报纸没能按时送到,忘了某个东西没拿,或是不得不换
一条新路线去上班……我们就会气急败坏。这些仪式就像有神力的护身符一样,可以对抗那个
无法承受的念头:我们身处在一个陌生的、时常不大友好的宇宙中。这些仪式是用来对抗海洋
般浩瀚的存在性焦虑的手段,虽然它们脆弱得不堪一击,但我们还是牢牢地抓着不放。
在典型的强迫症中,患者无意识地“选择”了重复性的想法和行为,将之用作一种仪式化的防御手
段,来对抗那压倒性的、海量的焦虑。有些新型抗抑郁药物显示出一定的次级效应,可以减轻
强迫思维的程度。可是,人人都会产生不想要的念头。任何一种强迫思维或强迫行为都是在防
御浩瀚的焦虑。我能够直接面对的事或许会令我暂时不太舒服,可至少它不再统治我了。
偶尔有些时候,我们会主动选择神经症带来的“继发性获益”,换成委婉的说法,就是“生病也有
好处”。在“做作性障碍”(factitious disorder)中,我们假装或捏造出身体上或心理上的疾病。生
病了,我们就可以扮演受苦受难的角色,或许就可以避开另一些令人备感压力的要求,因此也
就不必面对更大的焦虑。如果我身形肥胖,我或许就用不着面对亲密关系这个复杂又微妙的议
题。我或许会慨叹自己命不好,抱怨别人不拿正眼看我,但我也成功地躲在了由身体构成的防
御要塞里。如果我有伤残,那我显然用不着去面对生活的挑战,也不会遇到更多麻烦了。通过
对狭义焦虑的默许,我躲开了更为沉重的存在性焦虑。
一切行为,即便是那些被我们称作“疯狂”的行为,都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把它们视作对某种情
绪的表达,或是对某种情绪的反应。这就是为什么在分析和寻找病因的时候,分析师必须要
问:“是什么情绪状态引发了这个行为?”无论症状伪装成什么模样,躲在何种象征背后,它表现
出来的都是某种无意识的情感前提。情感状态与象征的外在表现之间的这种因果关系会构成一
种循环效应,渐渐地,它不仅会成为某个特定创伤的外在表现,还会成为一种总体性的人格形
式与反应策略。换句话说,我们变成了自己的创伤。那些命中注定的创伤引发出我们的反应,
而我们把这些反应活了出来,也因此成为那些象征性表现的同谋。这些行为、态度和反应策略
加在一起,构成了我们的“虚假自我”,一个临时性的人格。因此,我们不但深陷在自己的创伤
中,同时还深陷在对创伤的反应中。命运没有允许我们自然而然地舒展自我,我们不得不在反
应性的模式中体验自我,而这让我们与自我日渐疏离。
自我疏离的后果就是神经症。或许神经症是无可避免的——说实话,或许人更愿意继续留在无
意识的状态里——唯一的解药,唯一的出路,就是去面对神经症在防御的那个东西。我们在躲
避什么任务?答案总是能找到的。
管理焦虑
我们最原始的防御手段就是大家熟知的“是战还是逃”。面对难以负荷的重压,我们通常会选择逃
跑。我们学会了与痛苦的现实拉开距离。“眼不见,心不烦。”“你不知道的不会伤害你。”我们压
制,我们遗忘,我们割裂;我们把自己不喜欢的情结投射到别人身上。我们很可能被心中的情
结役使了好几十年,却从来不曾意识到,原来是它们在暗地里邪恶地运作。被它们支配的时
候,我们就好像被转移到了另一套为人处世的理念和准则中,开始遵照那些准则行事,随即我
们重新陷入寻常的意识状态,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转移的发生。
我们经常会把令人不快的事实真相压制下去,这种解离状态(dissociative states)看上去好像也
没什么坏处;我们都会这么做,也毫发无伤。但“解离”(dissociation)的影响就大多了,它有可
能导致记忆缺失,或是让人进入“神游状态”,此时人真的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好似跑到了另外一
个人的生活中游荡去了。近些年,由于在某些重大案件中成为主题,也在诊疗圈中引起极大争
议,多重人格障碍(如今叫作解离性身份障碍)落得了一大堆坏名声。
在解离性身份障碍中,自我被惨重地击碎,以至于无法与无意识抗衡;于是,心灵就自动自发
地漂移到了另一重现实中。这也是个正常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荣格会将情结定义为“人格的碎
片”(a splinter personality)。 但在极端情况下,这种心灵片段可能拥有了自己的“生平
传记”(而自我对此毫不知情),以及与之相符的躯体状况与情感状态。在巨大的创伤面前,我
们都会通过“人格解体”(depersonalization)来管理程度严重到无法接受的焦虑。我们让自己置身
事外,那感觉就像是我们变成了观察者,在一旁看着自己的人生。有时,要熬过某段经历,这
种拉开距离、置身事外的做法是必要的。如果事情已经结束,而人格解体还在过度持续,唯有
在这种情况下才称得上病态。
还有两大类对焦虑的反射性反应需要指出:适应障碍(adjustment disorder)与人格障碍
(personality disorder)。
适应障碍通常与导致压力的因素直接相关,而且它可能会使出一切能用的手段,比如回避、以
完美主义来防御任务完不成的焦虑,或是出现各种由焦虑引发的躯体症状与情感症状。一般来
说,当压力解除了,适应障碍也就随之消失了。
在人格障碍的案例中,当事人基本上都在生命早期遭受过严重的创伤,比如情感或身体上的虐
待,或是性虐。当孩子的脆弱边界遭到践踏,当自我无法应对那压倒性的、汹涌澎湃的情绪,
某些功能被关闭了。就像电脑里安装的浪涌抑制器一样,人格切断了联结,免得它痛苦地反复
过载。从病因上看,这种反应是相当合理的,然而,情感功能此后将永远无法运转了。这样的
人仿佛是从很遥远的地方感受生活,就像在看一部自己主演的电影似的。一般来说,他们的感
情道路都比较坎坷,因为他们同理别人的能力被严重削弱了,而在亲密关系中,同理与共情是
不可避免的情感需求。
患有偏执型人格障碍的人曾经遭受到原始客体(primal objects),即母亲和父亲的“背叛”。他们
调整了自己的人格,去期待并四处寻找这种背叛。他们仿佛被预先置入了背叛的程序,不知不
觉地选择那种能重演这种无意识剧情的伴侣,要么就是他们的猜疑、控制和无法信任会把伴侣
赶走——于是这更加坐实了他们最初的想法,即不能在关系中投入信任。
分裂样人格障碍(schizoid personality disorder)是一种过度保护的行为。这样的人与他人距离很
远,只能做出有限的情绪反应,倾向于避开亲密关系。这种自败(self-defeating)的行为确实能
实现目标——保护自己,免于再次体验到过往那痛苦的创伤。反社会人格(antisocial
personality)的人也是在生命早期遭遇了创伤,他们将别人视作有待利用的敌人,以免别人先利
用了他们。在人生早期关系中感受到的背叛被外推到整个社会;不仅情感功能被关闭了,他们
能感受到的个人痛苦与懊悔都很少,而且,曾经的受害者如今开始伤害别人。
边缘型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客体关系不稳定,这是因为
当事人的自我形象是不稳定的。这类人往往行事冲动,极少考虑到自己会给他人造成怎样的破
坏,他们忍受着剧烈的情绪变化,而且会周期性地感到空虚。孩提时代感受到的难以负荷的焦
虑创造出的自我感是如此脆弱,以至于他们的行为几乎无法连贯。
表演型人格障碍(histrionic personality disorder)源于孩童时期对关注、爱和赞许的需求没有得
到满足。因此,如果此人没有处在关注的中心,就会焦躁不安。他或她会用言行举止来吸引别
人的注意;如果真的遭到轻视,或假想别人轻视自己的时候,他们会感到一阵阵的嫉妒和狂
怒。同样,自恋型人格障碍(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往往令周围的人非常痛苦。这类人
不断地需索他人的赞美与肯定,借此来安抚心中由自我怀疑引起的大量焦虑。他们感到自己理
应得到他人的特殊对待,同时却对他人的需求和痛苦缺乏同理心。这类人很难相处,因为他们
总想操控别人;从表面上看来,他们显得强势又自信,但在内心里,他们感受到的是空虚和不
被爱。唯有和依赖型或依赖共生型的人在一起,他们才能维持较为长久的关系,因为只有那样
的人才会愿意终生围着一个自恋的空虚自我打转。
依赖型人格障碍(dependent personality disorder)与强迫型人格障碍(obsessive-compulsive
personality disorder)犹如两个极端。前者管理焦虑的方式是避免做出决定和承诺,极度服从,为
了得到别人给的一丁点儿好处而放弃诚实与正直。强迫型人格与此刚好相反,他们对人生的不
确定性的回应方式是竭力掌控一切,行事总是出于焦灼与紧张。这类人一心关注细节,这样就
可以忘掉大局;他们是工作狂,过于一丝不苟,吝于关爱自己或他人。
人格障碍最棘手的地方在于,对灵魂的破坏往往发生在脆弱无助的孩子身上。刚刚萌芽的自我
当然没有能力处理这种创伤体验,因此就把至关重要的情感功能关闭了。而在正常情况下,这
个功能可以帮助一个人对人生做出有质量的评估与反应。同时,天然的人格也被严重地扭曲
了,此人被束缚在一种病态的人生策略中。悲哀的是,这些人极少寻求心理治疗,因为那样的
话,他们就不得不面对童年时的恐怖感受,而那正是他们一直在防御的。
当一个有人格障碍的人确实来做治疗了,疗愈的工作也会艰苦卓绝,因为他会拒绝内化——有
时候是没有能力内化。实实在在地承认自己的感受,并为此负起责任,这项能力是一个人能否
在心理治疗或关系中得到疗愈的主要指标。再强调一遍,这相当于要求一个人去做他认为不可
能的事,去承受住莫大的伤害,并且切切实实地感受它。偶尔,疗愈确实能发生,但这不是因
为治疗师的解释或干预,而是由于患者感受到了一致的、持续的、充满关爱的关系,这正是当
年那个孩子不曾感受到的。若要全面更新一个人的自我感、对他人的体验,还有面对他人时的
反射性反应,需要付出许多年的耐心。
虽然人格障碍是最难治疗的,但此处的任务与其他沼泽里的别无二致:全然地经历它、穿越
它,勇敢地直面焦虑,推翻它的暴政。可是,承受住这份原初的焦虑,冒险离开当初为了生存
下去而发展出来的人格结构,这绝非易事。生命早期的体验越是难以负荷,自我遭受的破坏就
越严重,这项任务也就越发艰巨。
在对焦虑的管理中,上述策略的各式变体,以及各种条件反射式的反应,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
能找到。区别只在于反应出现的时间早晚和系统化的程度。这些模式在人生中出现的时间越
早,不假思索的程度越深,我们受到的束缚就越严重。恐惧是正常的、自然的;狭义的焦虑
——这种与我们的个人历史直接挂钩的感受——是正常的、自然的;广义的焦虑——人类生存
处境的脆弱性所导致的结果——也是正常的、自然的。不同的是这些感受的程度,以及我们做
出的反应的性质与后果。面对焦虑,我们每个人都会发展出条件反射式的反应,所以,我们都
可谓是自身历史的囚徒,而且往往并不自知。
只要我们的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反应依然还像程序一般,牢牢地安装在我们的“主机”里,无论
是否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种状况,我们也依然是伤害自己的同谋,令心中的创伤久久不愈。“无论
我逃向哪里,都身在地狱;我就是地狱。”
正常的焦虑与神经症性质的焦虑之间存在本质上的不同。想要充分地、尽情地生活在这个世界
上,我们必然会频繁地经受焦虑——作为一个有感知能力的物种,这种感受是我们命中注定
的。永远不要因为感到焦虑而嘲笑自己。唯有当焦虑妨碍我们尽情生活的时候,它才能称得上
是心理问题。而且,当我们自行选择的策略变成了阻碍,这就变成了一个道德问题。我们感到
焦虑是吗?但我们依然应该充分地、尽情地活着。想想尼科斯·卡赞扎基斯为自己撰写的墓志
铭:“我一无所求。我一无所惧。我是自由的。” 一个很难达到却值得追求的目标啊。
要踏上人生这趟旅程,拿到车票的代价就是承受焦虑;没有车票,就没有旅程;没有旅程,就
没有人生。我们可以躲开焦虑,能躲多远就躲多远,可我们也因此躲开了这只有一次的人生。
正如弗洛伊德指出的,心理治疗的任务就是让一个人从“神经质的苦难”转到人生的“正常苦难”之
中,所以我们不得不去面对那些无法面对的,不得不去承受那些无法承受的,为那些缠着我们
不放的、无法命名的东西命名。
再强调一遍:每一天,我们都被迫要在抑郁和焦虑之间做出选择。抑郁源自个体化的进程受
挫,而个体化正是我们最为重要的任务;焦虑则源自向前迈入未知。焦虑之路是必要的,因为
这条路上存在着“成为更加完整的个体”的希望。我的分析师有一次对我说:“你必须把你的恐惧
列入议程。”当我们真正面对这个议程,去承受它引发的一切焦虑时,我们的感觉变得好起来
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真诚地面对自己。
勇气不等于没有恐惧。勇气意味着,我们深知,比起令我们恐惧的东西,另外一些东西更为重
要。比如说,个体化的任务就比一切阻拦我们前进的东西更重要。有趣的是,当我们能够坦然
接受存在性焦虑,知道自身是脆弱的生物,依附在一颗不停旋转的、于时空中急速坠落的星球
上,与此同时,还能感激自己有机会参与这一趟伟大的旅程,此时我们就向着个人解放迈进了
一大步。焦虑就像雾一样,让我们看不清前方的道路;如果我们能够从中走出,就会大有斩
获。当我们置身于雾霾之中,就可以辨认出具体的恐惧,而且,我们常常会发现,从成年人的
眼光来看,那些恐惧其实是没有根据的——但对孩子来说,它们可怕到难以负荷。比如说,一
个人极度害怕冲突,而且不敢在会议上发言,那么他需要在令人动弹不得的焦虑之雾中找出恐
惧的根源。一般来说,这种焦虑的念头可以追溯到生命早期的恐惧,比如,“他们不会赞成的”,
“他们该不爱我了”。
对于孩子来说,这般原初的恐惧是实实在在的;但我们已经长大成年,可以拥有不同的体验
了。身为成年人,我能够去有意识地觉察,去直接面对和处理,这些将我从无意识的、往事施
加给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们真正地察觉到,有些东西比我们恐惧的东西更重要。确实如
此。我们就比我们恐惧的东西更重要。这就是勇气的含义。
现在,我亲爱的外孙女瑞秋·艾林已经降生,成了我们的一员。七磅九盎司,胖鼓鼓的小脸蛋
儿,眼睛美得让人愿意为之付出生命。她正精力充沛地哇哇大哭,她想要食物,也想要那个她
再也回不去的地方。长着胖鼓鼓的小脸蛋儿和美丽双眼的瑞秋,踏上了她那奇妙的,也满载焦
虑的人生旅程,朝着她的命运走去。她,以及我们所有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超越宿命、走向
命运 ,将直接取决于我们能从存在性焦虑——它将一直是我们如影相随的旅伴——的手
中夺回多少人生。
第八章
情结:“大脑主机”里的模式化反应
在探讨“如何应对沼泽地”之前,我们需要先花点时间回顾一下荣格的情结理论。关于这个主题的
文章已经有很多了,所以我们不会在这里停留太久。但在本书的这个阶段,情结的概念对我们很
重要。
如果荣格在1912年之前过世——此时他提出了原型与集体无意识的理论——他依然会是心理学领
域中的重要人物,因为正是他发现了情结的存在。事实上,为了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区别
开,荣格将自己的方法称作“分析心理学”(psychoanalysis),而在此之前,由于情结在他提出的
心灵模型中的重要性,他曾将自己的研究命名为“情结心理学”(complex psychology)。实际上,
弗洛伊德在介绍精神分析的演讲中,曾因荣格和所谓的苏黎世学派提出了“情结是梦的建筑师”而
对他们大加褒扬。
导致荣格想出情结这个概念的因素有许多,在此我只提两个。在一篇医学论文中,他研究了一个
灵媒,她那梦呓式的话语引发了他莫大的兴趣。 这位女士是荣格的亲戚,他相信她不会
造假。那么,如何解释经由她发出的那些“声音”呢?她没有精神病,也没有产生幻觉。荣格考虑
过幽灵从另一个世界现身的可能性,但他后来得出结论,认为那个灵媒可以把自我的管控降到极
低的状态,从而允许内心中另外一些部分发声。(做梦时我们都会经历这种情况。)
另外,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荣格在苏黎世的伯格霍兹里医院(Burgholzli Klinik)做“词语联想”
的研究,他发现,在对词语做出反应时,即便是正常人的注意力也会受到干扰。看上去,就像是
这些刺激词语引发出了强烈的情绪反应,足以干扰到意识的运作。 后来,荣格推测,我
们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一簇一簇的“分裂出来”的能量,他将之称作“情结”。
情结只是一种蕴含着能量的构造。这些能量有可能是积极的,也有可能是消极的,或是两者皆
有,这要看它们对我们的生活有何影响。情结是由我们的历史造就的。我们无法避开情结,因为
我们永远不可能摆脱自己的历史。事实上,我们身上发生过的每一件事似乎依然都还在心灵深处
存活着。事件发生的时间越早,情结的力量就越大。因此,由于孩提时期的敏感,父母情结对我
们心理产生的影响往往是最大的。
一般说来,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被情结操控了,因为当情结被激活的时候,它有力量接
管我们的意识。你可以试试看,对一个正被情结掌控的人说他的情结正在运作,看他会作何反
应。他肯定会矢口否认,并且会坚称自己的看法合情合理。唯有在做出行为之后,在行为造成破
坏之后,我们才会发觉情结的存在。或者,当我们察觉到身体出现反应时,或许能想到这是情结
被激活了,因为它蕴含的能量总会影响到身体。突然感到手脚冰冷、嗓子发紧、掌心冒汗等等,
这些线索都预示着那些分裂出来的能量被激活了。
另一种可能是,我们可以从情绪状态中发现情结的端倪。当我们感到自己的情绪“飙至满格”的时
候,可能会猛然领悟到,这是被情结掌控了。即便如此,理解情结,削弱它所蕴含的那些我们不
想要的力量,这项工作往往会持续一生。
下文中的图阐释了情结的运作状况。当我们落入沼泽状态,在所有的负面影响之下,我们很有可
能会再次启动旧模式来应对。如果我们打算走出心灵的沼泽地,推翻“过往”这个暴君,就必须了
解这个运作过程。
下图画出了心灵的三个层级:意识,或外部世界;个人无意识,即个体情绪历史的总和;原型,
或者说集体无意识,在这个地带,我们与全人类——包括过去的和现在的——共享着共同的特
质、驱动力和模式。
在个人无意识的领域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源自个人经历的情绪能量。比如说,如果我们曾经
被狗咬过,就会产生一个“被狗咬”的情结——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它的存在。即便我们很喜欢
狗,因为我们也有很多和狗相处的正面体验,这个被狗咬的情结还是会存在。当与早先经历一模
一样或类似的情景发生时,它就会被激活。
这样说来,那一簇簇的能量就像按钮一样,而且无可避免要暴露在世界面前,任何人在任何时间
都有可能无意中碰触到它们。关系越是亲密,可能被碰触到的按钮就越多,因为这样的密切关系
更加接近最原始的亲密,即亲子关系。出于这个原因,亲密关系会无可避免地背上“往日创伤”与
“不切实际的期望”这两副重担。当然,这对我们的伴侣并不公平,但这是避免不了的。
事实上,外部世界里的任何事物——一次偶遇,某种气味,电台里播放的一首歌,在街头无意中
瞥见的一张面孔——都有可能激活那些无意识的能量。这些刺激物会马上遇到一个“棱镜”,一个
基于过往事件的过滤器。过滤器提出一个问题:“我好像遇到过这种情况?”刺激物或许是独特
的,是我们从未经历过的,可心灵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过往体验,它马上就开始搜索类似的状
况。身在国外的时候,我们会四处搜寻熟悉的词语或习俗,好让自己感觉舒适一点,这是为了减
轻面对未知时的焦虑。不过,无论是身处异国他乡,还是在家里,如果我们基于过往的类似体
验,对当下做出不假思索的、条件反射式的反应,就会遇上大麻烦。
古希腊人认为,我们之所以常常做出害人害己的选择,是因为我们性格中存在缺陷,他们将之称
作hamartia,即人看待世界的方式。这倒不是因为我们天生邪恶,或是故意不通情理,而是我们
确实有自我破坏的倾向,一次次地重复原有的模式,再忍受结果的折磨。这个hamartia就是一种
心理棱镜,由我们对世界的直观“解读”构成。它是以下三种体验的结合体——原生家庭、文化环
境、个人创伤;它引导我们带着偏见看待世界。我们通过这个滤镜看待自己和他人,并以它为基
础,一次次地做出与过往类似的选择。显然,除非我们把它带入意识,并拓宽视野,否则就会永
远被狭隘的视角局限住。
饱含能量的个人情结在心灵中回荡,激活了那些我们一直没能消化吸收的原始情绪。这些未分化
的心灵历史包括一切在孩提时期没能力处理的情绪。显然,如今我们的处理能力肯定比那时候强
大,但即便是成年人,也有可能被日常生活中巨大的情绪波动压垮。此外,个体的独特情结就像
桥梁一样,通往整个种族的原型体验。例如,我们与父母相处的体验化作饱含能量的情结,能够
激活原型。这种生命早期的心理素材的核心是两种创伤:难以负荷的重压、遗弃。除却父母情结
之外,我们内心深处还存在对生活的总体感知和印象,即这个宇宙在总体上是滋养人的还是带有
恶意的。因此,任何一个情结其实都深深地根植于“存在”(Being)的土壤之中。当个人情结被激
活,涟漪渐渐扩散到我们所共有的那片“水库”中去,引发出共振——在那片水库中,我们参与着
天地与自然中的一切。
当饱含负面能量的情结被激活,也在自然那摇摇欲坠的外围引发了共振,焦虑往往会随之涌现
——无论我们当时是否能意识得到。此处的焦虑既包括狭义的焦虑,也包括广义的、存在性的焦
虑。这些焦虑令人感到不适,是难以接受的,因此我们会条件反射地做出一些缓解不适的行为。
这类行为的范围极广:从对战,到逃跑;从解离和否认,到关怀强迫症与依赖共生。一生中,我
们可能会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渐渐地发展出一套特定的惯常策略与反应,来应对有压力的状
况。不知不觉间,我们变成了往事的囚徒,我们自己的囚徒。
情结的运作环路有点像电路。开关一合上,灯泡马上亮了起来;同样,刺激出现,棱镜开始运
作,原始情绪被激活,焦虑涌现,人就做出舒缓焦虑的行为……情结环路中的一连串动作也发生
在电光石火的一瞬。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我们不再居于当下,而是回到了遥远的过去,回到了
原初记忆的现场。而我们能察觉到的,不过是一阵突然袭来的强烈情绪。
我们会为自己的清醒意识与心智成熟而感到自豪,可是,一想到以下这些,真令人由衷地感到心
烦意乱:这一生中有多少时候,我们在不知不觉间被基于往事的模式所驱使,它们隐藏得那么
深,我们很可能从未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也不知道是它们在默默地掌控着我们。不过,情结的存
在确实对解释这些问题大有帮助——为什么关系是个棘手的难题?为什么我们总是那么频繁地给
自己设套使绊?为什么这个世界总是一团糟?
我们永远也无法彻底搞清楚,是哪些过往的力量在塑造和引导我们。即便我们意识到了某些情结
的存在,并努力消除它们的力量,它们也会负隅顽抗。某些环路隐藏得实在太深,以至于变成了
我们的“电脑主机”的一部分,就算把硬盘换掉,也无法抹去那些模式化的反应。对付情结,有点
像解放磨坊里的老马。终其一生,这匹马都在围着巨大的磨盘打转,我们解开它的缰绳,对着它
宣读了一大通权利条文,结果第二天早上起床一看,那老家伙还在围着磨盘绕圈。
我想起了帕特里克。从小到大,母亲屡屡入侵他的情感边界,她主宰他的人生,限制他的情感生
活,总体上压制了他的自然成长。他“逃离”母亲暴政的方式是娶了一个同类型的女人。几十年
后,他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妻子掌控了。如果事先不跟她请示,他一条意见也不敢表达,一件
事儿也不敢做。这真是“才出虎穴,又入狼窝”啊。
帕特里克这一辈子都在忍受抑郁的折磨,有些年他试图靠酒精来抚慰自己。与此同时,多年来他
一直在另一个城市有个情人。看到这个,你大概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吧。他会定期开三个小时的车
去看她,但又很难享受幽会的乐趣,因为他满心都是内疚,而且极度害怕妻子发现。就像磨坊里
的老马一样,他悲哀地沿着抑郁的老路一圈圈地打转。帕特里克的母亲情结硕大无朋,他只能要
么屈从,要么哆哆嗦嗦地在暗地里反抗。他不肯付出必需的努力——英雄式的努力——来挺直腰
板面对这个情结,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承受痛苦,夺回属于自己的人生。
往事与模式犹如深深镌刻在我们心中的程序,仿佛已经化作了我们自身的一部分。该如何超越它
们,而不是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内化?我们永远也无法突破过往的束缚——直到我们能够说出
这句话,并承担起其间蕴含的一切痛苦:“我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是我选择成为的那个
人。”该如何穿越沼泽,不再泥足深陷,不再重复过往,也不再更严重地伤害自己,正是我们最
后一章的主题。
第九章
穿越沼泽
看清你的想法和感受……那里站着一位强大的裁决人,一位不知名的智者——名字叫作自性。
真理总在较难抵达的那一边。
——弗里德里希·尼采
重新想象自我
驱车从北卡罗来纳州进入弗吉尼亚州的时候,路上会遇到一片面积非常大的沼泽地,它的名字
非常形象——“阴郁大沼泽”,当地人有时候就简称它为“大沼泽”。行驶在铺设好的道路上,穿越
这片乌烟瘴气的大泥潭,那感觉还挺有趣的,但我认识的人里面没有谁愿意住在那附近。有些
读者可能在想:“对呀,那我们该如何避开这些沼泽地?”这种看法当然可以理解,不过,请这样
想的读者翻回第一页,把这本书再看一遍。
重点是,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被拉到这些沼泽地中,而且是一次又一次。我们愿意相信,如果
我们活得正直,品行高洁,就会免遭此劫。但是,想想约伯的故事,还有《传道书》中的讯
息。宇宙又没跟我们签过道德合同。我们是乙方,或许会在暗地里起草了这么一纸合约,可人
家甲方拒绝在我们这偷偷摸摸的把戏上签字。我们也有可能会想,经过一番真诚的、训练有素
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找到一片高地,把城堡盖在那儿了吧。可恰恰相反,我们发现,尽管我们
做出了英雄般的努力,但结果还是令人失望:我们又落回了老地方,那片熟悉的巨大泥潭。那
些伟大的韵律——大自然的、时间与潮汐的、宿命与命运的,还有我们自己的心灵的——兀自
按照自身的强大法则运作,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
心理层面上的成长确实会带来一定的洞察,有些行为得以修正,偶尔地,我们还能收获智慧。
我们不断地落入沼泽,然后,通过修习自身的功课,我们看到,命运的召唤,或者说我们的任
务,就是承受住身处沼泽的痛苦,并找出掩藏在泥泞之中的意义。借由这些,我们有可能变得
更有意识。毫无疑问,我们所能做的最具破坏性的行为,就是责备自己居然落入了沼泽,还滞
留在那儿——好像预先知道前面有沼泽地,就不会掉进去了似的。
当我忍受焦虑的折磨时,如果我严苛地批判自己,焦虑感反而会变得更加严重,更不用说那没
完没了的忧惧和自责会给周围造成多大污染了。与创伤认同的人会一直卡在原地:“我是个无能
的人,因为我感到焦虑。以前一直是这样,今后必然也是。我简直一文不值,我的创伤永无疗
愈之日了。”
类似的想法在童年期很常见,我们如此弱小,无力抵挡他人的看法,而且“牵连观念” 的
思维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身为成年人,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意识到,焦虑状态并不遵从
我们的意愿,也未必存在什么因果关系,而且它们是短暂的、无可避免的,但最重要的是,我
们有可能把它们吸收消化掉,然后继续过自己的人生。我感到了焦虑,那就焦虑呗;我依然拥
有我的人生、我的任务。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这样宣告:“我自相矛盾吗?很好,那
我就自相矛盾吧。我辽阔广大,我包罗万象。” 我们也是一样。
早一天换上这种心态,对自我感的破坏就会少一点。许多人感到,自己仿佛被置身沼泽的经历
玷污了,被它打上了标记,殊不知,左邻右舍也忍受着同样的痛苦。我们会周期性地堕入那个
地下世界,如果能够接纳这一点,我们的灵魂会逐渐变得宽广,也能悦纳人生中对立的两极
——我们将这种悦纳称作智慧。知识是可以学来的;智慧不是。智慧来自对痛苦的消化和吸
收。被消化吸收的痛苦能够拓宽人格,让灵魂的疆域变得广阔。
在前文对情结的探讨中,我们提到,它们就像是人格的碎片,是带有分离出来的“生平传记”的躯
体状态,它们携带着情绪的能量,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触发,让人做出无意识的、条件反射式
的行为。一想到有多少想法和行为都被过往影响着,不在意识控制的范围之内,我们就不禁感
到心神不宁。要接受这个觉察,即“我们的内在是如此复杂”,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很可能会像那
匹磨坊老马,明明已经卸下了重担,却还是沿着乏味的老路继续转圈。
磨坊老马和我们之间的区别在于,我们有想象的能力。我们已经看到,每个情结都带有一小片
碎裂的世界观。当我们陷在情结里的时候——也就是说,当那个能量簇被激活,掌控了我们的
时候——我们就被局限在那个世界观里了。一般来说,那个世界观来自过去的经历,局限在当
初的创伤体验里,而且它会逼迫我们通过那个视野受限的“透镜”看待世界。磨坊老马继续重复地
绕圈,是因为它无法逃脱过往经验的局限,无法打破原有的模式。想象中的局限就是它的宿
命,它的宿命又局限了它的命运。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受限于情结,不断地重复原有的反应模
式,直到我们能够拓宽视野为止——也就是重新想象我们自己。
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Thus Spoke Zarathustra )中,尼采断言:
人就像绳索,一头连着野兽,一头连着超人。这条绳索横亘在深渊之上。危险的跨越,危险的
路途。回顾是危险的,颤抖是危险的,停步也是危险的。
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桥梁,而不是终点;人的可爱之处在于,他既是序曲,也是终章。
我们体内的“野兽”,即是由直觉与盲目反应化身而成的磨坊老马。“超人”是尼采对完成进化的自
我的比喻,是不再屈从于纯粹天性或过往历史局限的、扩展了的灵魂。矛盾的是,我们既是紧
绷的绳索,也是深渊。那深渊一方面是仿佛能将人吞没的存在性焦虑,另一方面,也是我们身
上体现出来的骇人自由。这种自由之所以如此“骇人”,是因为它令我们心中充满恐惧——我们要
迈步踏上那趟广阔的、看不见尽头的自我的旅程。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Antonio Machado)观
察到:
人类有四样东西
在海上全无用处——
舵、锚、桨
还有对沉入水中的恐惧
站在横亘于深渊的绳索之上——那就是我们所在的地方——确实很骇人,可是,我们没时间往
下看,没时间惊惶地逃回去,也不能站在半途,呆若木鸡。无论是否愿意站在那条高悬的绳索
之上,我们都已经在了。我们是被放上去的。就像帕斯卡指出的那样,问题不在于纠结要不要
挂帆起航,因为我们这艘船已经漂在海上了。
尼采所说的跨越深渊和我说的穿越沼泽是一个意思。穿越,指的不仅仅是在沼泽中坚持住,直
至瘴气散尽——虽然这也是必要的;它还意味着,借由辨认出每个沼泽状态中隐藏的任务,让
自己的内在变得更加广阔。当尼采把我们视作“序曲”,他的意思是,我们可以通过想象来更新自
我感,从而超越过往对我们的局限;当他把我们视作“终章”,他指的是,正是借由旧世界观造成
的局限的终结和死亡,我们得以从伊克西翁的铁轮上解脱。
尼采追求的是从西方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进入一种激进的、对个人的重新塑造。个体若要
更新,首先就需要有尼采所说的文化更新,个体必须坚定不移地对抗个人历史的力量。在我们
身后的,是过往的宿命,是局限我们的世界观,它们的力量一直支配着我们。踏在脚下的,是
跨越深渊的骇人自由。在前方,在深渊的那一端,是被拓宽了的灵魂,在那里,个人历史被接
纳、被包容,但它无法再控制我们的生活。迄今为止,我们对原生家庭与社会文化的体验构成
了那条绳索,我们颤抖着,摇摇晃晃地站在上面。我们接受的教育、对世界的探索、他人的榜
样,以及从错误中学到的东西,带领我们走到了现在。于是,如今我们置身于绳索的正中央,
距离起点和终点一样远。
那么,是什么构成了绳索的后半段?是想象力,也就是对自我进行重新构想的能力——我们比
过往发生的那些事情更强大、更广阔。我要再强调一遍,如果一个人不能真诚地说出这样的
话,就无法获得自由:“我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是我选择成为的那个人”;“我不是我的角
色;我是我的人生旅程”;“我不是我那有限的人生经历,我是我的潜质中的创造力”。这种对自
我的重新构想无法让我们避开沼泽,但我们受到的污染会少很多。
对心灵的运作来说,想象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画面携带着能量。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
说情结本身就是一个意象,一个承载着能量的意象。当那一簇能量被激活,它触发了这样一个
画面:我们是谁,身处什么境地,必定会做出什么反应。这些画面存在于我们的身体里,存在
于表达创伤与抗议的躯体状态中。这些画面也存在于我们的无意识状态中,我们可以在梦境、
幻想与积极想象中看见它们。心灵能量是看不见的,但心灵通过画面把那些能量显化出来。因
此,情结是受到过往经历影响的画面,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就会受到消极的影
响,因为它们显化出来的画面是严重受限的,视角片面且狭隘。无论我们是否愿意,这些画面
都会推动我们的人生;而洞察、经受痛苦、个体化等个人功课的目标就是拓宽这些画面。
从下面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过往的经历会给人造成怎样的局限,重复出现的有害冲动是什
么模样,拓宽自我意象是多么重要。
罗伯特是一位四十五岁的商界管理者,有一个非常自恋的母亲和一个性格被动的父亲。罗伯特
从父亲身上学到的就是,他这辈子的任务就是要照顾一个受创的女人。此外,在童年时期,罗
伯特还做过一系列非常痛苦的脊柱手术。父亲的示范,以及手术中体验到的那种入侵的力量,
都令他深深相信,在这些全能的力量面前,他是无力的。他不仅没有力量做出自己的选择,还
要承受“为他者服务”的双重压力。在描述生活体验的时候,他经常使用一个比喻:感到自己好似
被牢牢地绑在了医院的病床上。考虑婚姻大事的时候,他娶了一个身患先天性疾病的女子,妻
子疾病发作的时候他必须照料她。在外界看来,这种选择或许意味着同情心,但实际上,这是
一种满含负疚的、被过往经历训练出来的、面对外界力量时的被动心态。
到了中年,罗伯特陷入了令他身心衰弱的抑郁。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讲到的,心因性抑郁
反映出的是心灵的某个部分受到了压抑,并处于痛苦之中。在罗伯特的生命中,一切感受、欢
乐、活力都被深深地压抑了,实际上,他向来处于“微笑型抑郁”的状态。渐渐地,在不知不觉
间,他陷入了一段办公室恋情,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工作。他被迫离职,没过多久,婚外情造成
的伤害也令他离开了家庭。结束婚姻固然痛苦,但罗伯特结束的其实是一份没有挑明的合约,
这个合约是他无意识地与母亲缔结的——他答允要照顾这个受创伤的女人,而且这个合约得到
了父亲的批准。要想离开这个在早年就形成的情结,罗伯特唯一能采用的方式或许就是离开那
段婚姻。
经过一段痛苦的调整期,经历了事业上的混乱、金钱的压力和对失败婚姻的愧疚,罗伯特和情
人在一起了。未来似乎变得光明一些了,过往负担的危害也在减弱。可是,说不清为什么,罗
伯特发觉原先的抑郁依然在困扰他,那种感受有所减轻,但并未彻底离开。他时常感到自己快
被压垮了,新事业也毫无起色,有时他还会跟新伴侣吵架,弄得满心怨憎,恨不得一走了之。
罗伯特没有意识到的是,他的父母意象反映出的世界观,还有面对手术的无力感,依然牢牢地
焊在他的“电脑主机”里。没过多久,他就开始用同样的被动攻击策略来对待新伴侣——他见过父
亲用这个办法,对待要求苛刻的前妻时他也亲自用过。如今这个办法又出现了,这是一个自觉
无力将人生直接承担起来的人采用的策略。他对新伴侣的怨憎就像是发脾气发错了对象,而且
他开始破坏对改变的期待,以及这些期待所引发的新生活。于是,在工作、亲密关系、与自我
的关系这几个领域,罗伯特又回到了旧日的沼泽地。也就是说,无论我们远游到哪里,都能遇
到自己的情结,因为它们一直如影相随。“无论我逃向哪里,都身在地狱;我就是地狱。”
在这个节点上,罗伯特来做治疗。他感到无望和无力,实际上,这正是他的原始情结的合理展
现。他花了一阵子才认识到,他下意识地把母亲在他生命中施加的力量转移到了新伴侣身上。
这就是为什么他开始感到抑郁、怨憎,并开始被动攻击对方。若是发现自己又落入了原来的沼
泽地,想必谁都会有同样的感受吧。同时,他也把医院病床上那个吓坏了的孩子的无力感转移
到了面前的艰巨任务上——在商业世界里重整旗鼓。
就在最低落的时候,罗伯特做了这样一个梦:
我跟N(他的新伴侣)在一起。那边有两个小池塘,一个浑浊,一个清澈。我躺在后面那个池塘
里。有一个男人站在这个浑浊的池塘边钓鱼,一杆就钓起来五条鳟鱼。我走进浑浊的池塘,很
快就开始下陷,就像踩到了流沙似的。我滑到了六英尺深的地方,于是我赶紧背对着塘底,把
双臂平伸开,稳住自己,免得陷得更深。我卡在那儿,屏住呼吸,感受着那股把我吸下去的力
量。
说到沼泽地,这个梦清晰地展现了罗伯特的处境。他感到,在那一刻他只能挣扎着“踩水”,竭力
避免沉下去。
反思梦中的景象时,罗伯特想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联系。他曾经跟父亲一起钓过鱼,那是很美
好的记忆,加深了他和父亲的感情。他注意到,那种浑浊的池塘里肯定不会有鳟鱼,因为它们
需要干净的活水,可那个钓鱼的人从泥坑里钓出了五条。罗伯特把他的地狱带进了新的亲密关
系中。N就在那儿,可他没办法转向她,她也无法帮他走出困境。一个池塘是清澈的,代表与无
意识那健康的、疗愈的相遇,可当时罗伯特几乎溺死在另一个池塘里。他的身体姿态——他说
那就像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让他想起被平躺着绑在病床上的样子。事实上,他想起小时候心
惊胆战地等着被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输液管插进了他的手臂。罗伯特害怕自己会淹死在那个
泥潭中,他就快撑不住了。
罗伯特的梦境完美地展现出一个人的原始情结对当下生活的影响。面对新的选择,他发觉自己
受到了旧模式的束缚。在重塑生活的过程中,他表现出来的被动状态反映出的是想象能力的局
限。他希望N来拯救她,但她没有。(在真实生活中,如果她真的这样做了,就会落入“母亲”的
角色,而他也并不会因此变得更好;他必须拯救自己。)
在梦境与真实生活中,罗伯特都有两个选择:他可以渐渐在泥沼中沉溺下去,直到生命活力消
失殆尽;或者,他可以拼了命地游出去。何况,梦里还出现了一种阳刚的能量,这为他提供了
另一个办法,回应了他对于“从父亲那里取得授权”的需求。钓鱼男子既能走进水里,也可以留在
岸上。他有能力把关键要素从深处拉出,也就是那些能提供营养、让人维持生命的鱼儿。而
且,有趣的是,构建梦境的那位睿智的建筑师知道,对于那些真心想钓到鱼的人来说,即便在
阴郁的沼泽地里,也能找到鲜活的鳟鱼。
我们在讨论那个梦的时候,罗伯特想到,梦里的那个钓鱼男子或许可以把钓竿伸到六英尺之下
(这让他想起被埋在六英尺深的墓穴里),把他拉出来。但那名男子代表的只是获救的可能
性。罗伯特必须努力主动与他取得联系,也就是说,罗伯特需要重新想象自己的样子——不是
那个被绑起来的、被动的、吓坏了的孩子,而是一个努力游泳的人。这个游泳的人可以亲自招
呼那个钓鱼的人,而后者代表的是获得了授权的阳刚力量,能够将他拉出泥沼,拉出那个伊克
西翁式的对父亲人生的重演。这就是罗伯特必须完成的功课,即重新构想他的自我意象,走过
那道深渊——我们必须拿出勇气,去构想出那条踏在脚下的绳索。
如果我们把地狱带在了身边,还通过重复出现的冲动去重建它,那我们必定也把那位地府的主
宰带在了身边。圣保罗说,他知道正确的事是什么,但他没做,他为什么不做呢?基督徒或许
会说,我们容易堕入罪孽,容易凭着某些邪恶的愿望做出糟糕的选择。柏拉图,以及这么多年
以来的柏拉图主义者,18世纪的自然神论者,还有19世纪和20世纪的众多自由派改革者们都认
为,没做正确的事是出于无知。他们说,如果我们受到更好的教育,有更清明的意识,就会做
出好的选择了。而另外一批人——从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深度心理学家——认为,有一种
阴影性质的能量存在,它不受自我的控制,甚至还会引诱自我成为它的同谋。因此,“好”的价值
观也有可能做出坏事。
达豪集中营(Dachau)里有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有一条道路通向自由,里程碑是服从、勤
劳、诚实、有序、洁净、持重、真诚、牺牲精神、爱国精神。”把美德拿来用在这么一个地方,
这颠倒黑白的能力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我们随身携带的是怎样的恶魔,竟能顶着良善的名义
犯下如此邪恶的罪行?
从功能角度说,我们必须面对的这个恶魔就在我们的内心;我们走到哪儿就把它带到哪儿,它
把力量渗透到我们的每一个举动中。这个恶魔体现出,我们的个人历史在按照自身的独立意志
运作。荣格观察到,我们“被无法自控的状态附身,就像最黑暗的中世纪所说的女巫或猎巫人一
样。只是叫法不同而已。那个年代的人把这叫作恶魔,今天我们把它叫作神经症”。 发
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我们如何诠释和理解过往的经历、如何把这些理解内化,这一切都深深根
植在我们心中,导致我们重建出一个不断更新的地狱。
“我即地狱。”只要这个恶魔还没有被命名,可以在无意识的洞穴中毫无阻滞地肆虐,我们就会为
它做事。这种力量在罗伯特心中运作,把他与母亲、与病床上的那个孩子永远牢牢地绑缚在一
起,还破坏他的亲密关系。他将会一直迷失下去,除非他能够为他的恶魔命名,在此后余生的
每个时刻都勇敢地面对它——这是为了赢得更为广阔丰盈的自我意象而进行的战斗。在这个意
义上,圣保罗在《使徒行传》26:18中这样写道: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在这个意义上,萨提殊·库玛发现:
思维是相当靠不住的。如果加以监管,它是个有用的工具。但是,如果没有监管,它就会制造
问题。这是一部非常高效的机器,不用任何原材料,就能制造出成千上万的问题!就这样,我
们制造出问题,再把自己变成这些问题的受害者。这就是在思维的协助之下创造出来的战
争……我就是自己的地狱,是自己问题的创造者。
唯有足够成熟的人,才能承认这个悖论:敌人正是自己。人至少要到中年,才能承担起这个艰
巨的任务。人需要对外部世界做出诸多投射——职业、关系、社会角色——并且承受投射无效
的苦果;人需要犯下足够多的错误,才能渐渐地看出自己的模式;人需要先发展出一个足够强
大的自我,才能有胆量向内寻找过往选择的源头。唯有在此时,一个人才具备了足够的阅历和
勇气,去盘点和辨析那些无意识的因果,进而突破旧模式,创造新生活。
虽然说,基本上要到中年时期,一个人经历的痛苦才足够多,也达到了足够成熟的状态,可以
开启拓宽意识的任务了,但中年之路与一个人的生理年龄没多大关系。当一个人不得不面对自
己的个人历史时——它正在按照自身的独立意志运作——一切就会启动。
茱莉亚已经寡居多年。失去伴侣之后,她一直非常痛苦地努力着,想要重归生活。悲悼之情当
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一项任务比悲悼更重要:找回自身的力量,找到属于她自己的人生智
慧。年轻时,茱莉亚早已学会放弃主见,听从全知全能的父亲。后来,她寻找那种能继承她父
亲的衣钵、继续扮演外部权威角色的男人。她找到了,也嫁给了他。在父亲和丈夫都离世之
后,茱莉亚感到被抛弃了:不仅被“权威”所抛弃,还有宇宙本身——如今这个宇宙看上去既陌
生,又心怀恶意。与此同时,她还不得不面对自身的老去、日渐衰退的健康,还有死亡的阴
影。
她需要借助治疗,渐渐找回自己的主见和力量,也找回意义更为深远的、哲学层面上的对宇宙
的接纳。此处我说的“哲学”二字,并不是指认知结构,甚至也不是宗教信仰,当然这两者都很有
价值,但我指的是情绪层面的延展与拓宽。茱莉亚的人生一直被父亲情结主导。虽然这看上去
并无坏处,但它阻碍了她的个人成长,令她在心理上并未成年。成长意味着她需要拓宽自我
感,不再做那个需要父亲保护和教导的小女孩。她就是深渊,也是绳索。就在分析疗程快要结
束的时候,茱莉亚做了下面这个梦。讲述这个梦境的时候,她说,这听上去好像是她编出来
的,可刚从梦中醒来,她就把它记录下来了。
我在外面散步。往左边一转,我发现了一个奇异的地方,那儿全是粉笔色或白色的石头。白色
的石头山,白色的石头路,连房子也是用粉笔白的大石块盖的,就像普韦布洛(Pueblo)的印第
安村庄似的。这片房子并不奢华,但也不是贫民窟。这里好像没有生命,没有绿植,也没有色
彩。
我走着走着,发现自己正走在主街上。我走进了一个大型展览里:那儿像是一个集市,有五花
八门的东西……每个人都很友善,都跟我聊天。那里有把椅子,旁边有一条大狗,显然是在哀
悼它的主人,而且它很感激我们注意到了它。
我觉得,这片白色的社区和集市就是人生的象征。市场蕴含着许多情感,但一切终将逝去。白
色的石头或许会永远存在,但不像那条狗和一个个纪念物那样饱含感情。
面对这个梦,茱莉亚的情绪基调是非常冷静、高度接纳的。她感到,这是一个“充满哲学意味”的
梦,它并没有把含义明确地说出来,而是展现给她看,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她把它吸收于
心。她迅速领悟到了梦境展现出的两极:永恒的白色石头城市,以及饱含激情的人生市集。叶
芝称之为“人类血管中的狂怒与淤泥”。 茱莉亚的人生之旅一直处于父亲与丈夫强有力的
羽翼的保护之下,因此她未能充分地承担起自己的人生,没有机会冒险临渊而立。
而她的梦敞开怀抱,接纳了对立的两极。投入生命,就意味着要承受失去之苦,要在沼泽地里
徘徊;然而,若是能够领会超越的意义,就能充分获得智慧。做过那个梦之后,茱莉亚就像变
了个人;它向她展现的,远不止一个概念而已。灵魂将对立两极之间的张力带入了梦境,其中
蕴含的智慧帮助她打破了旧范式,投入更为广阔的人生。有了更为广阔的自我意象,她可以做
出更广阔的选择了。她依然要承受悲悼、丧失与焦虑的痛苦,但她也明白了,自己有一个双重
的任务,投入人生,像那条悲悼的、忠诚的狗一样,承受着失去主人的痛苦,但同时也知道,
那座白色的石头城市将在失去之外永存。
茱莉亚不知道的是,里尔克也曾在一首诗中写到失去、消逝以及“白色城市”的意象:
一切都很遥远
而且早已逝去
我相信 那颗闪烁的星星
在数万年前就已经死去……
在这浩瀚夜空下
我想走出我的心
我想祈祷
在所有星辰中
必定还有一颗活着吧
我相信
我知道是哪一颗 经久不衰
是哪一颗 在夜空中那光芒的源头
像一座白色城市般 屹立永在
在生命能量的起起落落中,在永恒不变的消逝中,白色城市的景象只赐给那些已经穿越了名为
“失去”的沼泽地的人。
那些已经穿越了沼泽的人会领略到一种不可思议的甜蜜——虽然在遭受地狱折磨时,人不可能
想象到这种感受。我立即想到了《俄狄浦斯在克罗诺斯》( Oedipus at Colonus )、晚年的叶
芝,还有我自己的那个期待疗愈的梦。 据说,在九十岁那年,索福克勒斯 重拾
俄狄浦斯的主题,即那个讲述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受创的过去继续重创了后续世代的悲剧故
事。灾祸降临后,俄狄浦斯自我放逐,一连数年,他孤身一人浪迹天涯,以此赎罪。借由痛
苦,他变得谦卑,并与诸神建立了联结,当他在克罗诺斯走到生命终点时,他被封神,也获得
了诸神的祝福。因此,盲眼的但已获救赎的俄狄浦斯,这个已经“穿越”了沼泽的人,才有资格这
样说道:“痛苦与时间,那苍茫的时间啊,是教人满足的导师。” 还有日渐衰老、健康也
每况愈下的叶芝,回顾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后,在1929年这样写道:
我们必须大笑 我们必须欢唱
我们被世间万物祝福
我们看到的一切都被祝福
年轻人写不出这样的句子。我们必须等上数十年,经历过艰险和考验,最终渡过难关。这几行
出现在一首长诗的末尾,叶芝在诗中接纳了这一生中的失败、失望和失去。这里没有肤浅的乐
观,唯有一个人的深刻智慧——他这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沼泽地里,从雾瘴之中,他锻
造出自己的人生与艺术。
我在参加分析师培训时,曾遇到一个关键的时刻。当时,有诸多因素——完全不是财务问题
——让我感到无法再继续下去了。有天我做了一个深深触动我的梦。在梦中,我和儿子蒂姆在
森林中散步,那数百英尺高的松树上覆盖着皑皑白雪,景致美极了。然后关键的情节出现了:
蒂姆对我说,“当你承受了足够多的痛苦,还能像这些树一样高高矗立的时候,这雪就是天地赠
予你的礼物,是层层的恩典”。
落满白雪的树显得更美了,这确实令人感到这是一份饱含恩典的礼物。我的感受是,如果我能
想办法坚持下去,熬过困境,或许就能得到那份恩典。我的儿子本身就是上天赐给我的、饱含
恩典的礼物,同时他也是一个内在的象征,是我最好的、未来的可能性。这个梦本身就是一个
礼物,在我熬过那段困境的过程中,它对我的意义非同小可。
在研究灵魂沼泽的过程中,我会转向梦境,以及伟大作家们的智慧,这并非偶然。我们这些追
随梦境指引的人都知道,心灵中存在着丰富的、令人浮想联翩的、有独立意志的行为。我们被
拽落到怀疑、绝望以及其他数十种阴郁的沼泽地里,但我们也会得到充满疗愈作用的画面,这
恩典旨在补足我们的意识人格,为它指出新的方向,帮助它充分地发展。我们不得不忍受痛
苦,但我们得以穿越痛苦,寻找到更深层的意义。荣格说,神经症是尚未发现其意义的灵魂所
遭受的痛苦,因此,我们既不能免于受苦,也不能躲避“经受痛苦、寻找意义”的任务。正如里尔
克在他的人生与艺术中、茱莉亚在她的梦境中瞥见的那座永恒于时间之外的白色城市,当我们
在满是泥泞的沼泽中艰难跋涉的时候,我们也能寻找到心灵给予的支持。
另一个了不起的梦境有助于阐释这些。看上去,它好似比其他梦境的说教意味更浓,但做梦的
人坚称她没做任何修饰。在对那个梦的简短说明中,她这样写道:“那是一场在好几个地方同时
上演的戏剧。你在四处闲逛,在不同的地方体验它,每次只能得到全景的一个小碎片。你必须
把它们拼起来,努力理解其中的意义。”
这个梦若是写全了会有好几页,以下是最重要的情节:
我在最后一分钟赶到,连忙找了个最靠前的位置坐下。这更像是剧本朗读,而不是观看表演。
你只能听见声音,看不见发生了什么,想看的话只能通过墙上的一个小孔往那边瞧。我拿到了
一大堆关于这场剧的笔记和资料,我快速浏览了一遍,觉得很生气——他们怎么在刚开演的时
候发这些,应该在演完了之后发才对啊。我在资料里找到了好几张地图,能让人知道各幕剧在
哪些地方上演。这大概有助于理解全剧吧。
有两个男子低声说着剧中的对话,让人觉得好像在密谋着什么似的。我感到烦躁,因为我没法
听见完整的剧作。我找到自己的东西,再次换了座位。这场剧这么难以理解,真令人心烦。随
即我想起了之前听到的一点信息,说这部剧就是要去不同的场景中体验,你到各处去,边走边
搜集线索,然后努力地拼起来。
之后,有人告诉我们要摆弄手指,我觉得这好傻,也没半点用处。费这个劲干吗?但我马上领
悟到了什么——这是为了给另外一些东西腾出空间,一些新东西,所以才要摆弄手指。行吧,
现在我明白了,我需要四处走动,看剧,听各处的声音,然后看看能拼出什么来。
【梦境切换到了另外的场景,情节是一只骆驼被“骆驼蛋”引领着往前走。】
骆驼蛋掉到地上摔碎了!就在这时,一个成年男子从我们要去的那个方向走来。真是个悲剧
啊。随即我意识到,不,这不是悲剧!(只是表面上的悲剧而已。)蛋的作用就是把我们领到
此地,领到此刻。如今我们不再需要它们了。我们已经准备好,去接受下一个指引,发现下一
个洞察。
(上文中加粗文字是做梦人的原话。)
做梦的人名叫伊芙琳,是一位五十八岁的女士,她一直都明白,她需要找到自己的路。和我们
所有人一样,她希望得到确定性,但找到的只有碎片、失望,还有一场痛苦的离婚。她需要抚
养孩子,找到工作,但她最需要找到的是属于自己的真理。和我们所有人一样,她希望能有人
马上给她一个清晰的、连贯的完整图景。和我们所有人一样,她不得不痛苦地在几十年的漫长
时间里把一块块碎片拼凑起来。像茱莉亚那个白色城市的梦一样,这个梦告诉我们,我们面对
的是一场渐次展开的戏剧,但我们只能得到零散的碎片。它永远不会真正地清晰,我们的视野
永远不会毫无局限,我们对它的理解也永远不会彻底和完整。
但梦中的自我渐渐明白过来,这就是这场戏剧的特质:去不同的场景中体验它,一路收集你的
领悟,通过不断的摆弄和调整,为新东西腾出空间。其中的荒谬性超出了伊芙琳的理解,然而
她感觉到,这代表着她自身的某些活动,它们看似没有意义,但到了恰当的时候,就会引起某
些新的突破。她觉得这跟冥想很类似: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你开始感到沉闷和停滞,但随即
进展出现了。
对于骆驼,伊芙琳联想到的是“沙漠之舟”,能够在长途跋涉中——往往要穿越干旱地带——生存
下来的能力。蛋代表着她的潜力,是可以孵化的东西。但绝大多数的蛋都摔破了,这指向的是
她过去的行为,那些事把她带到了现在的地方,但今后对她不再有价值了。在这些破碎的蛋所
代表的东西中,她想到了她的婚姻、她作为母亲的角色、早先的职业生涯、她对父母的半推半
就的依赖,还有她在社区中各种各样的行为。她说那些蛋是“帮助我走了这么远的线索——这就
是它们存在的意义,而不是永远持续下去”。
这是个饱含智慧的梦,也是一个饱含智慧的结论。我们永远无法获得终极的确定性,永远无法
看见全部画面,永远也抵达不了阳光普照的草地。我们透过黯淡的玻璃向外看,而且只能看见
零散的碎片。叶芝说得好:
我为我的歌做了一件外衣
覆以用古老神话
做成的刺绣
于是,我们把这些经历和体验拼凑起来,穿在身上,走入世界。伊芙琳想要寻找确定性,想看
见更大的图景,需要外部的指引和权威,可这些愿望统统都落空了。但她领悟到,一个人为何
必须穿越沼泽地。她明白了,我们只能得到一些零散的碎片,还有不少破碎的蛋,但这一切都
是有价值的,都自有其意义。就像白色城市的访客一样,她也得到了邀请,可以参与这一场“伟
大的戏剧”,我们都是剧中的演员,但都微不足道。
印度教徒认为这个世界就是天神的戏剧。超越的愿景或许不太清晰,但是,我们去四处观看,
一路上孵化新蛋,承受灵魂的干旱之地带来的痛苦,到最后,所有这些任务都会帮助我们领悟
到,意义不在于抵达,而在于旅程本身。这就是一个“穿越”了沼泽的人悟到的智慧。没有哪个年
轻人,哪个执意要为凌乱破碎的生活找到解决方案的人,或是哪个想逃避痛苦中蕴含的任务的
人,能够穿越沼泽,领悟到这个智慧。就像俄狄浦斯与叶芝的人生故事,年轻的自我会对这个
奖励嗤之以鼻,永远也理解不了,但它确实是一个礼物,为此后的余生带来深度、成熟以及从
容的气度。
罗伯特、茱莉亚、伊芙琳,以及我们所有人面临的任务,正是尼采在上个世纪给我们提出的。
我们是“终章”,也是“桥梁”。必须终结的,是自我对控制、支配、安全感的渴望。这种渴望或许
相当自然,但它也会阻挡我们彻底转变。必须留在桥梁那一头的,是孩子式的渴望:抓住一切
安全感不放,不愿踏入未知的世界。我们的船太小,海洋太浩瀚。然而,最可怕的障碍始终是
过往经历对我们的束缚,是情结所代表的、受局限的世界观。
我们之所以崇敬真实世界里的发现者、探索者和先锋,还有那些拓展了思维或艺术表达的疆界
的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让我们看见了英雄的原型,我们每个人心中都蕴含着那种能量,为了
实现个体化的目标,它会自然而然地对抗那些令我们退行的力量,比如恐惧和无精打采。当外
部的英雄做出这种举动的时候,我们发觉自己内心里也有一种能量在共振,促使我们也去拓展
那些已知的边界。这就是尼采所说的,踩着紧绷的绳索(这绳索即是我们自己)跨越深渊。能
量已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冒险迈步,踏入前方的空间。在那个空间里,蕴含着更多自由,还有
更宽广的灵魂;那里就是我们注定要去的地方。
参考文献
arnold, Matthew. Poetry and Criticism of Matthew Arnold.ed.a.Dwight culler.New York:houghton-
Mi¤in,1961.
auden, W. h.Collected Poems.New York:random house,1976.
Bateson, Gregory.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New York:Ballantine,1972.
Bauer, Jan. Alcoholism and Women:The Background and the Psychology.toronto:Inner city Books,
1982.
Bonhoeffer, Dietrich.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New York:MacMillan,1972.
camus, albert. The Fall.trans.Justin O’Brien.New York:Vintage Books,1956.
__. The Myth of Sisyphus.trans.Justin O’Brien.New York:alfred a.Knopf,1955.
carotenuto, aldo. The Difficult Art:A Critical Discourse on Psychotherapy.trans.Joan
tambuseno.Wilmette, IL:chiron publications,1992.
__. Eros and Pathos:Shades of Love and Suffering.toronto:Inner city Books,1989.
The Complete Greek Tragedies. trans.robert Fitzgeral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7.
cooper, M. truman.“Fearing paris”.In River City, vol.9,no.l(Spring 1989).
corneau, Guy. Absent Fathers, Lost Sons:The Search for Masculine Identity.Boston:Shambhala
publications,1991.
edinger, edward F. The Creation of Consciousness:Jung’s Myth for Modern Man.toronto:Inner city
Books,1984.
eliot, t. S.The Four Quartets.In T.S.Eliot:The Complete Poems and Plays,1909-1950.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1962.
Flores, angel, trans. and ed.An Anthology of French Poetry from de Nerval to Valéry.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1962.
__. An Anthology of German Poetry from Hölderlin to Rilke.New York:Doubleday anchor,
1960.
Frankl, Victor. Man’s Search for Meaning.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59.
Frost, robert. Modern Poems.ed.richard ellmann and robert O’clair.New York:W.W.Norton,1973.
__. Robert Frost’s Poems.ed.Louis Untermeyer.New York:Washington Square press,1962.
heidegger, Martin. Existence and Being.trans.Werner Brock.chicago:henry regnery,1949.
hesse, hermann. The Glass Bead Game.New York: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1969.
hillman, James. Suicide and the Soul.Zürich:Spring publications,1976.
hollis, James. The Middle Passage:From Misery to Meaning in Midlife.toronto:Inner city Books,
1993.
__. Tracking the Gods:The Place of Myth in Modern Life.toronto:Inner city Books,1995.
__. Under Saturn’s Shadow:The Wounding and Healing of Men.toronto:Inner city Books.1994.
Jung, c. G.The Collected Works(Bollingen Series XX).20 vols.trans.r.F.c.hull.ed.h.read, M.Fordham,
G.adler, Wm.McGui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1979.
__. 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ed.aniela Jaffé.New York:pantheon Books,1961.
Kafka, Franz. The Diaries of Franz Kafka, I914-23.trans.Martin Greenberg.ed.Max Brod.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1949.
Kazantzakis, Nikos. The Saviors of God.trans.Kimon Friar.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60.
Kierkegaard, Sören.Fear and Trembling.New York:Doubleday anchor,1954.
Kliewer, Warren. Liturgies, Games, Farewells.Francestown, Nh:the Golden Quill press,1974.
Kumar, Satish.“Longing for Loneliness”. In Parabola, vol.20,no.2(1995).
Machado, antonio. Times Alone.trans.robert Bly.Middletown, ct: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83.
MacLeish, archibald. J.B.Boston:houghton-Mifflin,1958.
Modern American and British Poetry. ed.Louis Untermeyer.New York:harcourt, Brace,1955.
Mood, John. Rilke On love and Other Difficulties.New York:W.W.Norton,1975.
Moustakis, clark e. Loneliness.New York:prentice-hall,1961.
Nietzsche, Friedrich. The Portable Nietzsche.trans.Walter Kaufmann.New York:Viking press,1968.
Norton Anthology of Poetry. ed.a.alison.New York:W.W.Norton,1970.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 ed.Bernard Darwi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pascal. Pensées.New York:e.p.Dutton and co.,1958.
reynolds, David S. Walt Whitman’s America.New York:alfred a.Knopf,1995.
rilke, rainer Maria. Duino Elegies.trans.J.B.Leishman and Stephen Spender.New York:Norton,1967.
__. Letters to a Young Poet.trans.M.D.herter Norton.New York:Norton and Norton,1954.
Sharp, Daryl. The Survival Papers:Anatomy of a Midlife Crisis.toronto:Inner city Books,1988.
__. Who Am I, Really?Personality, Soul and Individuation.toronto:Inner city Books,1995.
Shelley, percy Bysshe. The Poems of Shelle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0.
tillich, paul. The Dynamics of Faith.New York:harper,1957.
__. The Shaking of the Foundations.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48.
tillyard, e. M.W.The Elizabethan World Picture.New York:Vintage Books,1954.
Wolfe, thomas. The Hills Beyond.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941.
Woodman, Marion. Addiction to Perfection:The Still Unravished Bride.toronto:Inner city Books,
1982.
Yeats, W. B.Selected Poems and Two Plays of William Butler Yeats.ed.M.L.rosenthal.New York:
MacMillan,1962.
Zoja, Luigi. Growth and Guilt:Psychology and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New York:routledge,
1995.
Zorn, Fritz. Mars.New York:alfred a.Knopf,1982.
后记
斑驳与模糊
潜入内心极深处时,每一个正常的人类都会心生畏惧,不愿继续;说到底,这种畏惧与抵制是
对走向冥府的旅程的恐惧。
——荣格
从这不受人欢迎的、下潜至冥府的旅程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如果那里有值得学习的功课,又
会是什么呢?本书提出了三个观点,或者说三个原则,如果我们能够认同它们,接受其中蕴含
的深意,它们就能引领我们走向更为广阔的心灵生活。
第一个原则是,由于心灵能量有自然的起落,所以我们会不可避免地被频繁拖入黑暗之地——
即便这违背了我们的意愿。就像困倦的孩子哭闹着不肯睡去,直到最后折腾得精疲力尽,我们
也是一样。我们认同那个脆弱的自我,以及它对永恒安全感的渴望——这渴望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也是徒劳无功的。当那个自我被拽落泥沼,我们感到挫败,还会为出现的症状而责怪自
己。我们因袭来的恐慌而羞耻,因抑郁而感到丢脸,我们掩藏起心中的恐惧——好像其他人从
不会被这些问题困扰似的。
因此,接受以下这几句话对我们实属关键: 我们的心灵生活会频繁地脱离自我的控制,我们
必定会被拽落到沼泽之中,而且我们会在那里遭受痛苦。 无论我们怎么否认,如何使用五
花八门的手段麻醉自己,或是信奉诸如“努力工作、端正思想”这样的信条,都不能让我们免于痛
苦。现代社会关于“幸福”的幻想是有害的,因为它非但不可能实现和持续,实际上还会加重我们
的神经症,让我们更加牢牢地抓住创伤不放。
第二个原则是, 在每一片沼泽地里,都暗含着一个挑战:发现这片泥泞中蕴含的意义,找
出我们在行为或态度上需要做出哪些相应的改变。 我们应当把每个沼泽地都视作待解的命
题:我的抑郁意味着什么?焦虑与我的哪些过往经历有关联?是什么在支配我、控制我?这种
态度会让我们主动地面对痛苦,而不是一味地被动忍受。在这样的搏斗中,我们从永久幸福的
幻想中,或未曾得到幸福的耻辱感中走出,走向一个或许最为珍贵的礼物——我们领悟到,就
算没有幸福,我们也能生活,但没有意义可不行。
在明辨每个沼泽地里暗含的任务时,我们“穿越”痛苦,朝着扩展了的意识走去。正如我们之前提
到的,荣格认为神经症是尚未发现其意义的灵魂所遭受的痛苦 。我们不可能免于痛苦,
如果我们陷在沼泽地中,却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充实自己的养分,我们收获的就只有神经症而
已。
本书的第三个原则是, 面对沼泽地带来的压力,我们每个人特有的反应模式是条件反射式
的,且被过往的人生经历所束缚,因此,为了活在当下,我们必须对自己进行重新想象。
对于活在当下的、有意识的成年人来说,可以做的反应非常多,选择范围很广。但是,激活了
的情结会令我们的视野变得狭窄,这是由我们退行的、反射式的反应决定的。我们无法消除情
结的活动,因为我们有着充满记忆的个人历史,有自己的世界观,还有一系列后天习得的态度
和行为。其实,有些情结反应是有好处的,能在危急时刻救命,能让我们与他人建立联结,或
坚定我们的价值观;而另外一些情结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就完全是消极负面的。最为原始的情结
自然是从最早期的生命体验中产生的,因此会把我们局限在孩童式的视野和反应中。
回想尼采呈现给我们的那幅奇特的画面:我们是深渊,也是跨越深渊的绳索。深渊意味着骇人
的自由,意味着广阔得令人生畏的人生旅程,而绳索意味着我们突破过往经验的局限、重新想
象自我的能力。如果我们被原生家庭、所属的文化或个人历史局限住了,那么我们就真的变成
了被动承受宿命的人。如果我们可以重新定义自我,迈步于深渊,踏着这条心灵想象出来的、
向前延伸的绳索跨越深渊,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加彻底地收回生命的主动权。
我们每个人都紧抓着两个不可能的幻想:永生不死、神奇他者。请注意,死亡并不属于本书探
讨的沼泽地之一,不过,肯定会有一些对死亡的觉察(或许还是过度的关注)终日萦绕在我们
心头。既然自我想寻求安全、稳定和控制,死亡就成了最严重的威胁、最黑暗的对手。但是,
或许死亡是一种莫大的解脱,让人可以从自我的琐碎执念中解放出来,或许它意味着自由和超
越。如果印度教徒是对的,那么人会经历诸多轮回和化身,获得最终的灵魂解脱。如果佛教徒
是对的,那么死亡犹如一场糟糕的梦,就像一幅错视画,是自我制造的一个妄念。如果一个人
能够超越自我的帝国主义,那么他就有可能超越那令我们痛苦的、生死二元对立的错误观念。
如果基督徒是对的,那么人还有来世。如果犹太人是对的,那么我们会经由子孙后代活下去。
无论一个人的信仰是什么,对死亡议题的思考都能提供一个参照点,它能够为生命引入深度
——从灵魂层面上思考我们是谁、我们该做什么。
我们能够肯定的是,有一种神秘的进程,它经由我们,寻求自己的充分显化;无论何时,只要
我们为内在的神秘服务,就能体验到与外在的神秘的链接。当我们有意识地与这种神秘保持联
系,就会活得更充分、更深入。虽然自我时不时地要经受存在性焦虑的冲击,但我们知道,自
我只不过是灵魂的一个小小的部分而已。如果帝王般的自我能够谦卑地、自愿地与心灵的其余
部分结为联盟,那么个体在与那个更广阔的神秘力量相处时,就会感到更加轻松自在。
如果自我能够永生不死,它会变得多么讨厌啊。但是,正如莎士比亚所说,“任是金童玉女,也
必像烟囱清洁工一样,最终归于尘土”。 因此,死亡并不是沼泽地,但存在性焦虑是。
死亡让人有可能拥有谦卑的智慧。
另一个幻想叫作神奇他者,即希望世上有一个人能够拯救我们,让我们不必踏上人生的苦旅,
让此后的生活一帆风顺。这种想法是非常普遍的。同名图书和电影《廊桥遗梦》( 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 )的流行即是这种有害愿望的表达——有一天,一位陌生人会出现在我家后
院,与我共享鱼水之欢,并因此与我建立起渴望已久的灵魂联结。
久久沉溺在这么一个幻想故事中,说明我们依然被锁在婴儿式的思维方式里。这源自孩子对父
母的依赖,它相当自然地转化为今后一切关系的模型。于是,我们把强大父母的范式迁移到了
他者身上。这种幻想,这种生命早期渴望的迁移,对关系的破坏力远远超过其他一切因素。一
段关系刚刚开始的时候总是清澈美好的,但我们的情结会污染它,而且,我们会因为对方没能
满足这个重大的隐秘渴望、没能实现这个不可能实现的期望而变得生气、沮丧和愤懑。
假使我们真的找到了那个神奇他者,最终他或她会成为我们最大的威胁,因为这个人会妨碍我
们更充分地成为自己。就在昨天,一位很有智慧的分析对象对我说,她正在学着不再“对希望上
瘾”。她依然盼望找到一段有意义的亲密关系,但她已经获得了力量,可以放下对神奇他者那令
人上瘾的幻想了。她的放下,正是艾略特所说的,“等待,但无需希望/因为我希望的 可能是错
误的东西” 。
永生,以及神奇他者的拯救,这两个幻想会妨碍我们尽情投入此生——此时,此地。如果我们
得到了上天的赐福,活到了中年,并且还拥有余生,那么我们必定已经经历过了不少痛苦。但
是,我们也被赐予了修正自己的能力。想要修正自己,我们不仅需要去朝拜帕纳塞斯山
(Parnassus)、雅典(Athens)、耶路撒冷(Jerusalem)或苏黎世,我们还要进入沼泽,在那儿
能学到的东西最多。如果我们活到了中年,并且还拥有余生,那么我们就有机会领略到智慧的
滋味。自我不会喜欢这种智慧,也驾驭不了,但它的广阔与丰盈是任何自我也想象不到的。“引
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
我们每个人都被赐予了一段旅程。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把这至关重要的“个体化”充分、彻底地
表达出来。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当有意识地、日复一日地修习这项功课,但与此同时,我
们也可以找一位心理治疗师做伴,让这个过程更加顺利。当然,心理治疗师也会有自己的创
伤,但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或她已经对创伤做过了功课,有能力明智地陪伴我们。无论以哪
种形式,艰难地穿越沼泽都会是一场教人谦卑也珍贵无价的体验。荣格曾写道:
心理治疗的原则性目标不是把患者送入那不可能实现的幸福状态,而是帮助他以坚定的态度、
富有哲学性的耐心来面对痛苦。生命渴求完整与实现,在欢乐与悲伤之间找到平衡。但是,由
于痛苦不为人所喜,人们很自然地不愿去认真思考会有多少恐惧和悲哀降临到人身上。于是,
他们用令人宽慰的方式谈论进步,以及可能获得的、最多最浓的幸福,但他们忘记了,若是不
曾充分地感受痛苦,幸福本身亦被掺杂了毒素。神经症的背后,总是掩藏着患者不愿承受的那
一切自然的、必要的痛苦。
每个人有各自的痛苦,但在这段共同的旅程中,我们都是同路人。我们实实在在地拥有这段旅
程。荣格提醒我们:
人格的获得……是面对生命的饱含勇气的举动,是对构成个体的一切的绝对肯定,是对普遍生
存境况最成功的适应,再加上最大程度的、自我决定的自由。
此外,他还说:“每一个个体都是生命在其变幻不定的情绪之下所做的崭新实验,是对崭新的解
决方法或适应方法的尝试。” 我们在沼泽中所做的功课,会创造出这种崭新的适应方
法,它令生命之力得以延展。
荣格也说过,每种神经症都是一个“被冒犯的神祇” ,他的意思是,某种原型层面的原则
被违背了。借由承担起每一个沼泽地中隐含的任务,我们有机会看清这些神性的原则。我为何
要用“神性”这个词?因为心灵的活动天生就具备宗教的性质。它寻求联结、意义,以及超越。一
个意味深长的悖论就是,更有可能发现这些神性原则的地方,不是在高山之巅,不是在大教堂
内,而是在沼泽地里。
生命具有超然的神秘,同时也是模糊的,还带着斑驳的污迹。我们永远也不能真正看清它。我
们永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永不可能将之完全修复,永不可能彻底完成。
珍妮弗要去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看望临终的母亲。上飞机时,她因这次见面而惴惴不
安,因为母亲一直想方设法毁掉她。然而母亲就要死了。“克制,同时保持开放……克制,同时
保持开放。”这成了珍妮弗的箴言。在飞机上,在机场,在医院的电梯里,她不断地默念这几个
字。珍妮弗想要用开放的心态面对母亲,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刻,给她饱含情感的回应,同时
也要在心理上保持克制,免得自己再度遭受野蛮的攻击。
然而,面对母亲,珍妮弗仅能勉强克制住心中的怀疑和愤怒。因此,这最后的一面给她留下了
深深的挫败感。几个月后,关于这最后一面的梦和场景闪回像洪水一样淹没了她。她狠狠地责
备自己:为什么自己还带着那么重的防卫心态?为什么如此漫不经心,在情感上为何如此疏
离?为什么没能跟母亲一同哭泣,然后说自己爱她?珍妮弗知道,那句箴言她只做到了一半:
有克制,但不够开放。
是啊,我们永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生命中满是斑驳与模糊,它速度太快,太复杂,太含混。
清晰、意义、胜利只会偶尔出现。当然,我们不是神,虽然我们心中有神性,但也同样带有恶
魔的成分。我们能生存至今真是个奇迹,而且,我们有时还能寻获片刻安宁,能友善地对待他
人,甚至偶尔还能对自己展现一点仁慈。
我们应该像珍妮弗责怪自己那样去责怪她吗?我们会告诉她,那最后的一面需要放到整个情境
中来看,因为她和母亲之间存在漫长的、满是伤害的历史。她会答复说,她又被拽到了原来的
沼泽地里,又用了原来的老办法去回应,她没能做到“超越”,没能抓住当时的机会。那么我们就
会请她做一件我们自己也感到最难做到的事:原谅自己只是个凡人。
在最后这个分析案例中,我们没能解决问题,因为人生并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而是一场
需要活出来的实验。借由痛苦,我们越来越深入地领悟到生命的意义,这就已经足够了。这些
意义令生命变得丰盈广阔,它们本身即是回报。我们无法避开这些灵魂的沼泽地,但是,我们
可以因它们给予我们的东西而珍视它们。
我们必须静静地继续前行
穿越那黑暗的冰冷 和空茫的孤寂
进入另一重情感的强度
去寻求更深层的和谐 更深入的交流